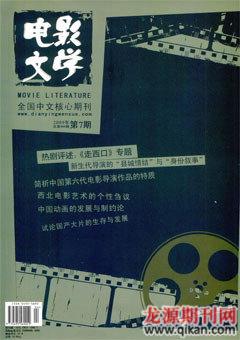放纵与反抗
冯仙丽
[摘要]新感觉派在他们的都市创作文本中,大肆渲染都市物质世界的新奇、刺激以及对现代人巨大的震撼力量,在小说的内容和结构模式上呈现出颓废色彩和放纵的姿态,然而透过文本迷乱、“自虐”的表象新感觉的深层的反抗意识也是我们不可忽略的事实。这种创作倾向上的多元性直接源于都市文化的驳杂性以及都市文化对知识分子的“异化”作用。
[关键词]新感觉派,放纵,反抗
物质文明的发展一方面为现代都市人提供“史无前例”的新奇和刺激,另一方面,都市的机械化、直线型和快节奏又给他们带来精神的压力和痛苦。新感觉派小说正是在浓郁的都市情调的渲染中插入不和谐的音符以此来提示都市的分裂状态和二重性。但由于创作对象的复杂性及创作主体对都市发展进程认识的局限,新感觉派的小说在主题表达和文本的价值体现上也存在着诸多分歧和不协调现象。新感觉派本着良好的初衷,“以先进的社会学视角批判都市,而又时时流露出流氓根性与低俗的市民意识…”海派文化的先天性不足使新感觉派在创作中情不自禁地偏离主题,他们或流连于庸俗的低级趣味中,或陶醉干自己发起的“语言暴动”中而忘记或逃避自己创作的神圣使命。但是历史从来就不是以单纯的面目示人,由于都市文化的驳杂性使得新感觉派在放纵的外表下时而呈现出反抗的姿态。
在新感觉派创作的都市小说中,男女情爱,特别三角恋爱的故事占绝对的优势,这是新感觉派为现代都市文化所作的另一种注释:现代社会创造让人瞠目结舌的物质奇观,同时它也在不断创造着“绝代”“爱情奇观”。《游戏》(刘呐鸥)中,女主人公与两个她不知道爱谁或者她都不爱的男人做着。爱情”的游戏。《风景》(刘呐鸥)中准备陪丈夫度过week-end的夫人与她在火车上刚认识的男士“一见钟情”的恋情成为现代都市一道“绝妙”的风景。《礼仪与卫生》(刘呐鸥)中,姐姐因为“礼仪与卫生”把自己的丈夫留给妹妹而自己则和妹妹的情人出去“换换空气”。《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刘呐鸥)中女主人公“未曾跟一个gentleman”一块儿过过三个钟头的爱情规则摧毁了古往今来一切美好的爱情神话。这是发生在现代都市的真实的“爱情”故事。刘呐鸥都市小说创作反映了商业文化对人们精神世界的渗透。市场经济的发展促成商业价值和商品观念的日臻成熟。商品等价交换规则的影响波及各个领域,甚至人们的情感领域。许多人不再相信会有海枯石烂、地老天荒的爱情。爱情成为可以用物质、金钱衡量的一般商品。刘呐鸥和穆时英笔下活跃在跳舞厅、咖啡馆等象征都市意象的舞女如同摆在商店中的琳琅满目的商品时时在用她们妩媚的外表吸引着那些。朝圣”的人们。
穆时英是个非常敏感的都市作家,他在刘呐鸥开辟的“新感觉”道路上飞速前进,并很快以他创作的实绩超过了刘呐鸥,从而赢得了“新感觉圣手”的美誉。但他编织的爱情“传奇”并没有摆脱海派小说的模式。他的《圣处女的感情》、《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和《骆驼·尼采主义者与女人》等小说都是把主人公置于咖啡馆或探戈宫中进行情感和肉体的交易,这些主人公女性形象是作者目光投射的焦点。“这些活跃在咖啡馆、舞厅和跑马场的尤物形象可以被理解成男性作家的一种臆想,也可以被读解成是城市物质魅力的载体。也因此更加速了城市中不可避免的商品化进程”。小说作者以“看者”的角色如同站在黑暗的城市的一角偷窥着“被看者”的隐私。《被当作消遣的男子》中有这样一段描写:“第一次瞧见她,我就觉得可真是危险的动物哪!她有着一个蛇的身子。猫的脑袋,温柔和危险的混合物。穿着红绸的长旗袍儿,站在轻风中,飘荡着袍角。这脚一上眼就知道是双跳舞的脚,浅海棠那么可爱的红缎的高跟鞋上。把腰肢当作花瓶的瓶颈,从这上面开着一枝灿烂的牡丹花……一张会说谎的嘴,一双会骗人的眼——贵品哪!”这种对女性身体部位的描写,虽然含着温和的批判,但作者却掩饰不住欣赏的态度。作者如“解剖刀”似的目光把女性身体切割成脑袋、腰肢、嘴、眼等一个个器官,并把它们看成刺激都市人消费欲望的现代商品。
新感觉派都市小说以男女情爱为结构模式“集中展现了洋场男女颓废变态的精神面貌,在精细的描写中流露出微妙的讽刺”这种结构既隐形地模拟着民初鸳鸯蝴蝶派文学和20年代叶灵凤、张资平等海派文人的小说模式,同时它也表明海派文化对新感觉派创作的影响。虽然新感觉派在表现内容上把都市情绪纳入了它小说表现的主题,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海派文学的表现范围,但他们所遵循的这种结构形式同样能揭示海派文化的内涵。上海商业文化的发展引起市民文化的兴盛。市民文化是一种通俗文化。它以日常生活的世俗性消解着精英文化的崇高和诗意。海派小说通常选择普通男女情爱故事作为小说的框架结构,这本身就说明海派作家的世俗眼光。他们不以“匡时救世”为己任,而是以世俗普通男女的情感纠葛,恩怨情仇作为表现对象,叙说着世俗人生的悲欢离合。新感觉派以自己生活经验为切入点,一如既往地实践着海派文学的创作传统。虽然他们以不断变换的视角和新鲜奇特的感觉表现着他们摆脱传统的先锋性尝试。但新感觉仍然逃脱不了“海味”文学的宿命。
刘呐鸥不厌其烦地遵循着一女二男情感游戏的文本结构。如《游戏》、《热情之骨》等等。作者借此不仅表达他对城市现状的批判和对都市人性发展的忧虑,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流露出他欣赏、暴露隐私的欲望。这种颓废变态的创作心理一方面反映了现代都市对人的扭曲,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海派文学恶俗的一面。与刘呐鸥相比,穆时英对都市病态的挖掘更深了一步。他不仅刻画都市人性堕落的一面,而且他还详细地展现现代都市人性格复杂的一面。作品形象本身也在控诉着都市的罪恶。这些作品表现了一定的社会批判意识和人性的发掘,但又往往被自身流露的颓废情调所冲淡,而无法达到更积极健康的审美观照。从《白金的女体塑像》可窥见一斑。谢医师在潜在的病态心理的牵引下,一步步地剥掉他的女病人的外衣。作者用大量的篇幅细致地描写了女病人裸露的病体,借此作者偷窥的欲望通过谢医师的眼睛得到一步步的满足。
施蛰存对平庸现实的焦虑使他把艺术眼光投向历史故事和佛教传说。他力图从历史故事和佛教传说挖掘出具有现代审美意义的艺术传奇。他把神圣历史英雄和佛教高僧赋予了世俗的悲欢,这不仅艺术地印证了他心中所信奉的弗氏理论,而且也从人性的角度把遥远的历史英雄拉回到普通市民读者的欣赏视阈,把一向束之高阁的历史故事给予鲜活的、富有生命气息的现实内容。这其中当然不乏艺术的崇高和尊严。但渴求被广大市民读者认可的世俗愿望也是清晰可辨的。
新感觉派对“现代爱情”的毁灭性描写也是以人们对物质的追求和现代消费观念作为参照系的。商品消费观念的渗透使得都市男女把追逐异性和“消费”异性作为满足自己现代欲望的一个目标。刘呐鸥和穆时英笔下的都市女性往往用自己的肉体作为物质交换的筹码。在她们贪婪的物欲追逐中,“贞操的碎片同时也像扭碎的白纸一样”
(刘呐鸥《游戏》)扔到墙角去了。商业社会创造的名目繁多、光怪陆离的影像宣告了物质对人的绝对胜利。那些被物质奴役的都市人不再相信亲情、友情和爱情,他们认为只有拥有物质才是最可靠的。在这时间拖着人走的社会,只有抓住机会、及时行乐,消费掉一切物质,同时也消费掉生命的价值才符合商品社会的消费规则。新感觉派在极力渲染现代都市人对物质疯狂追逐的同时,也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充满腐败和死亡气息的极具悲剧色彩的审美世界。那是一幅人、物倒置,欲望泛滥、灰暗、抑郁、窒息的都市图景。这影像中游荡着大崩溃前的慌乱,充塞着死亡前的狂欢。这是新感觉派为现代都市摄下的动人心魄的、也最为真实的感觉。但新感觉派对都市现实力图用泛化的感觉和意象来把握,有时甚至有意识地夸大自己瞬间感觉。这种聚焦在形式和技巧的创作必然会拉大小说文本与现实世界的距离,从而使作者只陶醉于自己瞬间感觉所带来的审美享受。这种主要依靠主观感觉所得来的夸张的现实世界必然会拉大与事物真正本质之间的距离。“新感觉派小说力图通过对于令人眼花缭乱的形象渲染,使读者的眼睛略过对‘历史之谜的好奇。而专注于形象本身。形象的意义不在于体现和揭示了历史的主题,而是在于它自身的美和魅力对读者的刺激。”新感觉派创作中的“移情”现象使他们的文本世界在审美风格上呈现出与现实世界极不协调的景象。他们总是用略带嘲弄的情感和夸张性语言来描写他们对现实的悲剧感觉。这就为他们所拥有的悲剧感觉涂上一层讽刺性的喜剧色彩。新感觉派主要通过对现代都市人与物赤裸裸关系的揭露及他们对自己发起的“语言暴动”的陶醉欣赏中完成悲剧性情感的喜剧转换。
新感觉派对现代人的物欲追求有着触目惊心的感受,但他们无能为力,有时甚至是身不由己的。在《黑牡丹》中穆时英借小说人物之口说出了他自己对都市生活的感受:“我们这代人是胃的奴隶,肢体的奴隶……都是叫生活压扁了的人啊!”“比如我,我是在奢侈里生活着的。脱离了爵士乐,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我便成了没有灵魂的人”。现代都市人在人类自己创造的物质面前失去了自我,成了物质的奴隶。这其中似乎隐含着许多对生活的无奈,另外也反映了物质对现代人强大的吸引力。但我们又不能不看做是作者在为自己逃避责任、逃避现实的行为寻找借口。新感觉派在迷恋物质又咒骂物质的矛盾中也不断削减着自己在文学史中的严肃意义。这种自觉与非自觉、理性与非理性的都市情绪决定着新感觉派创作的价值取向,它也是新感觉派创作的一大特色。
新感觉派对现代人物质化这一情绪的表达有着独特的方式。他们往往通过物的拟人化描写来实现的,但这不同于传统描写法的拟物,拟物是把物当成人来描写,赋予物以人的感觉,借以生动形象地刻画事物。而新感觉派则是带着嘲讽的意味把那些没有情感的本然的物质等同于人身体的一部分来描写。如穆时英的《上海的狐步舞》中作者把“街树”“电杆木”“等一切静物的腿”与姑娘们“擦满了粉的大腿”相提并论,渲染了一种堕落的都市氛围。为儿子与父亲的姨太太勾搭创作协调的背景。作者又把“偷溜了出来。的灯光用“处女的”一词作以反讽式的修辞,隐喻式地把都市隐私和都市偷窥隐私的“性格”凸现出来。施蛰存是个创作异常丰富的作家,他不但创作了《夜叉》《凶宅》《在巴黎电影院》等都市小说,还创作了《追》《鸥》等现实主义作品。另外,历史小说也是施蛰存对中国现代文学一项杰出的贡献。他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对历史中的真实人物和事件或佛教传说进行改编。施蛰存借助历史人物传达生命欲望与现代文明的冲突,并肯定了人的欲望的合理性。施蛰存曾在《将军的头·自序》中说:“《鸠摩罗什》是写道和爱的冲突,《将军的头》却是种族和爱的冲突了。至于《石秀》一篇,我只是用力描写一种性欲心理,而最后的《阿褴公主》,则目的只简单地在于把一个美丽的故事复活在我的面前”,欲望与文明的冲突,自古以来就是个悲剧性主题。“五四”时期,中国文学受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也出现了许多表现性苦闷和性压抑的文学作品。如郁达夫、郭沫若等人的作品表现得较为明显。生活在三十年代都市上海的施蛰存并没有对他所熟悉的都市人进行人性解剖,他则借助干历史英雄和佛教高僧来“图解”他的艺术理念。
《鸠摩罗什》塑造了佛教高僧鸠摩罗什欲修正果又爱妻子的矛盾心理,《将军的头》写历史真实人物花惊定将军为了严肃军纪毫不留情地处决了那位冒犯美丽少女的士兵。而他却受着对那位少女强烈爱欲的煎熬,最后竟驱使他掉了脑袋的身躯去见她的意中人,《石秀》是写爱欲与友情的冲突,《阿褴公主》是写性爱与种族的冲突。历史英雄或佛教高僧在人们传统的观念中是一种神圣崇高、令人敬仰、代表着成功的伟大形象,而在施蛰存笔下,这些人物内心却充满着无法消除的痛苦,是一些令人同情,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物形象。施蛰存的艺术处理一方面消解了这些人物英雄的或神性的光环,使他们由性格单纯的“神”还原成凡俗的栩栩如生的人。另一方面,作者用夸张的戏剧化的情节削弱了作品悲剧性意味而使作品表现出一定的喜剧化色彩。《鸠摩罗什》中鸠摩罗什虽有“十余年来的潜修”,但自从在草堂寺讲道瞥见长安名妓孟娇娘之后就再也无法平静下来。小说喜剧性地在高僧脑海中不断闪现妻子和孟娇娘的幻象。
《石秀》中,石秀在“因为爱她,所以要杀她”的意念下纵容义兄杨雄杀掉他“美艳”的妻子潘巧云。当石秀看着杨雄。破着潘巧云的肚子,倒反而觉得有些厌恶起来。然而当石秀看见潘巧云“这些泛着最后的桃红色的肢体,石秀重又觉得一阵满足的愉快了”,作者用细腻的心理描写把残暴血腥的行为与爱到极致的癫狂状态恰当地统一起来。把悲剧性的恐惧的场面用主人公石秀“愉悦”的心理淡化了。施蛰存借历史小说,一方面传达人的内在心理与人类文明的矛盾冲突,强调人的潜意识对人外在行为的强大约束力量。另一方面,他实际也是用这种“回避现实”的创作暗示人的欲望在现代社会发展中不可低估的作用。现代社会的都市化进程的加快引起现代人物欲的极度膨胀。又从而引起现代人精神、情感和道德等一系列的变化。
新感觉派意识到现代文明是一种势不可挡的进程,同时也意识到在此过程中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以及人的欲望之间对抗性存在的关系。新感觉派以自身的社会历史观不可能完全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社会现象的内在动因,因此,面对这种社会现实,他们愈会产生极度的焦虑和不安。但在强大的都市化进程面前,新感觉派并没有徘徊一隅,自甘寂寞,他们也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人格力量以此抵御都市的诱惑,他们总是在对都市的对抗与依恋中、理性与非理性中消溺着不健全的人生。新感觉派有时清醒地意识到都市对人的排挤以及强大的异化力量,但他们有时又身不由己地惊叹赞赏甚至沉溺在都市声色享乐之中,从而放弃他们严肃的历史使命。这是商业社会对文学艺术致命性的影响和制约所产生的结果。现代商业文化的发展不仅支配
着物质生产领域的市场化,而且它也毫不留情地伸展到艺术领域。当众多作家走出学院、书斋而成为职业作家之后,文学创作已同其他职业一样成为知识分子谋生的手段。在生存压力和市场利益的驱动下,知识分子不自觉地与他们的产品消费者——广大市民达到合谋。为了迎合广大市民的需要。新感觉派在不断向自己文学理想前进进程中不忘苟且广大市民的欣赏习惯、审美趣味。他们深谙消费文化制约下的现世原则和快乐原则,在这些原则的支配下,新感觉派“将现实感发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个流派披认为是中国小说摆脱根深蒂固的永恒崇拜最深湛的尝试。它处理时间的空前大胆之处,并不是它企图寻找一个时间与感觉的断片与生活的连续性之间的秘密,而在于它从这些断片中继续寻找一种分裂感”这就是说,新感觉派打破传统的努力并不仅仅因为传统创作规则束缚了他们创作想象力的发挥,也不仅是他们为自己单纯的创新欲望所驱动,他们还是在为寻找到打动读者的策略而努力。另外,新感觉派总是把承载着都市精神的现代物质景观原生态地呈现在他们文本中,竭力为读者提供一个现实感非常强的,能够打动读者神经的真实世界。同时,又不失时机地把窥视到的都市隐私大加渲染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使读者与作者共同跌入到一个颓废迷乱、令人战栗的传奇世界。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感觉派创作的都市场景和都市人物形象一方面承载着新感觉派的都市批判,另一方面也在无形地实践着新感觉派的商业动机。这种创作动机的下意识转化不仅提示了新感觉派创作的商业化理想,它也昭示了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对知识分子创作观念的冲击。
商业文化在近代的迅速发展不断瓦解着知识分子的传统人文主义理想。近代上海在商业之风的吹拂下,“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传统训世理想也不再是经世不变的立世法则。在商业社会中知识分子地位历史性变化使新感觉派在世俗理想的牵引下,不断背离传统知识分子“经世致用”的为文之道。这种对传统的背离虽然使新感觉派经历了痛苦的心灵裂变,但媚俗所带来的心理补偿不断弥合着他们的精神创伤。新感觉派复杂的创作情绪体现他们所代表的文化精神的复杂性。新感觉派的都市小说总是在大量颓废的、充满肉欲的腐烂气息的描述中直露地表述着对都市机械的、病态的嘲讽。新感觉派就是超脱与俗世、肉体与精神、乡村道德与都市文明的夹缝中,不断由批判走向被批判的怪圈。施蛰存作为一个具有浓厚的古典文化修养的知识分子,古典浪漫的情怀始终萦绕在他的创作中,但世俗文化的强大力量不断销蚀着他浓郁的浪漫与抒情面对通俗文化的强大生存空间,施蛰存不得不变换策略,为平庸的市民生活提供神秘、怪诞故事的刺激,这是他在变化了的现实面前无奈而明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