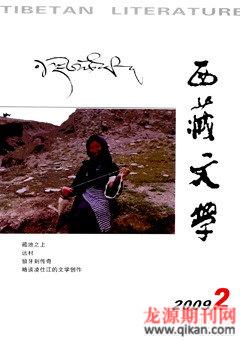碰撞与融合——民族形态的一种诠释
汪 潞
“第一声枪响之后的数月里,只有普布一家人搬出了村子。”这是小说的开头,也是这一声枪响把我带进了《远村》那五万多字的阅读。
远村到底有多远,作者没交代,甚至故事发生的具体时间、详尽的地点,作者也没交代,只是从那些民风民俗里知道这个村庄在西藏。尽管如此,初读之时,还是一下子就被吸引了,虽然觉得小说的人物与情节描写有点弱,那些语句似乎未经仔细的雕琢,有几处甚至不够流畅。故事觉得不甚完整,但那略显粗糙的文笔里却奔涌出一种属于这个民族特有的质感,让我有点惊喜,这大概和作者生长在西藏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样的风格注定不是靠情节与人物来赢取读者。那是什么吸引我呢?我想是一种民族形态。一种碰撞与融合的民族形态。
曾经。处于地理和认知文化边缘的西藏一度是那样的让人觉得遥不可及,它总在不断被审视、被言说,进行文本再创造,但随着旅游业、信息资讯的发展。西藏的神秘光环逐渐褪去,人们不再满足于在它的蓝天下旅游、拍照、猎奇,更多的人开始期待文学的西藏。来复原它那粗犷博大的情怀。这就有了各种文字的细枝末节,它们在共同构筑一个民族的灵魂,从而向人们展示另一种更为真实的存在。罗布次仁就是这其中的一个劳动者,他在耕耘,在展示,在他自己的《远村》里,挥洒汗水。
小说通过对扎西大爷、罗顿、小姑娘德吉、小哑巴等几个特殊人物的多层面刻画,以及那些离奇的故事和亦真亦幻的场景描写来诉说着一个民族特有的生活方式,展示了佛教文明与现代文明,传统与现实之间那种非常微妙的碰撞与融合。让民族性从单一对佛教的归属感、对传统的推崇感,到对真实生活的需求里来回交替出现。
在小说的前半段里,佛教是唯一的一种文化形态,是当地人们生存、认识和活动的方式。扎西大爷就是这种文化形态的化身,当村民从他那里获得经验和预言。使之成为他们生活中赖以生存的精神力量时,这种类似集体无意识的东西让村民们相信诸如:“扎西大爷在达龙寺做僧人的时候,寺庙的饮用水是从后山的泉眼里提来的。有一次。一个朝佛的女人在泉眼的水池里洗了衣物,弄脏了泉眼,结果泉眼里的水干了。寺里断了水,每天僧人们要到下山几十里远的河里挑水。扎西大爷得知情况后,用糌粑捏了两个人,给他们施法。让那两个人动起来,还走进厨房拿起水桶到山下去挑水。后来,扎西大爷在泉眼旁念了一整天的经,用自己的拐杖在原来的泉眼旁捅出了一个泉眼,寺里又有了水。”之类的传说——尽管没一个人亲眼看见。
正是基于这种对佛教文化的信仰,那里的村民“每家每户但凡遇到芝麻绿豆大的事,都要到曾在达龙寺做过多年和尚的扎西大爷那里去问个吉凶,求个解决的法子。扎西大爷也总会耐心地帮着想法子,出点子。”在这里,作者试图向读者展示这样一种形态:当人类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这种原始的被动式的归属需求开始被抽象化和神圣化了,演变成了民族性。民族性一旦在人类文明中获得固定而神圣的位置,人便渐渐臣服于它。
但当小女孩德吉身上发生了一些奇怪的症状,而扎西大爷又无法解释和破译时,村民们“对扎西大爷是否拥有无边法力产生了些许的怀疑。”扎西大爷“能感受到这种威信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威胁。”扎西大爷面对村里发生的很多自己的能力无法解决的事情时,决定要再度去达龙寺修行。在他快要到达时,达龙寺却因突发的地震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废墟。作者以这样的方式隐喻着人内心的信仰方式一旦遭遇到外力的不可抗拒性时,它所构建的崇高地位也有可能瞬间坍塌。
扎西大爷离去的几年间,村里的人已经把他淡忘了,他们依然生括在约定俗成的世界里,却不期等来了现代文明。作者没有繁琐地交代现代文明的产生及传播过程,但安排了一个年轻人替代这一演变过程。他就是罗顿,一个靠打猎杀生维持生活的外乡人。他快要饿死时,无意当中被村上的羊倌救回了村里,这个情节是扎西大爷预见到的。所以他被安排住在了小说一开头就离开了村子的普布家。
在短暂的接触后,村民对罗顿虽有好感,但他们又认为猎人罗顿是不可靠的。“他手上沾满了动物的鲜血”,所以他再好,“村民们还是不敢跟他过于亲近。”这正是佛教文化中“戒杀生”的根本体现。
正因为内心潜伏的这种宗教本性,后来当村民“隔三差五都能看见他在水渠里穿件只能遮羞的短裤子洗澡”时都很担心,小说借助一个“小哑巴在他面前不停地比划”使他终于明白,不是“嘎玛堆巴”星升在空中时,到水渠里洗澡“要是触怒了天神,就会降下灾祸。”罗顿虽然说:“这些都是大人骗小孩子的,天上没有神。洗澡不会带来灾祸。”但“自那次以后,罗顿再也没有到水渠里洗过澡,他总是把水挑回家里洗澡。”这件事让村民们觉得“罗顿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应该跟这样的人来往。”作者似乎想表达这样一种思想:佛教作为一种传统的信仰模式。一种传统文化的积淀,它在某些方面已经同现代社会、现代文明产生了一定的距离,但当他们能相互尊重时,即使不会融合也不再是抵触的了。
自从人类诞生以来,人与自然就交织在一起。人先是由自然力量的威慑而乞求大自然的恩惠,后来却因认识自然到利用自然,这是现代文明产生的必然性。人的谋生不可能完全依赖于自然、完全利用自然条件来生存,人的劳动就是对自然对物象的改变,以便从中获得生存所必需的物品。
小说里让罗顿来做这一切,所以罗顿手里有了一张可以变出一切的魔术布,它浓缩了许多发明创造:变出“孩子们从没有见过的玩具”,“给每个村民的家里变出了一台能从河道里把水引到田地里的大机器”,“罗顿给的药,只要吃上一两片,病情会马上好转”,“他拿出了一种药给村民们说,只要在青稞地撒一点,青稞产量要比往年多一倍”……村民接受得并不情愿,他们无法理解“自古以来水都是往低处流,怎么可能让低处的水往高处流呢?”怀疑使青稞高产的“药”是妖术,“使用这种妖术种青稞会亵渎神灵。”但生活的需求又使他们接受了这一切。这正是民族性遭遇现代文明时的矛盾心理。
虽然村民在罗顿的帮助下过上了好日子,但当村民们听说?在离村子有三天路程的一个山谷中,有一座新的寺院,这座寺院与原来的达龙寺非常的像时,村民心底对佛教文化潜藏的敬仰又油然而生,于是大家一同出发前去朝拜。如同扎西大爷知道罗顿会来到村里。扎西大爷不阻止;罗顿虽不肯信传言,但也不阻止村里人去新寺院朝拜……作者用这种时空交错的写作手法,让两种文化状态默默望向对方,顺其自然发展,没有刻意地抗拒回避。
村民见到寺院后虽一致认同了寺院是扎西大爷修建的,但在他们回村后还是对其他人说,“那座寺院据说是从白衣之邦——印度,被一只仙鹤驮来的,那只仙鹤在空中飞行了九九八十一天,终于找到了那个山谷。”使村民们“都相信了那座寺院是从印度被仙鹤驮来的,后来,就是去过寺院的村民们自
己也相信那座寺院是从印度来的。寺院的来历从村子里传了出去,很快传到了周围和更远的村子里,就这样这个村民们编出来的寺院来历,得到了人们的认可,而这寺院自然也就有了一个很贴切的名字:飞来寺。”佛教的神秘需要古老的传说和神奇的迷幻色彩加以渲染,而它的信徒在对它进行顶礼膜拜之时,更乐意让它具有这样的神秘,所以村民们不认为是在说谎,只是在满足所有人心里的需求,包括他们自己的需求。
忙于劳动创造的那段时间里,罗顿让村民们感到“村里就像是翻开了新的一页,新的事物一件接一件地出现,村民们感到自己脑子一下子没法接受这么多新鲜事物。村民们现在总感到自己太忙了,白天在田地里干活,夜里不是看演出,就要去学习文化知识。村民们每天都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充实感,根本没有时间考虑别的事情。村民们在学习了一段时间的文化知识以后,很多村民自己也可以发明一些小东西,用于白天的生产上。那段日子,村民们的心中燃起了火一样的希望。每个人在干活时,都觉得有使不完的劲,用不完的力。”在这样的日子里,人的生命似乎变得充实了,村民整天为获得更多更好的生活而忙碌着,在那一时段里,他们找到了碰撞之后的融合。
“村民广播站”作为现代文明标志之一的重要传播媒介在“远村”出现了。它让村民们足不出户就能了解全村的大事,还“感到他们和罗顿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许多。”甚至会说“这些天没有听到罗顿啦的声音,心里总觉得空荡荡的,根本没有心思呆在别的地方,办完事急匆匆地赶了回来,还是我们村上好哇,我都已经离不开罗顿啦的声音了。”
这里暗示着现代文明已经给村民养成了在固定时间必须吸收外界信息的习惯,当他们意识到传播的重要性时,他们已经成为了深刻的社会人,因为社会最基本的意义就是传播。如果传播不定时,或者传播常常中断,那么人们就退出了社会的层面。
罗顿因为“变”出了铁犁、药物、抽水机、银幕、广播等,受到了村民敬重,但当村里的人说“您到我们村上也有些年头了,这些年来您身边一直没个知冷知热的伴儿,想给您找个伴儿”时,他也有了孤单感,一连七天没有出门,“心中感到自己是那样的无助,像是被什么人把他孤零零、赤裸裸地抛弃到了这个村子。而身边的一切在顷刻间变得暗淡无光,每一件物品都似乎是孤立无助的个体”。于是他梦见自己成了新郎……这是小说里不多的人物内心描写之一,它折射出人们内心对人性温情的渴望,这是任何一种文明到来都无法替代的。
小说结尾部分,一个“身上带着格萨尔王的神气”的百岁老艺人出现了,当他为了感谢村民的热情款待而“在收割好的青稞地里,整整讲了三天三夜的格萨尔”沉沉睡着后,醒来却听见“耳旁还在响着自己讲的格萨尔”。原来是村上的广播里在播放他的声音,“他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他那心中固有的格萨尔王,朝着草原的尽头飞奔而去,消失在了地平线上。他搜索起在脑子里原有的格萨尔王形象,可那个形象在他脑子里像被人扫去一般消失了,他怎么也回想不起来。那一瞬间。他自己也说不清是害怕,是失落,还是别的什么,只感到脑子里一片空白,再也没有一丝的力量从床上站立起来”。正是这种瞬间的失落让老艺人觉得自己不再具有神奇的能力,于是他“用了一天的时间把他所能说的格萨尔故事传授给了哑巴”,他似乎想让一个不能发声的人固守着这份传奇,但哑巴十年后忽然开口“我昨晚梦见格萨尔骑着一匹白马来到我家,早晨醒来时,我能说话了。”老艺人怅然离去,小哑巴却可以开口说长篇故事,作者以这样一种荒诞的方式告诉读者: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精髓,只能是愈久弥香,无论经历怎样的变迁,它总会以自己的方式留存给世人,而不会在碰撞中轻易消亡。
作者还通过“曾让那一带村民感到骄傲的德吉女活佛最后成了凡人”。“圆寂的活佛原来是扎西大爷,”这样两件事告诉读者:凡人是具有佛性的,是有获得一切智慧与觉悟的可能,因此,人人都可成佛,而佛的根基却是凡人。
小说描写了佛教文明在夕阳余晖照耀下的宁静与传统人伦秩序美的和谐,也展现了现代文明带来的勃勃生机与人类内心的某种失落。
到底是佛教文明与传统阻碍了现代文明进步,还是现代文明催生了佛教文明的繁荣?以及对传统的怀念?作者没有回答,他只是真实地描写了一个民族对外来文化抗拒与接受并存的心态,没有直接批评或赞美哪一种生活形态,给读者留下了自我消化的空间。小说里揭示的冲突,其实只是人类天性的一种碰撞,“碰撞”带来破坏与生机,“融合”带来发展与可能产生的危机。正因为这样,所以人类才一直进步。生存和死亡,本能和道德,孤独和虚荣,这些都无一不留在人类的心底,只要有人类的存在,那么这些碰撞与融合的过程将永远存在,他们共同推动一个民族、—个社会向前迈进。
责任编辑:克珠群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