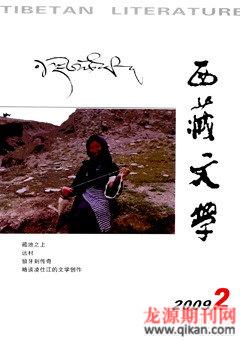狼牙刺传奇(外一篇)
官晓丽
阳光照临时,河水正欢腾。那时,我眯了眯眼,看看远处的村庄,灰色的静静的村庄。像传说中的那样,那里有我美丽的姑娘卓玛啦。她每天起得和家里的花母鸡一样早,天边还挂着月亮灰白的影子时,就挽起长长的乌发。背了水罐来到我面前。她舀起一瓢又一瓢水,直到灌满了她的水罐。她转侧背起那沉沉的水罐,水罐溅出水花落在她黑色的裙沿上时,我才瞧见她穿了一双高帮胶鞋,灰蓝的底色被汗渍、泥土以及灰尘掩盖,两只鞋的鞋尖都破了。露出毛边以及美丽姑娘的大脚趾头。她毫不为大脚趾感到羞赧,居然大声唱起歌来。拖出长长的尾音,绕着弯儿一样的歌声在空气中久久不肯散去。河边来了个小伙子,牵了匹马却心不在焉。马儿走到江边已经停住,他却忘了河沿不如自家房沿那么毫无遮拦地宽阔,几乎失脚落进河水里。姑娘停了歌声,向他吐了吐舌头笑起来。
我又眯了眯眼,看看自己的脚下。草发芽了,它们戳破了冬日灰色土地的顽固,一个个昂首挺胸地得意。我是花儿,一朵即将开放的淡紫色的狼牙刺花,我有理由比它们更骄傲。于是我也把头抬起来,假装看不见它们。它们开始嘀嘀咕咕嘲笑我,说我本该退到远处的山脚下去,那儿才是我安身立命的地方。我知道,那里的确有成片的狼牙刺生长着。可是命运让我在这儿扎了根,我就没理由退却。
最近我发现了姑娘卓玛的秘密,这更让我觉得有趣。她一天比一天起得早,而且梳头时没忘了梳顺后给头发抹点儿酥油(酥油还不够人喝呢,她居然偷偷往头上抹,要是被阿妈发现,轻则挨骂,重则挨打或罚做更多活),挽起盘好后的头发油亮亮的。她走路时故意弄出些声响来,比如踢地上的石子,唱歌,不停地摇晃背上的水罐,等等。这小妮子的心思傻子都能明白。然后有一天我就看见牵马的小伙子帮她背了水罐,两人一路做的什么事,大概只有水罐知道。到了院子前,听到院子里黑狗的吠声他们就得分开时,水罐只剩半罐水了。
这条河叫雅鲁藏布江,一条性格多重的河流。它一时很乖觉,水清清浅浅的,连水花儿也懒得起一个;一时又非常狂浪,浑浑地扑向河岸。有一年,它甚至淹没了河岸边的一片柳林。那可是一片老柳林,是我妈妈的妈妈还在山岗上晒太阳那阵就生出来的一片柳林。后来我被什么风卷到这儿落户时,河边又有了一片柳林,瘦瘦的身子骨儿,腊黄腊黄的脸儿,能成什么气候呢!在我怀想老柳林的那几年里,这片小树突然就改了腊黄脸和瘦身子骨,枝叶摇摇摆摆地互相寒暄致意起来,渐渐有了些树林子的味道。我晓得这是为什么——栽下它们的那些人旱季时隔上个把月就来浇一趟水。一年四季有水滋润着。想长不好都难。柳林子离附近的镇子不远,离远处的村庄也不远,成了镇子里和村庄里人们经常光顾的地方。镇子里的人喜欢来这树下乘凉,喝青稞酒玩骰子;村子里的人喜欢到这儿歇息,离庄稼地近,累了就到树林子里躲那又狠又辣的太阳,顺便吃了糌耙打个盹儿再去地头劳动。
夏天的时候,我可没地方躲太阳,只能支棱着脑袋任它烘任它烤,久不久的,就晕起来,做起了白日梦。我梦见一个小女孩儿,十岁多的光景,骑在一堵残破的老墙上。朗朗有声地读什么“桂林山水甲天下”、“草原英雄小姐妹”,统统是些我不知道的人和地儿。她读了那么一会儿,就合上书翻身下墙,墙下有几分地,种了些胡豆和蔬菜。地的前面是一排铁皮顶的平房。她一路蹦蹦跳跳进了一间平房,一会儿又拿个铁壶出来。给窗台上的花浇水。窗台加上电瓶做成的花盆的高度(那时大家都喜欢拿废弃的电瓶或空了的铁压缩饼干盒做花盆),使她只能搭着个小板凳上去浇,颇费力气。和那些花儿比起来,我惭愧得要死。白色的臭海棠急不可耐地开了一朵又一朵,还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的美,非得弯个身子把头探出窗台来;小小的蝴蝶花一丛丛偎在一起,看起来不招摇,可是那花瓣醉人的玫瑰红实在妖娆得过分;竹节花儿直棱棱地开了几朵粉色花,不用宣布都看得出来它有多骄傲。我和这些开在盆里,天冷了屋里藏着天暖了窗台上沐浴阳光的香花嫩草真是没法比,一难过,梦就醒过来了。
卓玛好久没来过了。我并非想她,只是对她和牵马的小伙子的事感到好奇。我有一颗好奇的心,也亏了这样,否则怎能忍受这枯燥的日子。没有卓玛的日子,我只能胡思乱想。有时望着天边的几朵白云,我就心想自己是那个梦中女孩儿,晚上睡觉时有个大眼睛的洋娃娃陪着。她每天读书浇花,生活快乐吗?小镇很小,向东一条路。向北一条路,这就是小镇的全部。起风时,有糖纸吹到脚下,所以我知道镇里的人有糖吃。其中一种泡泡糖纸我见得最多,薄薄的红色长方纸上画了一个扎着马尾巴的小女孩儿。嘟着小嘴吹出一个大大的泡泡来。我梦里的女孩儿就是她吗?起风的夜里,白铁皮的屋顶被刮得咣啷咣啷直响,铁丝串起的窗帘布没拉严实,漏些白的黑的影进来,她梦梦魇魇的,觉得是些精灵鬼怪。忙抓了被角盖住眼睛。一个床上两床被子盖着四个孩子,分别是她的哥哥和两个妹妹,第二天起来两床被子往往扭在一起,弄得不是这个感冒就是那个肚子痛。妈妈有一夜起来给四个孩子盖被子,忽然生了气,给了哥哥屁股上一巴掌。她怕这一巴掌哪一天会落到自己屁股上,所以只敢小心翼翼地抓了个被角盖在眼睛上。
我才不在乎黑夜和白昼。对我来说,脚下的土地就是我坚持的位置。我开花的时候算不上美,不需要那么多人带着欣赏的眼神来看。我的花枝上长着尖尖的针刺,花穗散发出苦味,飞虫都避着我。这是多么清静的不受打扰的生活。秋天第一次打霜,那些半尺高的茅草就低了头,可我还这么硬朗,花儿结出的种子一串串的,像野豌豆的豆荚,干透了一破,我也就跑下地来。真希望风来得更猛些,送我去更远的地方。
若干年以后,我再次回到了山脚下,离村庄远了些,离镇子近了些。我从前所在的位置,被修成了一座铁桥,连接着江的此岸与彼岸。真庆幸自己换了个地方,否则来来去去的汽车和轿车扬起的尘土、发出的吼声真叫够受。在我离开前的某个日子,卓玛又出现了。她还唱从前的老歌,戴着从前那对黄铜色的耳环,所以一来我就认出了她。以我们的寿命计算,她离开了有半辈子那么长。奇怪的是她似乎一点也没有老去,那身脏兮兮的黑袍换成了天青色裙子,前边系个五色邦锦,脸上的高原红也褪去不少,正在河边抖落出一麻袋一麻袋的土豆来洗,旁边停着个三轮拖拉机,“嗒嗒嗒”地叫了半天才消停下来。拖拉机上跳下个十一二岁的女娃娃,穿了身红色校服。拿个皮球在河沿上踢,踢着踢着皮球落水了,她慌慌地喊“阿妈”、“阿妈”,卓玛就立起身来用根树枝把落了水的皮球勾回来捡起递给女娃娃。看得出来,那个牵马的小伙子没让她受什么苦。我还记得从前看见的那些老阿妈,头戴鲜艳的方格围巾,黑红黑红的脸庞布满岁月的沟壑,脸上贴着伤湿止痛贴,像故意打上的标记一般。好在她不曾这样一副打扮出现。我喜欢美的东西永远都美,当然不美的后来又变美了就更让我欢喜了。土豆洗得差不多
时,来了个中年男子,我猜他就是那个牵马人,只是比起从前瘦挑的身子发福了,头发也剪得很短。红衣服的女娃娃跑到他跟前,他环手把她抱上了拖拉机,把一袋袋土豆搬上去码好,带着卓玛开上那玩意儿就离开了。
我呢?这些年就这么过去了,悲伤和惊喜都无从谈起,因为我也就是一棵狼牙刺,跟随四季花开花谢,有时也随风起舞。像一首老调《风中之尘》那样,恬淡不过,忧喜自知。我要说的是,我的前身是那棵江畔的狼牙刺,我的现世是它的一粒种子。一只笨鸟不小心误食了我,把我带到了山脚下的烈士陵园后边。我们野生植物和动物是有所区别的,他们会感觉到死亡,而我们得到的总是新生,每一粒种子都会继承它前世对生命的全部感受。现在我来到这里,周围的一切都有些陌生。当八瓣梅开成一片片的时候,学生和成人陆续来到这里扫墓,一人胸前一朵白花。烈士陵园里立着许多石碑,碑上的文字我统统看不清楚。人们把这些碑后躺在墓里的人叫做“国殇”、“烈士”,大意是他们为国捐躯,凛然悲壮。我不认识他们,不过我却喜欢起这些人来,他们真安静,无所怨尤地远离故土,在这儿安息,陪伴着我。
我梦中的那个小女孩儿呢?我牵挂她,是觉得和她有缘,要不她怎么会一再出现在我的梦境中呢?有时我梦见她长大一些了,学生头改成了两条辫子;有时她又很忧伤的样子,在雨天的屋檐下沉思默想。她原来总骑在上面读课文的那堵老墙也不见了,墙外修出一条水泥大马路来。墙里也没了自留地和种在自留地里的胡豆、蔬菜,自然那排铁皮顶的平房也不见了,菱形的花坛、高大的杨树和一大片草坪代替了以前的一切。我疑心再也梦不到她了。
有一天天气不错,阳光温和,一丝风也没有。我正很无聊,突然觉得眼前光线一暗,有人来了,就站在我跟前,戴了副窄边黑框眼镜,卷发上别着两枚黑色水钻发卡,三十来岁光景。她空着两手就这么站了两分钟。在这两分钟里。我眨巴眨巴地盯着她,她不就是那个骑着土墙读书的女孩儿么,昨就跑到这儿来了?到底是我做梦还是她在做梦?没等我想明白,她就把我从我的枝梗上摘了下来,握在手里拿走了。
我真想惊恐大叫,不知道她要把我怎样。
我们走过一段石子小路。走过一段松柏掩映的水泥路,走过一行行石碑,在一块灰白的石碑前驻足。她轻轻地轻轻地把我放在了石碑前。我抬眼看看,石碑中间刻着“童华”两个字,该是一个人名。人名左边有两行竖排文字:原边防一营二连副指导员,四川省重庆县人,生于1939年,牺牲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我觉得自己的身子有些湿润了,原来是她的眼泪。她半蹲半跪着,啜泣着小声地呢喃说:童伯伯,我代表阿姨、童烨和我爸爸妈妈来看你了。你知道吗?我们离开了那么久。可是我们的心一直都没离开过这里。童烨常念起你。她现在一家都在藏北,生活工作各方面都挺好,你不用担心。现在,地区变化真够大,我差不多找不到以前读书、生活过的地方啦。你现在住的这个地方,比起我们上学那会儿,也修整得更宽敞美丽了,种了好多树,栽了好多花。你不是很爱花草的吗?童伯伯,我爸妈已经退休回内地了,现在他们的生活也非常好。有时还去探望探望阿姨呢。阿姨身体还算可以,就是听见我们说起你时她总要掉眼泪。童烨也是这样,有时想爸爸想得好厉害,我爸爸就和她开玩笑,哄她喊他一声爸爸,她一喊他就笑起来答应,还说自家女儿可没童烨这么乖这么逗人喜欢……
人类的眼泪成湿而略有温度,每一颗眼泪落到我身上时,我就颤动一下,承受它难言的力量,觉得自己的生命并未一步步走向死亡。蓝蓝的天空下,是这片远天厚土,是我静默雄伟的家乡,是那些可以随风远扬的生命的种子。
作为一棵狼牙刺守候在一块石碑前,我终于完成了自己一生的使命。
2008年6月22日
献给我的第二故乡西藏
妞妞我爱你
妞妞属牛,天生爱哭。刚落地时,她夜里哭、白天睡。妞妞哭起来,真是令人手足无措。她眯紧了眼,皱起了眉,咧着嘴一口气能哭上半个小时,任我们怎样搂怎样哄都停止不了哭闹。
涛人说,“如果未生之时了解了凡闯的苦难,我们恐怕要失去降生的勇气。”妞妞为降生到凡间而害怕吗?
哲人说。“悲伤是凡间的产物,天堂是没有悲伤的。”妞妞预感到凡间的悲伤了吗?
看着襁褓中的妞妞哭得那般撕心裂肺,我也跟着落泪。她那么娇弱,小小的身子在薄被下不停地扭动,像要努力挣脱一切令她感到不爽的束缚。怕她哭得太久把身子哭坏。于是我找来医生为她做检查。
“孩子很健康”,医生看了几张检验单后说,“是不是你们给她穿、盖得太厚了?”
按照医生的建议,我们为她换了薄的棉布衫,不再总用小棉被紧紧裹住她,哺乳时也更注意卫生和喂的次数,又把尿不湿改换成了棉尿布,可是妞妞爱哭如故l没了小棉被束缚的她,哭起来居然手舞足蹈,眼泪顺着眼角滚落进油亮亮的短发里,湿了脖子,湿了小枕头。我们兀自的心急如焚。她却兀自的哭得来劲。
哲人又说,“上帝把两头掐掉,只把之间那一段平凡展示给我们。”那被掐掉的两头说的是人的生和死。
虽然找不到妞妞哭闹的原因,我却相信她哭得有理由。那理由上帝只是不展示给我们知道,但妞妞一定知道。她不哭时,黑楚楚的大眼睛扑闪扑闪地盯住了你看,那目光真够清灵澄澈,使你不得不相信生命里的确有许多未知的神秘。
妞妞的哭永远是我们心上的痛。
记得有一年出差,可以顺路回家探望父母和女儿。快一年没见着妞妞的我一路归心似箭。想象见到一家老小时的情形。听人家说,有的孩子久了没见父母,等见了,只会喊作叔叔阿姨。下了车,远远望见一个趿了凉拖鞋、穿着自底粉花裙的小丫头朝我奔过来,一边跑一边喊“妈妈!妈妈!”我泪眼婆娑地搂住扑进怀里的妞妞,她身上有一种好闻的熟悉气息,让人想要把她永远搂在怀里去疼、去爱。
妞妞拉着我的手,一路蹦蹦跳跳引领我往家走,两只高高梳起的羊角辫也随她一起跳跃,宛如一对小花蝶在眼前翻飞。离家那么久,可妞妞还是那样依恋我,使我觉得做母亲是件很幸福的事。她坐在我膝上,把头埋在我怀里,用手一再地抚摩我衣服上那一排亮闪闪的缀饰,一边拿眼睛觑我。她在偷偷观察我哪!仿佛要确证紧紧依偎着的人就是她的妈妈。我们相互看看,又相互笑笑。我心里涌起了酸楚,她却是满心的欢笑,全然不去想几天之后的离别。她小声问,“妈妈,你耳朵上挂的什么呀?”我答是耳环。她摩挲了半晌,才说,“妈妈,这个耳环不够大。等我长大了,赚很多钱,买一个大大的耳环送给你!”说着,还用手比划了一下她要送出的耳环有多大。
临走时,女儿执意要送我。看着她晴转阴的小脸,大眼睛里噙满了泪水,我只好强作欢颜,告诉她很快又能见面。她紧紧拉住我的手,一声也不言语。上车前的一分钟,却趴在我肩头,呜呜地哭了起来。大巴车开动了,渐行渐远。摸摸肩头领角,湿湿冷冷的一
片是女儿的眼泪。好多年里,那种痛的感觉还停留在心里,挥之不去。
在不断的相聚与离别中,妞妞一天天长大。她还是爱哭依旧,还是人小脾气大,还是为了些在大人眼里毫不起眼的事情而哭闹。在相聚的日子里,她和最爱的爸爸一起嬉戏玩闹,一时高兴,一时又恼了,哭起来像晴天里的炸雷,不过雷声大雨点小,顷刻也就过去了。在我们相互不得不分离时,她曾经几次在空姐的带领下一人乘飞机返回内地,因为紧张而忘了和在远处看她离去的爸爸妈妈说声再见。她不是不再为离别伤心,只是渐渐知道,孩子大了总有一天要远离父母独自去飞翔。
我们把妞妞像放风筝一样转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去上学。听她在电话那头哭,我们在电话这头心痛、伤感。电话线就如风筝线,风筝飞得远了,那线就牵着人的心。因为她不在跟前,就常常想到她在跟前时的种种情形。
四岁的时候,妞妞来西藏过暑假,便陪我一同去茶园会朋友。朋友穿得极时髦,最称奇的是那一头蓬蓬松松的头发,弄得我以为认错了人。女人之间的恭维。让孩子听了都难过。在回家的出租车上,女儿问我,“那个阿姨明明是丑丑的,你为什么说她好看呢?”我跟她解释。见了朋友说她长得不够漂亮,朋友是会不高兴的。说她好看那是一种礼貌。妞妞很不以为然,她掷地有声地说,“我才不要和丑丑的人一起玩!见到了丑丑的人,我就说,你好丑哟,说完了我就跑,让她追不到!”
有一段日子我总是加班,回家很晚,先生不理解,便爆发了家庭战争。女儿见我哭得伤心,到跟前来劝慰我说,“妈妈,你以后别去单位上班了,从明天起,去当空姐好了。”当空姐是女儿的梦想。她觉得空姐漂亮,招人喜欢。我听了破涕为笑,说,“妈妈老了,妈妈也不够漂亮,不能当空姐。”她很执着地说,“你不老啊!你天天吃萝卜就能漂亮起来。”我问她为什么?她说。“你不是每天吃饭都告诉我,多吃萝卜,多吃蔬菜,吃了会长漂亮的吗?”
五岁的时候,她把我千里迢迢从西藏带回去的玉质弥勒佛象从脖子上取下来还给我,并且说,“妈妈你又骗人!你说这个大肚子菩萨会保佑我平安健康,可我还是经常肚子疼,还发过烧哪,它一次也没保佑我!”
妞妞看世界,就是这样与我们不同。她拒绝一切与她本性相违的东西,而我们已经学会去笑媚地接纳。所以,周国平称每个孩子都是圣哲、诗人。孩子的纯真衬得我们世故、衰朽;孩子的率真与自然流露出生命健康的本色,而我们已经渐悟“人性”,远离了神性,像丢失了通灵宝玉的贾宝玉,慢慢变得浑浊起来。
妞妞爱美,正如所有的女孩儿一样。一岁半时,她背着我,偷偷给自己画口红。人太小,手还不能捏稳口红棒,于是把小嘴巴画成了红红一团的小猪嘴。这还不够,她把眉毛也涂了口红,跑出来给大家看。我们全抚掌拍手地笑了,她却以为自己画得很美,咿咿呀呀地唱了起来,自得其乐。后来上幼儿园了,喜欢和我一起欣赏电视里的时装表演节目。她看得很入神,还不时和我讨论哪个模特漂亮,哪款衣服最合她的心意。因此,她对自己的穿着很有主见也不足为怪。有时为了穿哪件衣服上学,她能和我们赌半天气,就因为我们替她拿了主意。也许是电视节目启发了她,有一天我进屋,发现她端坐在椅子里,正全神贯注地拿剪刀在剪什么东西。定睛一看,天呐,她正一刀一刀地剪着自己身上的衣服!我上前一把夺下剪刀,再细细地察看,衣服的前襟已经被剪出了许多“精致”的小眼,下摆也一绺一绺地,颇有波西米亚风格。问她为什么要把好好的衣服剪破,她说那不叫剪破,那叫剪好看,因为她觉得以前这件衣服不好看。这样的回答并没有超出情理太远,我们也就放弃了惩罚她的想法。
妞妞爱照镜子,在镜子里做各种鬼脸,把头发一会儿梳上去一会儿又放下来,要么用卡子卡着,要么就用头花儿扎起来。她有很多发卡和头花,她把它们放在一个纸盒里。圆的、方的,绿的、红的,各式各样,琳琅满目,却排得很整齐。纸盒也就成了她的宝贝,不许别人乱动,如果同她生活在一起的小哥哥(舅舅的孩子)动了那纸盒,她简直要跳起来和他吵。妞妞也很爱穿裙子。初秋时节,天渐渐转凉,外婆要她回屋换了薄裙,以免感冒,可她硬是不肯,而宁愿在薄裙外罩上一件外套。每每春天才来,她又急不可耐地要大人把她的裙子从箱底翻出来要穿。“好个爱臭美的妞妞!”我们都打趣她。
当叶利钦发现他女儿身上呈现出他的某些特质时。他认为他的生命得到了最好的延续。生命科学家说,父母爱子女是基因遗传造成的,因此父母之爱并没有更深的奥义,只是物种遗传的本能。我们爱自己的子女,也许是因为他们继承了我们的某些特质,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也许因为那本来就是一种本能,犹如所有低级动物都会照看自己的子女一样。妞妞的举手投足令我喜欢,她的种种喜怒哀乐让我感同身受,同时又使我猜想我的婴幼儿和童年时期大抵也会有相同的表现。
她喜欢小动物和我如出一辙。那一年为她买了一只皮毛黑白相间的荷兰猪,取名“叫叫”,因为小家伙不习惯单身生活,成天的叫。她于是就成天侍候起叫叫来,一会儿拿饼干喂它,一会儿又去厨房取来青菜叶子喂它。我们发给她的糖果,她也省下来给叫叫吃。叫叫有尖尖的门牙,所以我们不准她抱它玩,可她还是趁人不备把它从笼子里抱了出来,结果叫叫溜下了地,一家人满屋地找,才从沙发下把它找出来。一个月后,叫叫死了,我们偷偷把它的尸体处理了,回头才告诉妞妞。妞妞哭了,她为失去了一个好伙伴而伤心。很多天里,想起叫叫,她依然难过。为了填补失去“朋友”的空虚,我们又买来两只虎皮鹦鹉。她又高兴了,没事就去逗弄,还把指头伸进笼子里让鹦鹉啄,恨不得自己也变成鹦鹉和那两只鸟挤在笼子里。本来爱清洁的先生,看着阳台上羽毛飘飞的小“动物园”,闻着鸟粪散发出的臭气,哭笑不得。他自嘲道,自从有了女儿,家就变成了动物园!没错,从那以后,我们又买过小白兔,北京犬。北京犬换季时就换毛,换毛时家里到处飘荡着纤细的狗毛,有时呼吸,连鼻子里都能钻进狗毛。妞妞可不在乎这些,她把小狗当亲人当伙伴,没事就抱在怀里,牵了它在院子里疯跑,带它去找小朋友玩。她给它取了个响亮的名字——乖乖。爱屋及乌,我们也就把乖乖当成了自己的又一个孩子。
妞妞渐渐长大。她依旧内心敏感,天真烂漫。有一次先生望着熟睡中的妞妞说,这孩子傻气得很,真是像你。她要总这么傻里傻气的,将来长大了可怎么办!我笑笑,觉得不以为意。孩子终归是孩子,她将来长大了,会有她自己的选择。不知怎么的,我就是相信她。觉得她长大了一定是个特别的姑娘,能笑着看这个世界。因此,我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责任编辑:刘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