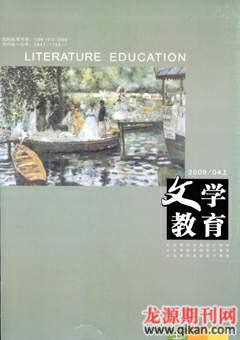以阎连科作品为例谈乡土世界人性的异变
方 培
文学即人学。文学归根到底是对人这个客观世界个体存在的终极追问,人性异变更是“人”学的核心命题。在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涌现出展示人性在两极世界——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中的生存境遇的作品,前者如老舍的《骆驼祥子》已成经典,后者如余华、莫言等早已声名在外。而作为当代文学中的一员,阎连科更是以一种独特的视角,一种越轨的叙述风格和笔调展示了人性在乡土世界中的残酷异变。在他的文本中,乡土世界是被剥去了诗意外衣的赤裸存在,人在这个现实地狱更是完成了从肉体到灵魂层面的痛苦畸变。
一、肉体怪象隐喻的荒诞存在
深入阎连科的乡土世界,直面读者的,首先是文本中扑面而来的肉体怪象:开棺虐尸、白花花的天灵盖、一只耳朵、一颗眼睛、一条舌头等实物的惨象层出不穷。因此,在他的作品中,人得以存在的载体以各种各样直接而又惨烈的残缺方式诉说着肉体的异变。《年月日》中先爷以自己的躯体作为玉蜀黍延续生命的肥料,人的生存自觉让位于植物的生存;《受活》中村庄中上百个残疾人组成的“绝术团”上演的荒唐的故事,“导演了一幕乡村社会畸形梦想的一次聚焦”[1];《耙耧天歌》中尤四婆对尸体以及自我肉体的戕残,都在言说着乡土世界中肉体这个物质存在的显性残缺。
是什么使得创作者使用如此直白的语言描写肉体的缺憾?应该说,在这些文本中,作者通过一系列怪异的肉体和实体构建了一个荒诞不经的存在系统。这个存在是以不完整的人体来建构的,人体在作者的文本世界中一定程度上已经被物化,物化为容器、工具、手段甚至图腾。《年月日》中肉体物化为一种容器,但它是内涵了能使他物延续生命的“有质物”,而在玉蜀黍焕发蓬勃生机的同时,主人公先爷的生命似乎变象地转移到了玉蜀黍上,即肉体腐烂了,人的“精气”还在;《受活》中更是残缺肉体的一次大狂欢和大表演,不圆满的个体聚集到一起似乎幻化成了具有圆满内在的表象残缺群体,而这个群体也被物化成了一个获取财物的工具。整体中的个体通过相互之间的密切联系与协调合作使这个群体发挥了巨大效用,获得了大量的钱财;同时在这个文本中,一具更具有象征意义的肉体更被上升到了图腾的高度。开始列宁的遗体仍是受活人获取利益的手段和方式,但在长久的渴望和期许中,这具遗体被抽象为概念化的一幅美好图景的标志、一个光明的希望,成为了被崇拜的图腾。而祈福于这个图腾,村民们就能摆脱现实自身的残缺,获取物质生活的圆满。
因此,概括以上的文本分析,通过作者对肉体残缺的展示,我们能觉察到作品背后所隐含的主题意义——对肉体的崇拜。无论是先爷、尤四婆这种以个体一己之力来改变现实既定命运,还是受活庄残疾人以群体的合力去争取生存境遇的改善,他们潜意识里都暗含了一种信念,即肉体能帮助“我”或“我们”去改善或解决当下面临的难题。而在这些作品中,几乎都是以成功佐证了他们信念的正确:先爷的玉蜀黍上“七粒指甲壳般大小、玉粒一般透明的玉蜀黍子”[2];尤四婆四个变得“和村人、和耙耧山人一样精灵了”[3]的儿女,残疾人绝术团取得的巨大成功。但是在另一层面上,这些乡村人物对肉体崇拜的表达方式却又是“变态”的。先爷将自我躯体活埋,最后“他整个身子,腐烂得零零碎碎,各个骨节已经脱开”[2],玉蜀黍的根须穿透他的胸、腿、手腕,红根扎在头骨、肋骨、腿骨和手背上。《耙耧天歌》里尤石头“被二妞熬喝剩下的一条腿,和薄淡模糊得如压根儿就没有一样的脸”[3],尤四婆自我取下脑子熬汤等等。因此在内心灵魂对肉体的神圣崇拜与外在表达方式的矛盾对立中,作者就借用肉体的诉说颠覆了固有观念中乡土世界人的诗意美好。
二、灵肉纠结背后的人性扭曲
但是作者不仅仅停留在对这些近似“酷刑”般折磨的肉体残缺的展示中,而是通过肉体深入到灵魂,通过肉体与灵魂的辨证关系来折射出乡土社会人性畸变的内核——存在的虚无和荒诞。乡土世界的苦难性与年年月月似曾相识的生存境遇已逐渐消磨了乡村人生命的自我存在感,“活着”已成为一种本能,近似于动物的生存行为了。而在孤岛似的乡土世界中人群也逐渐丧失了支撑自省意识的价值支柱与抑制人性异变的道德准绳。那么以何种方式证实自我的存在,以抵消存在的虚无感?阎连科作品给予人们的方式就是对肉体的折磨,通过这些可感可视的近似自残的行为来减轻灵魂扭曲的撕裂给人带来的生命痛感。这是缺乏话语天赋和权利的乡村人所能自慰的唯一的发泄渠道。
进而深究人性异变的深层根源,我们发现正是乡土题材小说永恒的母题——生存。生存包含着肉体生存与灵魂生存。一方面,自我的物质缺乏(肉体的残缺和生存资料的贫乏),直观、显性、可感知,所以造成了一种坚强的麻木。而另一方面,人性层面的灵魂残缺却隐性、不可感知,因此成为人性灵魂的无意识残疾,造成了人性的异变。在阎氏的所有作品中,主人公直面的就是生存这个基本问题。《年月日》中先爷活埋自我躯体以求保留整个耙耧山脉唯一的玉蜀黍苗的“壮举”,《耙耧天歌》中尤四婆削骨治儿女,《受活》中受活人以自我残体上演的生命救赎……一切的荒诞行为追求的都是生命延续的可能性,而先爷们所拥有的强大的生存欲望就促使他们采取种种极端的行为去与自己的“命”抗争。尽管天命所带来的苦难无穷无尽,但人们从不曾放弃。
但是阎连科表现生存的独特之处正在于——通过具有异质性的残缺肉体怪象的聚集来整合泛化为一种常态,继而表现人性的变异。在阎连科的文本中,从肉体层面至人性层面,残缺已经遍及章节段落之间,如空气一样弥漫。日常生活中非常态的怪象、异态在其文本中已经泛化。在其构建的文学世界中,这些残缺已经变象地具有了常态性,换言之,即异态泛化性。局部层面的怪象能使人触目惊心,意识到自身的“独特性”,但在具有普泛性隐喻的异态生存环境中,“触目惊心”则变成了“司空见惯”,而身处其间的人物们因群体环境的影响与暗示,已经丧失了自省的意识,即先爷们在无休止的与天命抗争的循环中逐渐失去了“自我”,蜕变成了一种“坚强的麻木”——永不言弃却又不思其意。但是更令我们所震惊的是作者赋予这些处在人间地狱中的人们的人性象征。应该说,阎连科的乡土世界是荒诞不经的存在,却又昭示了一个个乡村最原始的生态。而这些荒诞不经的存在,折射的却是乡村人无法言说却又切身体会到的存在的虚无感,空虚从肉体渗透到了灵魂。
精神层面的自我审视克制着肉体的行为方式,但是当这些非强加的意识约束不复存在时,人性扭曲的终极悲歌就在小说中上演了,一幕幕残缺影像的重叠都在展示着乡村人的灵魂扭曲与价值缺席。《日光流年》里耙耧山脉遇上亘古少有的蝗灾,为节省粮食,村人们将残娃全部扔到山谷,任凭他们饿死,用尸体诱引供全村人食用的乌鸦[4]。在生存没有保障的情况下,人类表现出“弱肉强食”的一幕,优胜劣汰是所有生物的生存规则,面对生死关头,人类先天的生存本能理所当然地被置于后天的道德文明之上,人伦亲情全消解在人性的残酷中。《受活》中受活庄组织的绝术团里得小儿麻痹症的孩娃,从开始表演把瓶子穿在鸟头样的脚上走路,到穿着瓶子翻筋斗,故意让玻璃瓶碎在脚下,让观众欣赏血淋淋的扎着玻璃渣的脚,升级至用力跺碎玻璃瓶,让血像雨水样滴下,直至在观众怂恿下仅拖着扎了玻璃渣的脚在台上流着血走圈,使原先露在脚底外的玻璃都钻进脚底板里,脚成了“喷血的水龙头”才算结束[4]。一幕幕升级的血腥场面事无巨细地表现了人性深层的噬血本能和暴力嗜好,对弱者的悲悯异化为对其的进一步残害。阎连科无所不尽其极地展示了生存苦难中的人性之恶。在他的眼中,人性中隐藏的恶魔如其他本能一样,深藏于人的体内,时机一到就会不可遏制地爆发出来,毁灭自我。
三、生存绝境中的苦难悲歌
而所有这些人性的异变,却又是在生存——这个亘古不变的人类命题下发生的。正是生存的内驱迫使受活庄人、三姓村人、先爷、尤四婆等以一种变态的方式来完成他们的种种行为,而正因为这种生存是随时伴随着苦难的,所以对于这些处于闭塞世界中的人们而言,抗争只能选择一种异于常规的方式。
他们的生存在作者的有意隐喻中已经上升到了整个民族、整个人类的生存,人类被浓缩为先爷、尤四婆、三姓村人等,他们被置于永世循环的苦难中。为求生存,先爷必须自埋以保留整个耙耧山脉唯一的命脉和生的希望;尤四婆的儿女必须代代以尸骨做汤以延续人类后代的繁衍;三姓村人也必须以最极端的方式与四十不存的命定厄运抗争。所有人的抗争都代表了“个体强大的生存欲望”和“人类繁衍后代的生命天性”[4]。
这是阎连科小说中最无奈的苦难悲剧,人类的生存仿佛处在无休止的与命运抗争的轮回中。先爷留的七粒玉蜀黍子将命运之神引领到了七个男人的面前,尤四婆的后代注定陷入削骨救儿的轮回中,三姓村人也永世在喉堵症的梦靥中挣扎。种种苦难描述都深刻反映了作者在现代社会对乡土文明的深刻反思,他试图通过对苦难的极致描写来揭露和批判现代文明下的乡村和乡村人的异化。于是在作者酷烈、压抑、沉重的叙述笔调下,乡土世界乃至整个人类的人性悲剧就纷至沓来了,悲观的情绪就一直笼罩在他的文本中。而作者在谱写一首首乡村世界的葬曲时,却又是“用‘轻的叙述艺术来驾驭‘重的现实苦难”[5]。在整个叙述中,他就像是一个冷酷的旁观者,淡淡讲述自己似曾听过、见过甚至亲身经历过的“故事”和“历史”。于是在作者冷静的叙述格调中,读者们似乎看到了非常透彻的精神真实,更体会到了平静之下暗含的震撼人心的苦难。
但是我们不能仅从作者赤裸的冷酷叙述中,就妄加断定阎连科的美学追求是悲观的乃至绝望的。正如作家的自白:“我不是要说极终的什么话,而是想寻找人生原初的意义。”[6]因此在阎连科的文学世界中,他对人性深层的探究始终都包含着他对乡土和人类的热爱之情,他只是拒绝外在美好的粉饰,而忠实于自我的生命观照。
“阎连科就是在这样的独白和孤寂里,与当代人进行着对话”[1]。他的文学创作注定是一条与黑暗、苦难为伍,历经心灵磨难的道路。但是在他的文学世界中,始终有一些温暖的东西支撑着他继续寻找自我,探究人性,关照社会和人生,也坚定着我们对于人类的信心。
参考文献:
[1]孙郁.日光下的魔影——《日光流年》、《受活》、《丁庄梦》读后[J].当代作家评论,2007,(5).
[2]阎连科.年月日[M].乌鲁木齐:新疆出版社,2002.
[3]阎连科.瑶沟人的梦[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7.
[4]余萃.苦难生存中人性深层的探究——论阎连科“耙耧系列”小说[J].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5,(5).
[5]刘剑梅.徘徊在记忆与“坐忘”之间[J].当代作家评论,2008,(1).
[6]阎连科.日光流年序言[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3)
方培,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