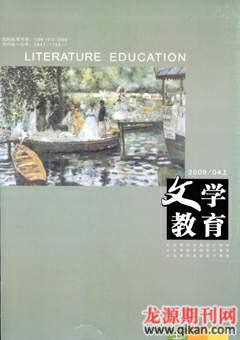小说的神秘从何而来
以“最后一个”命名的小说,如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等佳作,往往隐含了历史的挽歌意味。但张国增的这篇《最后一座木房子》,不是那种关于“文化寻根”的宏大叙事,它指向的是个体生命的神秘梦魇。
这是一篇颇有神秘色彩的小说。小说中的神秘感,不仅仅来自于内容的神秘,如木匠锡昌破坏了锡福新房子的风水,并导致了锡福的死亡,这种神秘其实还是表层的、浅显的,带有民间的谶纬色彩。事实上,构成这篇小说的整个神秘主义氛围的,主要是这篇小说的形式而不是内容。正如人们常说的,写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写,换句话说,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形式。与其说内容决定形式,毋宁说形式决定内容。在当代先锋小说家的视野里,内容是形式的产物。同样一个故事,如果讲法不同,故事的内涵就会发生变化。所谓讲法,也就是叙述策略,比较典型的就构成了叙事成规或叙述模式,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之类,都可以理解为典型的叙事成规。比如这篇小说的故事,作者可以按照现实主义叙事成规来讲述,木匠锡昌害死了锡福,并夺回了原本属于自己的女人,但他的后半生一直沉浸在暗中造孽的痛苦和悔恨中。如果这样讲述,就是一篇不折不扣的拷问人性的小说。然而作者没有这样做,他的叙事意图主要不是为了拷问人性,而是试图编制人生神秘的密码。与揭示或敞开什么相比,作者对遮蔽似乎更感兴趣。为此,他选择了云山雾罩式的先锋派的叙述实验,通过叙述人称的变化、叙述时空的交错等等去营造人生的宿命和因果。
虽然这篇小说从表面上看是最常见也不过的第三人称叙事,但小说中其实有两个叙述人:一个是第三人称的全知叙述人,一个是第三人称的限知叙述人。这两个第三人称叙述人错综复杂地缠绕在一起,全知叙述人时常打断限知叙述人的叙述节奏。最先出场的是全知叙述人,作者在这里选择第三人称全知全能的叙述是必需的,因为这种上帝般的叙述人可以俯视主人公的命运,木匠锡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被全知型的叙述人所掌控,主人公仿佛叙述人掌中的玩物,命中注定无法逃离命运的巴掌心。小说开篇从三十八年前他害死了情敌锡福并给他送殡的场景写起,写晚年的锡昌出现了时空错乱的幻觉,误把过房儿子福麟当作了孙子胜有,由此引发了锡昌对孙子讲述自己的人生往事。但那是他的人生隐秘,所以他的讲述不是以惯常的第一人称来展开,而是选择了第三人称叙事,仿佛讲述的不是他自己的往事,而是一个陌生人的故事。他的讲述是有节制的第三人称限知叙事,几乎省略了叙述人的感情色彩,也放弃了对主人公的心理描写,完全是“呈现”式的叙述,重画面、重场景,仿佛早期的黑白电影,但此时无声胜有声,更加增添了这篇的小说的神秘气息。有意味的是,作者还让锡昌的孙子——作为故事的听者(受众)的胜有也参与到故事的讲述中来,其实也是让读者积极参与故事的重构。这种让读者和叙述人一起完成故事的讲述的做法,既是新颖别致的“元小说”技法的运用,也是作者营造文本神秘气氛的一种叙述策略。锡昌故事的神秘面纱正是在叙述人和听者(读者)的共同作用下一步一步地被敞开的。锡昌的自我讲述是这样开始的:“叙述中的小伙子踏着晨曦,一步步朝黄龙岭上走来。胜有首先看到了他白色的粗布短褂和肩上的木匠家什。”这种叙述仿佛电影镜头,由远及近,其中隐藏着玄机。讲述的中途,作者如此实现着叙述转换:“此刻,故事中小伙子虽然走出了黄旗沟的地界,毕竟走不出讲述者的视野。”叙述中的宿命气息简直扑面而来。又如:“夜幕在讲述的停顿中慢慢合拢。”“透过淡薄的晨雾,胜有再次看到了那个叫锡昌的木匠。”叙述人就这样用第三人称讲述自己的隐秘故事,诡秘中悬念丛生。虽然随着作者的叙述走向终结,隐秘最终被解开,但文本中的宿命气息不仅没有被祛除,相反变得更为浓烈。
此外,文本中还多处运用了暗示和预示的叙事技巧。如锡昌的病根,他暗中放在锡福房梁上的木车,他最终的离家出走,无不是命运的隐喻。尤其是预叙的运用,把主人公三代人的命运纠缠在一起,打破叙事时空的界限,更增添了宿命意味。作者拆解了现实主义叙事成规中常见的理性的因果律,如锡福之死是由于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的社会原因所致。通过个人化的神秘主义叙事,重建了非理性的宿命论的因果律,传达了个人对命运的神秘体悟。
李遇春,评论家,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新文学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