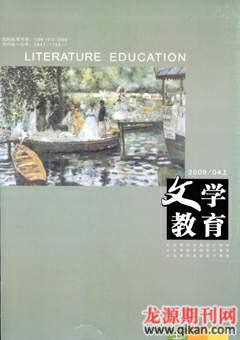最后一座木房子
张国增
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
欲知后世果,今生做者是。
——《三世因果经》
最先冲开记忆闸门的是那座木房子。房门进开的时候,一驾花轱辘车披着纷落如雨的碎片,从脑海深处浮幻而出。拉车的关东牛仗着凶蛮的犄角,从颅骨的封结中挺出脖颈,把压抑许久的吼声播撒成一串无始无终的寂灭和空冥。
于是,三十八年前那次出殡的场景,就像潮水一样从玄秘深邃的远方漫流而出,缓缓地,洇透了时空层层帷幔,泛硷般变幻在记忆的坝堤上——
树叶凋落,纸钱飞扬。
黑白的底片上,老人偌大干瘪的面影铺陈得若隐若现。杠夫抬着棺椁,把整幅的出丧场面重叠上来,便有呜咽声细如蚊蝇般由远而近,惶措,匆忙,在眼前盘桓了几遭,便头也不回地遁入两腮的塌陷里,只把几缕锈迹斑驳的唢呐声遗落在颧骨上,涩涩地,撩拨着老人的心尖儿。头顶上,间或有三两声炮仗无声爆响,纸屑飘飘洒洒的,似乎在试图弥合着山里断裂的岁月与沟壑。两条送葬人流从鼻翼两侧的幽暗里挣脱出来,拖沓着,摇晃着,簇拥着一个男孩愈走愈近。孩子的面庞逐渐放大并清晰,以致与老人的面孔重合在同一画面。这是一张瘦削的脸,嘴角甚至有清亮的口水迎风飘曳。老人隐在画面后,面容呆滞沉静如水,眼睑却连连眨动不止。这不是孙子胜有吗?此刻,胜有瘦骨嶙峋,脸色阴郁而悲戚。他托着灵牌,边走边喊:爸!阳关大道,朝南走吧……喊声尖细且凄楚,还带着颤颤的尾音,打着旋儿,拧着弯儿,生猛无羁地从时光深处透泻出来。乍泻的喊声丝毫不减原有的威势和质感,似强光,如钢针,朝着老人直刺过来。老人的心房骇然一抖,身子便不觉一偏。就这么一抖,一偏,竟偏过了锐利的锋芒,竞抖落了迷乱的幻象。一时间,老人蓦然醒悟到这不是胜有,而是胜有的爸爸——他的过房儿子福麟——是八岁那年的福麟在为生父打幡引魂!
死者是个年轻汉子——黄旗沟生产队长黄锡福。锡福生前曾带着乡亲们风风火火地走了一遭——入社、合作化、大跃进……走到“低标准”时,这条牛般的关东汉子,终于走不动了。撂下老婆孩子,一个人躺进黄龙岭上的土坑里,不无遗憾地看着沟里人日后学大寨、学小靳庄、战天斗地修梯田……也看到两年后,老婆彩凤挟着儿子福麟,走出了他那座落成不久的木房子,嫁进上院本族兄弟黄锡昌的家门。此后,三十余年生计劳作不用亡者操心。
——老人是在三十八年后腊月的夜里看到篇首场景的。
他在看到纷乱往事的同时,看到了一个女人。女人步态轻盈,风摆嫩荷似地移上前来。于是,就有玫瑰色的雾翳包容了老人的身,就有幽兰般的气息挟裹了老人的心。锡昌哥,醒醒呀。胜有让你讲故事哩。女人说完,嫣然一笑,然后精灵一样款款退去。老人回过神,探身一拽,情急之下,是一声衣物撕裂时干脆粗长的细响。他惶惶地收回手来,一看,抓到的是一件凉喇喇的塑料物什。
——玩具车的铃声是老人惊醒的直接原因。
他虽然极力想要留在梦境里,却不得不睁开眼睛。孙子胜有提着一个古怪尤物,兴致勃勃地坐在面前。老人瞥了眼墙上的钟,这才发现抓到面前的,还有孙子稚嫩的小手和圆圆的脸庞。
……你知道现在几点钟吗?
七点呀,爷爷。电视里树爷爷和花儿姐姐的故事刚讲完呢。
是呵,他太困乏了。老人已经三个昼夜没合眼了——尽管刚才他确确实实地打了个短暂的瞌睡。
爷爷,你也给我讲个故事吧。
老人知道那精灵的提示兑现了。因为六年来,它不止一次在他的生活中预言并应验。
爷爷,这是爸从城里刚买回来的。孙子一骨碌爬上炕,炫晃着手中红绿相间的玩具车。爸还说,过几年,给我买个真家伙,往城里送罐头……
胜有见爷爷另有所思,就撇开玩具车,搂住了老人的脖子。
爷爷,讲一个吧。
老人挣扎着坐起身。一瞬间,他觉得自己又一次回到了刚才的梦境。不,梦是假的,而刚才的一切却是真的!老人清楚这个“梦”的由来——它始于福麟跟他的一番谈话,更始于很久以前,那件与“车”有关的事情……
爸,跟您商量件事儿。前天夜里,福麟憨笑着坐在对面。
老人一时没作反应,静静地,望着儿子的脸。
爸,我琢磨趁着眼下冬闲,后天,把下院的木房子拆了。它太老旧,又常闹鬼,整个沟里也找不出第二座……开春后,在那里盖上一趟厂房,办个罐头厂。
老人记得,在儿子走出房门的瞬间,一股冷风呛进了他的喉咙……
从那时起,老人就病了,浑浑噩噩的,一直病到了现在。老人感到胸腔不断地向外扩张,心脏在充塞中膨胀,肋条轻微的脆裂挟着气管混浊的吐纳,使成串的咳嗽像黄昏后的蝙蝠一样,次序有致地从口中倾巢而出。恍惚间,透过自己栅栏一样的肋骨,老人看到胸中那轮桃形的落日,于晦暝中飘移过来,跳跃着,变幻着,逐渐充斥了整个视界。一片弥天漫地的猩红深处,有木屑状的黑斑迅疾地滋生而出,越来越大……
老人睁大眼睛,惊骇地凝视着这个纠缠了自己几十年的病根。
爷爷,快讲呀。
一阵剧烈的咳嗽平息后,孙子捶着老人的后背,把他从迷幻的困扰中拖拽出来。
——讲什么呢?
老人的眼前是科尔沁草原的毡包和马群,是兴安岭守林人的木屋和白雪,是鸭绿江上一丝不挂、野陛张扬的放排汉子……随着场景的更迭变换,老人知道眼睛又花了:是的,自打六年前彩凤下葬回来起,就花了;老是看见一个人影在跟前晃动——身材让人眼熟,脸面却不清楚。有时离他很远,远得只是—个模糊的身影;有时又离他很近,近得几乎抬手就能碰到他肩上的斧锛锯凿……可就是始终看不清面目。
不过不看也知道—一那是个小伙子。
老人清楚这个小伙子的身世和经历,更清楚迄今为止,唯一没有讲给胜有的,就是他的那些陈年旧事了。
叙述中的小伙子踏着晨曦,一步步朝黄龙岭上走来。胜有首先看到了他白色的粗布短褂和肩上的木匠家什。小伙子的身体是精壮的,精壮的身体从老人的讲述和摇曳的树丛中几经隐现,停在岗梁上的大青石旁。放下家什,解开腰带……短暂的间歇后,祖孙二人同时听到了一种熟悉的声响,那是水流与山石激溅出来的脆响。
锡昌哥……小伙子听到一声轻柔的呼唤。
身后的树丛中,闪出一个水红布衫的姑娘。老人的眼睛豁然一亮,他是多年以后才知道,那姑娘是早已候在那里的。小伙子忙不迭系紧腰带,转过身,迎上前来。
妩媚的睫毛泛起一缕温润,姑娘低下头。老人看见她柔滑的秀发梳拢得光洁而熨帖。
锡昌哥……你真走?
一阵沉默过后,小伙子点了点头,点得很慢、很沉。
我说过——我不嫌……
姑娘羞赧地把头埋进小伙子的胸前,语音极低地说。小伙子呢,轻拢着姑娘的肩头,目光却投得很远。
此刻,一行秋去的大雁忧悒地滑翔在青蒙蒙的天际。
你不嫌,我嫌!嫌有了金凤凰却没有梧桐树。彩凤,让你嫁进我那座旧房子,我会觉得欠你一辈子的!
老人知道,这是小伙子的心里话。抬眼看时,却见他嘴唇嗫嚅着,并没有把它完整妥帖地说出口来。
锡昌哥,你不要走了,我们啥房子不能住呀。
这次,小伙子倒是回答得快捷而干脆。
彩凤,你不要说了。除非我让你住上这样的木房子!
说话间,从怀里掏出—件木雕,塞进了姑娘手里。那是他用几个晚上,精心雕刻的小巧别致的木房子。
直到小伙子的背影,让一片明艳的杏黄托浮着融入淡蓝的远山,姑娘依然站在岭上,怔怔地,眺望不止。风来了,吹着姑娘的头发,也吹着老人的记忆。老人就看到姑娘在风中一点点变老、变丑,最后变成黄龙岭上那堆野草萋萋的荒冢,这才想起自己刚才看到的,都是四十多年前的情景了。那山道、大青石,还有姑娘和小伙子,都是当年的模样。老人清楚,那块青石是“大跃进”的时候,公社修果园劈开的,盖了果树队的房子。更清楚后来生产队解体了,乡里就把果园甩给了村里,村里又把它包给儿子福麟。几年的光景过后,福麟就在他的老宅上,盖起了这座沟里沟外独一份儿的小洋楼……
这小伙子是早晨上工前出走的。昨天,他还是黄旗沟生产队的一名五好社员,现在不是了——现在他是一个浪迹四方的木匠。在队里,他弯腰流汗地苦干了三年,小伙子的心凉了,同时也从一种狂热中清醒过来。小伙子想起了对彩凤发过的誓言,他要让自己心爱的姑娘住上宽敞明亮的木房子。三年过去了,小伙子发现这目标离他越来越远,以致变成一团模糊的幻象。他焦躁、苦闷,一个大胆的念头霍地跃上了脑际——他毅然决定出走四乡,靠响当当的木匠手艺,去实现自己心中的夙愿!
——听懂了吗?就这样,他一个人跑了单帮儿。
爷爷,小伙子后来挣到钱了吗?
胜有睁着黝黑的眸子,朝楼上望望,回头看着老人。
楼上传来电视的乐曲声,挺慢,颤悠悠的。老人知道,儿子和媳妇还没有睡下。他斜楞着脖子,再听,就听到唱的是好人一生平安……老人想起锡福,想起彩凤,想起自己漂泊的前半生,无言地笑了。此刻,故事中的小伙子虽然走出了黄旗沟的地界,毕竟走不出讲述者的视野。老人目送着小伙子,直到把他送进一支凶悍粗蛮的伐木队伍。那是狗皮棉帽子组装的天地,是一脸胡楂儿满嘴猥亵的雄性世界。伴随着一声声“顺山倒”的号子,老人看到小伙子头发乱了,胳膊粗了,昔日光洁的嘴上,渐渐泛起一层青的胡楂儿。他像红了眼的公牛一样,没有人干活儿胜得过他!冬天伐木,夏天放排,科尔沁草原贩马……在风餐露宿的五年中,他完成了一个青头小子向男子汉的过渡,同时,腰里的“天安门”票子,一天天地厚实起来。
胜有把胳膊支在膝盖上,神情专注地看着对面,看那如豆的野猪油灯光,看那小伙子点票子欣喜万状的侧影。正看得入神,爷爷的手搭在了他的背上。胜有就回过头,看着爷爷。看到爷爷滞涩地点了点头,说,挣到了,挣得很多。
如果不是爷爷点明,胜有一时很难认出,站在黄旗沟口的这个男子,就是当年黄龙岭上毅然出走的小伙子。男人步履蹒跚,面容憔悴,满是风尘的白布短褂群鸽般飘舞在故乡的晚风中。
老人的讲述省略了感情色彩,听起来,像早期的黑白电影——无色且无声。
男人在这无色无声的境界里,一步步走近了阔别多年的村口。走着走着,站住了,站在夕阳里,—任扁长的身影急不可待地蹿上路旁的井台。井台上,谁家的女人正在搓洗衣裳,熟悉的背影勾勒着柔美的曲线,羊脂般的酥手在盆中揉搓不止。女人的身旁,就是那只水桶了。水桶静静的,把一团沉稳的黑点缀在白亮亮的井台上。男人的目光最终锁定在水桶上,迟疑了片刻,就惶急地抢上前去。探头,俯身,那嘴就牢牢地叼住了桶口。叼住桶口的嘴立时变得停顿而安分,却急坏了下面的喉节,喉节就急躁暴跳地蹦蹿起来,蹦得胜有的耳畔,折起一串咕咚咕咚的联想。
就这样静得安闲,就这样躁得惶急。男人在这疏密张弛中,喝饱了肚子。喝饱后的男人抬起头来,吁了口气,想起该对水桶的主人说点什么了。
胜有看到黑白的画面下,急遽变换的几行字幕——
谢谢,大嫂……
……锡昌哥,是你?你不是……
彩凤,是我……
夕阳的逆光下,两个黑色的身影凝固得泥塑木雕一般。
这些年,你在外面……
想呵,想咱黄旗沟,想……
两人正说着,突然从那种投入中回过神来,面孔转向了同—个方向。
画面把—个抱着婴儿的汉子切换到祖孙二人的视界里。汉子神色慌忙,匆匆跑来。一边跑着,—边连连低头,看那怀里的孩子。孩子哩,小腿在汉子胸前裸露着蹬踢,包裹的一角就拖在了腋下,旗帜一样飘摇着,招展着。
孩儿他妈,娃崽儿他哭呀……要喂奶哩!
汉子把孩子塞给女人的时候,女人就趁机转过身去,背对着两个男人。汉子对妻子的举动毫无觉察,倒是偏过脸,怔怔地看着来人揉起了眼睛。
锡昌兄弟,是你……你回来了?
锡昌呢,看看面前的汉子,又看看转过身去的女人,锡福哥,彩凤……
哦,彩风是你嫂子了。
一时间,胜有看到了锡昌难以言喻的表情和锡福拍在弟弟肩上的大手。
拍在肩上的手是无声的,跟拍在水面上差不了多少。可是,画面却被拍碎了。画面一破碎,人物的脸就扭曲了,田园房舍就倾斜了,山峦林木就开始旋转起来……而点缀在诸多影像之上的,是一个个杂乱铺排的“嫂子”、“嫂子”的词组。
夜幕在讲述的停顿中慢慢合拢。村口、井台、辘轳,还有山里人家零星间隔的灯火,相继归入一团沉静而深厚的黑。
夜里划亮一根火柴,眼前立时升起一轮圆月。锡昌躺在月亮里,闷闷地,吸烟:吸着吸着,连同破败的背景,连同颓废的心绪,一览无遗地吸进了黄澄澄的铜镜里。月亮就那么悬着,夜空就那么静着。万古如斯的长夜深处,谁在用一声长叹连贯着时空的两端。同—个地点,同样的不眠之夜,一端是初秋时节,一端却数九隆冬。进行和回顾交叉着,错合着,有如两条河里的水,在这里交汇碰撞,变换漫流。不变的,是那天上的月,是这窗上的霜,挑着空静的白,一成不变地留守着记忆。那霜里,映着祖孙二人的脸,清白清白的,镀了水银一般。
就这么一个讲着,一个听着,不知不觉间,看那火柴已经灭了。
火柴灭了,月亮就落了。落入云层的下面,落入一片无际无涯的黑。
锡昌在黑暗中掖掖被角,掖完,又伸出胳膊,把卷制的喇叭筒吸得忽明忽暗。伴随着烧燎烟丝的滋滋声,一个人从黑暗深处走出来。走来的人似乎踮着脚,走得悄然无声,走得若隐若现。老人还是一搭眼,就认出了这是猫眼。一个瘦猴般的辽西汉子,三十多岁,刀条脸。这家伙让人记住的地方太多了,最不能忘怀的是他的眼睛,贼溜溜的。特别在生气或发怒的时候,能射出两道翡翠色的绿光来,瞅着鬼火一般,让人心悸。锡昌和猫眼相识的那年,在通化,给一个公社书记家盖房。猫眼无端挨了东家的训斥,挺窝火的,躺在帐篷里阴着脸,一言不发。锡昌那时年纪还小,想劝慰都找不到合适的话语,就在猫眼身边,陪着他闷坐。猫眼枕着胳膊,望着棚顶,眼睛叽里咕噜地打转儿。转着转着,拽起一把刻刀,挺身跳下了板铺。锡昌怕他一时冲动,做出什么傻事来,就上前拦阻。可猫眼只是从卧铺走到门口,就停住了。停在一堆刨花前,弯下腰去,翻。翻了一会儿,翻出一个木块儿。猫眼拿在手里,掂了掂,就回到了铺上。回到铺上的猫眼,闷着头,吭哧吭哧地削起了木头。这家伙不愧是手艺人,一双鹰爪般的枯手纤巧无比。那木块儿几经翻转,就显出一驾小车的雏形来。而且越削越精,一会儿工夫,车辕轮轴依次从手中蹦跳而出,瞅着活脱脱的。削到夜半,总算削好了。偏着脑壳,端详;端详了半天,这才满意地掖在枕下,就要倒头睡去。锡昌自始至终地看着他,看得惑然不解,就缠着猫眼,让他说出究竟。猫眼支支吾吾地搪塞着,想敷衍了事,这越发激起了锡昌的好奇心。看看实在拗不过,猫眼翻过身来。翻过身来的猫眼,下巴抵在枕头上,死盯盯的,望着锡昌。兄弟,你听过咱手艺人的黑白两道吗?
啥……啥黑白两道的?
白,就是东家对得住咱,咱也绝不能亏了人家。手艺人头号儿的德行就在这儿!
黑呢?锡昌惊异地瞪大眼睛。他觉得此中定有蹊跷,不像自己看的那么简单。
要是东家对不住咱,咋办?猫眼没有正面回答,倒是反过来,问他。
咱给他干活儿,他能对不住咱?锡昌笑了,觉得这话问得毫无来由。
呸,蠢货。猫眼看着锡昌满是月光的脸,考小孩儿一样问他。我问你,如果你碰上个好东家,咋办?
那还用问,好好给他干活儿就是了。
如果遇到坏东家、黑心的东家呢?猫眼说着,把头一探,目光直逼过来。
那怕啥,顶多不干就是了。
说得容易。都不干了,你他妈挣谁的钱去!
那咋办,也像你,削小车出气?
你叫它小车?蠢货!这叫木车(发音ju),灵验得很哩。
小车也好,木车也好。顶啥,能帮你出气?
顶啥?明天你就知道了。猫眼打了个呵欠,往被里缩缩,语调含混地说了声,睡吧。
第二天是书记上梁的日子,书记上梁自然是极热闹极气派的。然而,锡昌并没有被这些浮华喧噪所困扰。从打早晨开工起,他的眼睛,就一刻不离地盯着猫眼。他要看看,这个诡秘怪异的家伙,整的到底是啥西洋景儿。这一刻,终于在他的等待中到来了。那是贺客最混乱鞭炮最密集的一刻,锡昌看见,猫眼偷偷地把木车放在了书记的梁柁下。车辕朝外,斜斜的,指着大门的中线。锡昌站在梁下,吃力地咽了好久,才把那声惊叫咽回肚子里,而且一直咽到了晚上。晚上回到工棚后,熄灯,躺下,锡昌才把疑问抖到了猫眼面前。猫眼被逼不过,咬着锡昌耳朵,把个中奥秘向他和盘倒出。这—倒,倒得年轻人石破天惊震撼不已。他陌生人一样看了猫眼良久,一字一句地低声骂道:
猫眼,你这么阴损,当心将来养孩子不长屁眼儿!
猫眼听了,不屑地缩脖直笑。两肩一抖一抖的,满脸邪色。
老人用干裂的嘴唇,开启了黄旗沟又一个黎明。
透过淡薄的晨雾,胜有再次看到了那个叫锡昌的木匠。木匠披着衣衫,怔怔地,站在一处房场前。木匠的脚下,到处是杂乱堆放的石块、木料,这使他的举手投足变得拘谨而顾虑。有时,他要憋足气,曲腿,耸身,然后蛙一样从这里跳到那里。有时,又要斜着身子,呼气,收腹,再螃蟹般侧着身体穿行。就这样走走停停,就这样跃跃蹿蹿,几经辗转,锡昌来到一处窝棚前。窝棚是临时搭建的,很低矮。窝棚的门里,当然更低矮了。锡昌停下身,停在花布门帘下。门帘迎着曙色,挡在面前。锡昌在帘下站了很久,很久过后,他咽口唾沫,喊了声,哥。早晨的空气虽然湿漉漉的,但并不滋润人的喉咙。锡昌的这一声喊,干巴巴的,狗尾巴般摆动了一下,就软软地跌落在地上。落在地上的声音消沉而低靡,还是惊动了窝棚里面的人。锡福和彩凤一脸惺忪地走出来,眯缝着眼睛,看。看了半天,看到—个瞧悴的身影,立在晨光中。晨光是微红的,衬得身影愈发的黑,黑如木桩。木桩一直那么沉默着,包裹呢,就在这种沉默中,塞到了锡福的手里。锡福接过包裹后,挺困惑的,回过身去看着彩凤。彩凤也蒙了,站在门帘下,满脸惑然。于是沉默便推进并延续了许久,于是夫妻俩便对视了许久。许久过后,锡福还是伸出手,打开了满是油渍汗垢的包裹。打开后,里面竟是—叠票子,整整齐齐的,摞着,砖头一样。两人当时就怔住了,大眼瞪小眼的。半晌,目光才慢慢地回到锡昌身上。
兄弟,你这是……
哥,你们收下吧。锡昌一脸木讷,嗓音低沉,哑嚎嚎的。
这怎么行呀?锡福有些失措,转身对着彩凤,摊开了两手。
盖房子需要钱。哥,往好上盖吧。锡昌站在晨光里,依旧平淡木讷。
可你……你还没成家呀!锡福终于想起了回拒的理由,脸色焦焦地说。
我……什么也不需要了。锡昌说完,转身走了。背影黑黑的,哀凉委顿,让人心冷。
锡福两口子把上梁的日子,定在农历的八月十六。
日子定下的前几天,锡昌就开始忙碌起来,有事没事的,都在赶制着一驾手雕的木车。一天中午,锡昌从下院回到家,坐下身,专心致志地雕刻起来。雕着雕着,就想到了猫眼,还有他雕的那个木车。想起了木车,心里就不由得对照起来,对照制作上的谁快谁慢,对照工艺上的孰优孰劣。彩凤就在这个时候,走进了木匠的家门。彩凤不是一个人来的,她带着儿子福麟。两人走进屋子的时候,悄没声儿的,直到走到了对面,锡昌依然沉浸在那种对比中,浑然不觉。锡昌看见彩凤,脸刷地一下红了,嘴也拙了,结结巴巴的,连说没事儿没事儿,刻着给孩子玩的。等到彩凤走后,锡昌连忙收起木车,收了很久,直至锡福上梁那天,才算派上了用场。
上梁的中午,帮忙的、随礼的、干活儿的,一时间纷纷离开房场,聚在东面空地上,喝东家的喜酒、吃东家的喜宴去了。偌大的房场上,变得冷清空旷起来。没有人注意,在这种冷清空旷中,锡昌骑在梁柁上,磨磨蹭蹭的,没走。梁是新伐的白杨,一刮,沁着浆汁儿,还发散着鲜润微甜的气息。木匠就那么坐着,坐了很久,木雕般望着下面的柁根,更准确的,是望着柁根下面一个新凿的洞口,愣神儿。洞口黑幽幽的,看去独眼一样。有凉风不时地渗出来,丝丝缕缕的。锡昌坐在梁柁上,眼睛一直对视着那只独眼。对着对着,他的手就不知不觉地探进了衣袋。
……这车辕朝后,金银财宝生拉硬拽地涌进家门,小日子一准儿过得火炭儿红;这车辕朝前,任你多大的产业,也得顺水东流、家境败落!探进衣袋里的手,攥住了木车。懵懵懂懂的,耳边响起了猫眼低沉喑哑的嗓音。
一只手掏出木车,缓缓地,朝洞口送去。一只手按住凿子,吃力地,撬起了梁柁。这中间,锡昌不知掉换了多少次木车的朝向:朝前,朝后;朝后,朝前……他做事从没有像今天这样优柔寡断。直到木车又一次抵到洞口,锡昌还是没有拿准,这车辕到底应该朝前还是朝后?也许再给他几秒钟,再给几秒钟的时间就好了,他就会拿定主意,心无旁骛地放置下去的。锡昌记得,他最后一眼看到木车时,车辕恰恰是朝前的方向。就在这时,空地那边喜宴开始了。喜宴开始了,鞭炮就响起来了。鞭炮一响,他的心就乱了,这使他永远失去了修正的机会。他看到人们擎起酒碗,吆喝着,嬉闹着,纷纷向锡福两口子恭贺乔迁之喜,祝福上梁大吉。他还看到,锡福站在人群里,应承着,招呼着,不时地抬起手,挠着黑亮的脑门儿。锡福的身旁,自然站着彩凤,贴得挺近的,脸快贴到锡福的肩上了。彩凤搂着丈夫的胳膊,面庞红润艳若桃花,俨俨一个喜气洋溢心满意足的美妇。锡昌看了,心头一搐,按在凿把上的手,不觉间就抬起来了。手在上面一抬,下面一声闷响,木车立时被压在梁柁下,严实实的。一枚进起的木屑,精灵般钻进了锡昌的口中,不及反应,就滑进了嗓子。慌乱中,锡昌狠命一咽,不想那东西既粗砺又尖锐,在食道里翻滚着、切割着,一路闹腾着下到了胸口。下去后,翻动几下,这才瓷实慵倦地躺在了里面。
嗓子一痒,锡昌立时咳了起来,咳得昏天地黑,咳得泪如泉涌。咳了许久,才慢慢平复下来,锡昌一边拍着胸口,一边想,这下总算结束了。然而,这些并没有结束,而是刚刚开始。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由此留下了病根儿:咳嗽。而且这咳嗽终生缠身,而且这咳嗽无药可医。在此后几十年的日子里,锡昌无时无刻不倍感煎熬,如坐针毡!
那场漫及全国的大饥荒让人触目惊心。黄旗沟每天都要死人,偌大的沟筒子里,流淌着彼落此起的哭泣和哀乐。树枯了,地荒了。天上的鸟,少了;地上的人,蔫了。鸟一少,天就空了,空成一片死静的蓝;人一蔫,街就冷了,冷成一线清冽的白。只有队里食堂的饭口,一日两次地热闹着;只有木匠锡昌的生意,一反常态地红火着!锡昌在那些日子里,整天沟里沟外地穿梭不止,为这家那户的死者做材。材做好了,犒赏就来了,虽微薄,倒也实用!或一顿两顿饱餐,或三个五个饼子。却因而混得个一饥半饱,足让村人艳羡。
一日,那工收得早,没到中午,锡昌就回到家里。回到家里的锡昌蹲在地上,掏出饼子,艰难地啃咬。饼子是高粱面的,很黑,还硬。啃着啃着,眼前一暗。锡昌抬起头,看那狭小的窗玻璃上,两只小手扣着一颗脑袋,怯怯地,朝屋里窥望。窥望中的眼睛,贼亮,透着荧荧绿光。锡昌想了想,起身走出房门。窗下,立着一个孩子,两手并拢于股间,静静地,望着他。叔,我饿……锡昌俯下身,辨认许久,才认出是锡福的儿子福麟。锡昌就叹口气,心里一阵酸楚,掏出另外一个饼子,递给福麟。福麟接到手后,仰起脸,久久地,看着锡昌。锡昌被看得胸口一紧,避开福麟的目光,看那天上的云。锡昌看云的时候,一条身影斜刺里抢过来,极快,还挟着风声。身影抢到孩子身旁,一出手,打落了福麟手中的饼子。饼子刚落地,即被拾起,来人头也不抬,捧着饼子,狼吞虎咽地大嚼起来。锡昌和福麟愣住了,呆呆地,站在房檐下。直到来人三下五下地把饼子吃完,直到来人忙手忙脚连连撸捏着喉节,锡昌和孩子才同时认出,这人竟是福麟的爸爸锡福。锡福拍着胸脯,半天才缓过气来,他看看锡昌,又看看孩子,目光惑惑。福麟儿,你在这里做啥?一时间,就看见孩子张大的嘴巴,就看见孩子眼里的泪水。锡福抚着额头,站着,吃力地想;想了许久,就想起刚才抢吃的饼子,正是至亲骨肉的口食!当下,一步步地朝后退去,嘴唇嗫嚅着说,我……我还是个人吗!一边叨念着,一边转过身,踉踉跄跄地跑出了院子。锡福跑出院子的时候,是中午。太阳高悬着,火辣辣地照,照得沟里沟外白亮亮的,池水一样。一时间,那水面就破碎了:碎成一声凄厉的号、碎作一块死寂的静……有波纹蔓延着,扩散出来。散过时间,散过空间,散在三十八年后的胜有身上,让他感同身受地体察了那种撕肝裂胆般的震撼。
我还是个人吗——我还是个人吗——
爷爷,锡福真的抢吃了儿子的饼子?
老人把目光从遥远的往事中收拢回来,沉沉地,点了点头。
他怎能抢吃福麟的饼子呢?
他饿呀。
他饿儿子也饿呀!
当时他的眼里,只有饼子。
儿子呢?
从打抢吃饼子那天起,锡福就变了,变得沉默寡言,变得拒吃食物。彩凤一旁见了,很是担心,就劝;但劝也无用,锡福闷着头,依然不吃任何东西。彩凤很无奈,眼睁睁的,看着男人的脸渐渐晦暗无光,看着他的身体慢慢收拢萎缩……那心里,火烧火燎的,就哭;哭也无用,锡福依然不吃不喝。就这样闷着头,就这样闭着嘴。几天过去,锡福的眼睛凸出来了,锡福的两腮塌下去了。昔日夯实的脚步,如今少了脚后跟一样,走路轻飘飘的。彩凤急了,红着眼睛,来找锡昌。锡昌就跟着彩凤,来到了下院。这时,天已黑了。天黑,屋里更黑,黑得锡福的脸纸一样悬在那里,白寥寥的。锡昌见了,心里虚虚的,走过去。哥,你不能这样!锡福的脸依然白得像一张纸,悬着。悬了半天,叹口气,叹得那纸飘动几下后,无声地飘出了屋子。
锡昌跟到门口,站住了。这时,月亮出来了,锡福挂在月亮地里,模糊糊的,剪影儿一样。锡昌扶着门框,眼睛直直的,看。直看得神思恍惚,直看得嗓眼儿发痒,看着看着,一串咳嗽涌上来了,锡昌忙不迭蹲下身,按住门槛,好像能把这咳嗽摁在门槛上似的。就这么撅着屁股,就这么蹲着身子,摁了许久,才把那咳嗽摁住。锡昌抬起头来,抹了把眼泪,边抹,边想,难道猫眼说的,真就这么灵验?
三天后的早晨,天刚放亮,锡昌被一串脚步声惊醒了。揉着眼睛,坐起身,彩凤已经闯进了屋子。锡昌见她惶急的样子,知道情况有异,连忙抬起脚,把身子顺到炕沿上。
彩凤眼里蓄满了泪水,说话喘吁吁的。锡昌,快点过去吧,你哥快是不行了。
锡昌心头一凛,回身抓起炕上的汗衫,说,真的?
自从出了那事儿,彩风跟着锡昌,急匆匆走出屋子,他就滴水不进了。
嗨,咋就这么倔哩?
他说……他没脸见人了。他不想活了。
锡昌走进下院的时候,锡福躺在炕上,直挺挺的,平静而安详。锡福的脸黄白发亮,看去贼寥寥的,很是饱满。与脸膛同样饱满的,是肚子,高高地隆在被子下面,孕妇临产一般。锡昌屏住气,轻手轻脚地走上去,探出脖子,看。一时间,看那肿胀的脸上,蓄满水似的,吹弹即破的样子。锡昌倒吸一口凉气,睁大眼睛,再看。就看到红的血管,蓝的筋络,红蓝交错在一起,乱麻一样。锡福这时还不糊涂,还觉察到身边有人来了。他伸出手,抓住锡昌的胳膊。抓住后,转过脑袋,慢慢地,又睁开了眼皮。锡昌看他眼睛,整个一个肉球儿,很圆,还鼓,鼓得馒头似的。这时,“馒头”裂开一条缝,细细的,有蚯蚓般的目光在缝里扭曲着,蠕动着。蚯蚓爬上锡昌的手,爬上了臂,爬过了脖颈,爬上了脸颊,凉瓦瓦的,停在了上面。
兄弟,哥不行了!锡福看到锡昌想要出口阻止,就摇摇头,制止了他。哥这辈子没亏欠过谁,可欠你的,实在太多了!
锡昌听了,不敢正视他的眼睛,扭过头,避开了锡福的目光。北墙根下,摆着口老式木柜。柜顶的摆设,挺简陋,简陋得那座手雕的木房子,突出且扎眼。
哥这辈子,看来还不上你了。可我不能糊里糊涂的,听凭人死账烂!锡福说到这里,眼皮翻启了几下。彩凤一旁看得明白,拉过福麟的手,拉到锡福的病榻前。福麟呵,别忘了!咱爷们儿欠你叔的。
哥,你别说了。怪我呵,都怪我呵!木匠鼻子一酸,眼前的景象立时模糊起来。
哥要走了。哥走,就把她们娘儿俩托给你了……
爷爷,后来怎么样了?
后来,他们就成了一家人了。
再后来呢?
再后来,日子好了,福麟也大了。他要拆掉那座木房子了。
不拆不行吗?
不行呵,它是沟里最后一座木房子了。
拆了木房子,不就看到里面的木车了么?
是呵。拆了木房子,人人都会看到里面的木车了。
那木匠怎么办呢?
那木匠……睡吧,孩子。明天再讲吧,明天你就知道了。
灶间的声响,像数不清的小虫儿,咬着胜有的耳朵,咬得他不得不睁开了眼睛。胜有睁开眼睛后,搓了搓,一时间,就有探询的心念,被搓上了脑门儿。那木匠呢?胜有想到木匠,自然想到了爷爷。于是,他一骨碌翻过身,把脸朝向爷爷睡的炕头。炕头这时空落落的,根本没有爷爷的影子。只有被褥整整齐齐地缩在一角,怯生生的,收拢而拘谨。
胜有惊悸地四下环顾,这才发现,屋子里除他之外,空无一人。
……妈,我爷哪儿去了?
大雪天儿,能哪儿去,一惊一乍的。
女人的声音裹着水汽,从灶房里传过来,听着柔润且漫漶。
可他不在屋里……
是不是去下院了,看你爸他们拆房子了?
一股无由的惊恐扩散开来。孩子偏着头,想想,然后跳下炕,几步蹿到了门厅。
胜有推开房门的瞬间,那座木房子正在落架。满山白雪伴着腾起的灰尘,被他一股脑儿地迎进了屋子。
天地间一时很静。静若止水。
一抹黄尘慢慢地升腾起来,不断地高,不断地淡。淡着淡着,淡出一方清明剔透的山里世界。太阳升起来了,光线透过灰尘,照得农家的房顶一片黄亮亮的白,白得耀目,白得爽眼。房顶的炊烟呢,更白。白色的炊烟扭结着金黄的光柱,攀爬着,上升着,用曲线诱人的动感搅扰着大山的浑重和沉默。沟膛子里,此落彼起着鸡鸣、犬吠、马嘶、牛哞,中间夹杂着男人呵斥牲口的粗鲁,女人召唤娃崽儿的娇嗔,喧闹而哄乱地迎接着黄旗沟新一天的莅临。
一行歪歪斜斜的足迹印在初雪的山道上,看去格外醒目,迟疑着,盘旋着,伸向山外。弯弯曲曲,曲曲弯弯,直至隐没在山坳间那团渐渐远逝的雾翳深处。
(选自《芒种》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