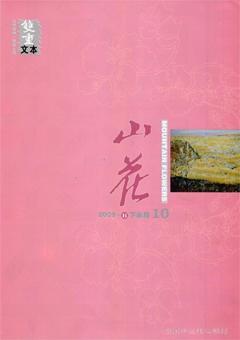大众文化背景下女性文学的繁荣及其审美流向分析
20世纪以来,大众文化已经悄然无声地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就我国而言,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商品经济蓬勃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长足进步,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兴盛于90年代的中国大众文化正在逐渐改变着传统的文化模式。大众文化一方面为女性写作提供了更宽阔的创作空间,另一方面又因为其强烈的渗透性并通过自身信息和受众的大量性、形式的流行性和模式化、观赏的日常性和效果的愉悦性以及商业性等特征对女性写作的发展起着巨大的影响。
1、大众文化背景下女性文学的繁荣
纵观文学史,不停留在花前月下、低吟浅唱的女性作家不乏其人,她们那些境界开阔、气宇轩昂的作品也广为流传。春秋时期许穆夫人的《都风·载驰》、五代后蜀妃子花蕊夫人的《述亡国诗》、南宋词人李清照的千古绝唱《乌江》等,都展示出一种慷慨悲歌的豪迈之气。到了清末,女中豪杰秋瑾的诗文,如《满江红》、《鹤鸽天》以及《宝剑歌》等,更淋漓尽致地抒发了女性的英雄气概。
而在现当代女作家身上,女性超越自身的对社会历史的关注得到了更加广泛而深入的表达,其中的代表人物,首推丁玲。与其他女作家相比,她的一系列作品更加贴近风起云涌的社会现实。在这些作品中,一种强烈的关注现实的忧患意识——在转向左翼文学后表现为明显的政治意识和对革命的自觉归依,始终与被新文化运动唤醒的追求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的个体意识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作家独特的创作风格。纵观丁玲的创作,这种创作个性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艰难的整合过程,是作家精神世界的内宇宙与客观世界的外宇宙不断碰撞发展的结果,与时代变迁和作家的自身遭遇密切相关。
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进步,电台、报刊、电影、电视等新的信息传播手段发展起来,运用这些媒介,文化出现了变为一种可以为制作者带来利润的商品的可能性。女性文学无可厚非地要介入到大众文化的制作方式上来,使作品以商品的形式作用于广大读者,大众文化为女性写作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女作家们对自我意识进行自觉的追求,“个人化”写作和“私人化”写作开始登堂入室,女作家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日益苏醒的性别意识和坚定的女性主义立场渗透到文本之中。虽然她们的表现形式、表现风格及其表现性别意识的程度、视角各不相同,但从本质上讲,她们以最具个性的方式向传统挑战,将长期遮蔽于男权阴影下的女性经验、欲望表达出来,付诸文本之中。
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陈染的《私人生活》被认为是这一时期女性文学的代表作。林白、陈染、海男等的文学作品从自身经历和自身经验出发,以自觉的女性意识为指导,生动、深刻地展示出一个令人感到陌生的世界,甚至将复杂的心理及晦暗隐秘一起逼真地展示出来。张洁在这一时期的作品,更多关注的是私人领域,涉及了爱情、婚姻、家庭夹缝中的人性关系,叙事方式由对男性中心意识认同的宏大叙述转入更具女性意识的私人性话语。徐小斌则采取一种基于女性主义的反叛立场,并以极具强烈反讽意味的戏仿手法解构着男权文化。与80年代女性书写人生及人性的矛盾不同,她们完全挣脱了性别禁忌的桎梏,在强烈的性别反叛意识的驱动下书写对生命的体验和思考,她们不接受世俗目光的窥视,它的本质是对人生和艺术价值的真诚,对生命的尊重。
在继以陈染、林白、徐小斌为代表的“身体写作”之后,进入到了“另类”女作家的写作时代,她们以“躯体修辞”为特征,被称为“七十年代生”女作家,她们的身体写作在这个大众文化四处渗透的时代所表现出来的,是冲出了上一代写作中的道德底线,肆无忌惮地描写性隐私,潜藏着她们的功利目的和商业目的。回顾一下2000年以来的文坛,但凡引人注目的热闹事件总与所谓的“身体写作”有关,从人称“美女作家”的卫慧、棉棉,到以《夜妆》(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标榜“胸口写作”的赵凝;从“下半身”的诗人写作团体,到以《沙床》(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而得到“美男作家”称号的作者,再到以《暧昧大街》(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标榜中国“男人私小说”的作者;从被指为“妓女文学”的《乌鸦》(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到网上网下都火爆的所谓性爱实录的《遗情书》……这一阶段文学中的身体是仅各具单一功能——作为无度的性行为的载体——的身体,并且,“身体写作”的产品在一片叫骂声中走俏市场。
我们看到了市场经济时代最受追捧的“双旅”景象:一方面,批判者通过对“身体写作”的责难而成功地显示、维护了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优势:另一方面,诸多写手在种种责难中出名,又因出名获得丰厚的经济回报。她们的成长期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大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并行的,大众文化特征势必会影响着“七十年代生”作家们的审美表达。
2、大众文化背景下女性文学的审美流向
2.1正现象
从审美价值取向上看,随着大众文化的不断丰富、发展,以伦理观念为核心的审美价值体系面临着新的挑战。新时期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巨大转型,便道德本位这一审美价值尺度被多元的审美价值取向所代替。女性作家的作品,无论是以张洁、张辛欣为代表的表现女性在家庭与事业中的双重困惑,还是以林白、陈染、徐小斌为代表以解构男权霸权话语,表现女性自我觉醒,张扬女性意识的“个人化”或“私人化”写作,抑或是“七十年代生”女作家的“另类”写作,都反映了不同时期的女性遭遇,满足了大众审美价值转变的需要,她们以女性独特的笔触表现女性在社会转型时期面对爱情、事业的人生态度以及在消费社会下女性价值观的变迁。大众审美价值的转变是女性写作的文本意义得到合理阐释成为一种可能。
在卫慧的《我的禅》、张抗抗的《作女》等小说中,不管是意识深处的“女权主义思想露了头”的倪可,还是大肆嘲讽、调笑男性的卓尔,都热衷于出入咖啡馆、酒吧,四处旅行。寻求刺激冒险的心理动机乃至性放纵的程度、方式都很相似。在这些女主人公周围,总是有一群痴心不改的仰慕者或拥趸,供她们颐指气使;《作女》中,有芦荟、老乔、郑达磊,以及邂逅的不知名的鸟类爱好者对卓尔的宠爱和膜拜。铁凝的《大浴女》中,有陈在、麦克、方兢一干男人,唐菲、孟由由几个女子,虽然这些人的目的和手段各不相同,但都须臾不离地围绕着尹小跳旋转。这里举一个例子,张洁笔下的吴为,她最早映入读者眼帘的形象,也是她最后的清醒时分的形象:就在前不久,由她出面,为一位年届八旬,门前车马稀落的前辈,安排了一个生日聚会;她刚从西藏旅游回来,给每个朋友都带了礼物,那些礼物品位不俗,总能引起朋友们的意外喜悦:
还给自己买了一套意大利时装,据说价格不菲;
又请了几次客,并亲自下厨,偶尔峥嵘地做了一两个菜,在她并不稳定的厨艺记录上,那几道菜的口味真是无可挑剔:
还有人说,在一场盛大的、庆祝什么周年的文艺活动中看到她,装扮得文雅入时;
这一段讲述,是对主人公形象的概括和总结。从卫慧的笔下走
到张洁的笔下,这些主人公的年龄在二十至六十岁之间不俗而又文雅入时,她们的多才多艺和善解人意,她们对价格不菲的时装的爱好,她们的气质,她们的自由不羁而又深孚众望。女性形象不再处于孤寂的境地:相反,多半成了领军时尚、左右逢源的潮头人物,以至于我们足以从这些女性人物的日常行为方式上,去领悟或领教什么是中产阶级的格调或精英主义的趣味。
由此看来,大众文化语境下女性作家的写作不仅在自我意识上有了更深一层的自觉,而且对商业化社会“游戏规则”的把握也更有穿透力,商业视角下的女性写作有了更为自由的广阔空间。当然我们也要意识到女性文学的审美流向的危机,那就是媚俗。
2.2负现象
媚俗是当代审美文化转型时期所产生的一种负现象,例如1998年,《作家》第7期推出一组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小说专号,在封二封三配上了她们的照片,让她们看上去更像一些商业招贴画。而在文本中,处处充满着商业化的气息,作品中专注于琳琅满目的物品的堆砌,从衣、食、住、行到家居摆设都充满了后现代消费的意味,似乎是著名商品的展览,渗透着浓厚的“拜物教性”。光怪陆离、变幻莫测的城市、时尚的生活方式、邂逅的情爱,以及必不可少的酒吧、咖啡厅、美容院、香水、电脑、名牌服饰和摇滚乐,建构着当代商业社会和城市幻想的新的符号系谱。个人欲望、物质享乐、奢靡浮华的观念在意识形态话语中已经获得了正统地位,只要我们想象一下“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成功人士”、“社会精英”等流行语汇及其所指,就能了解此言不虚。因此,以超前的方式来否定现存秩序、对抗流俗,这本身已成为现存秩序和流俗的一部分。个人的精神追求、自我价值定位已经被指标化,对理想的追求变成了对快乐的追求。
她们以大量的笔墨描写现代城市体验及物质体验,满足人们对后现代消费生活状态的向往。女性作家“物化”写作状态以外在表现形式上的媚俗和写作主体意识上的媚俗陷入了商业化模式的怪圈无法自拔。例如卫慧的《上海宝贝》:
我是这样一个人,对于父母来说,我是个没良心的小恶人(在五岁时我就学会拿着一把棒棒糖傲然出走);对于师长或昔日杂志社领导、同事来说,我是个不可理喻的聪明人(专业精通,喜怒无常,只要看过开头就猜得出任何一部电影或一个故事的结尾);对于众多男人来说,我算得上春光潋滟的小美人(有一双日本卡通片里女孩特有的大眼睛和一个可可-夏奈尔的长脖子)。
这段引文是作为叙事人的主人公对自己的认知。主人公对自己的认知仅限于“我是这样的”,而没有意识到“为什么是这样的”。主人公的自我意识流于臆想,她把对自己的希望变成了臆想的现实,她在对自己所作的评价中没有负面的成分,即使是“小恶人”、“喜怒无常”等语词也是一种反语式的自我褒奖,意指自己个性的特出。因而在旁观者看来,她所总结的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也就是她的自我评价)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相情愿的。
现今,以“美女作家”为主体的“女性写作”是以顺应时尚的方式,变对抗、叛逆的另类为新潮、浮华的另类,虽然引人注目,但是“美女作家”变卖了早先女性写作书写女性历史的使命和批判现实的先锋性。当初女性写作对私人生活的描述、对感官和女性经验的暴露,在集体主义和相对封闭的意识形态环境中,形成强烈的反差和冲击力。个人欲望、物质享乐、奢靡浮华的观念在意识形态话语中已经获得了正统地位。只要我们想象一下“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成功人士”、“社会精英”等流行语汇及其所指,就能了解此言不虚。因此,以超前的方式来否定现存秩序、对抗流俗,这本身已成为现存秩序和流俗的一部分。个人的精神追求、自我价值定位已经被指标化,对理想的追求变成了对快乐的追求,创造的冲动变成宣泄的冲动,我们当下的女性写作,已然成为市场经济社会一个有效率的“部类”,写作亦为“技术理性”所俘虏。
3、结束语
中国的女性文学不可能脱离文学语境而独立存在,进入转型时期的女性文学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大众文化的空前发展为其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它也会因为大众文化的巨大商业渗透性而陷入“商业”和“文化”双重陷阱中无法自拔,存在媚俗化危机。所以,在大众文化背景下,女性文学凭借什么为价值依托才能够继续向前发展,将是女性写作保持其长久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作者简介:
全朝阳(1971-),女,重庆市梁平县人,成都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主要从事汉语言文学、语言艺术与播音技巧教育教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