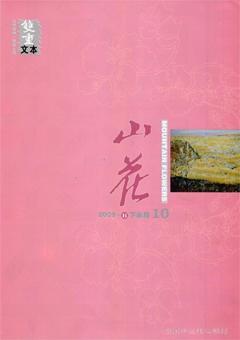聚增势能 洞穿感知
艺术张力的概念由美国现代诗人艾伦·退特最早提出。他在《论诗的张力》中说“我们公认许多好诗——还有我们忽视的一些好诗——具有某种共同的特点,我们可以为这种单一性质造一个名字,以更加透彻地理解这些诗。这种性质,我们称之为‘张力”。张力源自物理学的一个概念,是指物体受到拉力作用时发生在内部的一种牵引力。后来这种物理学力的概念借用到诗学研究中,是指诗歌文本内部诸要素(情感、意象、语言等)的排列组合中生成的,能聚增为超常的、可达情境极地的,洞穿读者惯常感觉心理的势能的紧张关系。
“张力”作为诗学概念,是20世纪新批评派对抒情文本魅力的勘探发现和对诗学理论的擦亮。“张力诗学”认为,张力源自于诗歌文本元素之间的不同排列组合,因而张力既存在于诗歌的内蕴、主干、语义之中,也生成在诗歌的意象、肌理、语符之中。
有了张力。弓才能把箭射向远方;弓拉得越开,箭就飞得越远。唯有文学作品具有“会挽雕弓如满月”式的张力,才能使艺术之箭敲开读者的心扉,引起他们的心灵震撼和情感共鸣,产生长久的艺术魅力。一个文学文本是否有张力,以及张力的大小,并不只是取决于作为物理属性力的强度,而主要取决于读者的心理尺度。对于力的感受和度量是以一个大体的中性状态为基准。在心理常态下,打破惯常状态的越界运动,与常态拉开距离,超过心理“度”,就会产生张力,拉开的距离与常态心理尺度越远,作品就越具有使读者彻骨透心的审美震撼力,感人殊深的艺术魅力。
作为一种艺术思维与手段,诗歌情感张力的生成主要有两种基本范式:一是异质元素之间悖论式组合。“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夕阳霞光万道,自然美丽无限,但同时又隐喻着人生的黄昏,生命的暮年。这样,自然的良辰美景与内心的萧条秋景形成了巨大的两极反差而又相反相存:审美的悦心悦意与人生暮年的忧患感伤造成了强烈的对立冲突而又悖论式地并置诗行。从而使整个诗行的语意生成、聚集了一种能穿透感知的强大的势能和压强。
另一种范式是同质元素的叠加、聚增。“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乡土依恋,团圆意识是传统文化根深蒂固,挥之不去的情结。因此,对中国古代人来说,与家乡、亲人的分离本身就是最令人黯然神伤,柔肠寸断。而对于那些多愁善感,情感敏锐而又丰富的人来说,离别就格外让人悲不自胜,愁上添愁。并且,多情的离别不是在“喜柔条于芳春”、“迟日江山丽”的季节,而是发生在“悲落叶于劲秋”的时节。经过“离别”“多情”“清秋”的层层叠加,相互组接,从而使普通离别之情被演绎、聚集、生成了一种能洞穿读者心扉的强大势能。诗歌形式需要有这样的一种势能、一种能量源泉、一种双向的、引而未发的力,它一旦与人的心灵相对应,就会迸发出强大的张力之火花。杜甫的《登高》属于后者的一个范本。
“以悲为美”是中国古典诗歌鲜明的美学风格。从宋玉始,诗人将登山临水的送别之情,羁旅孤苦的寂寞之心,文士失意的忧愤之怨,以及时光匆匆。生命将尽的惶恐等种种人生愁绪通过叶落草枯,山川寂寞等的悲情意象,出神入化地传达出来。自宋玉以后,从曹丕“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抒思妇之怨,到李煜“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写亡国丧家之痛:从岑参“千念集暮节,万籁悲萧辰”的生命悲叹,到马致远《天净沙·秋思》表羁旅无涯,游子之苦,产生了数不胜数的悲情作品,成为古代文学史上一道独特的诗学景观。杜甫的《登高》则是悲情作品中一首“拔山扛鼎”之作。
在《登高》的悲凉秋景中,诗人通过自己那种“多薄命”的人生苦痛的抒写,不仅汇聚了古代士人所普遍感悟的生命不济和人生不遇的双度悲情,而且把每一种悲情都写得至深至悲,彻骨透心,形成了浓重的悲剧情调。古代诗人悲情愁绪的根源主要有二:一是源于“逝者如斯夫”的生命感伤。在传统诗歌中,对时光流逝、青春不再、人生易老的生命悲叹被历代诗人反复抒写传唱,历久不衰。生死情结时时缠绕古代诗人的心性,成为他们挥之不去,抑之难平的人生长恨。早在《诗经》中就可看到“心之忧矣,于我归处”对生死的高度觉醒和殊深忧患。二是源于“天涯沦落”的人生苦绪。其中又包含了“离愁别恨”和“文士不遇”的人生双重之悲。对古代诗人来说,骨肉分离,漂泊异乡最让人柔肠寸断,伤悲动情。屈原感叹“悲莫悲兮生别离”。江淹说“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因此,绵绵乡愁又成为古代作品一以贯之的常见主题。古代文人群体多心存高远,志向宏大,追求“立德、立功、立言”,以实现“济苍生”“安社稷”“安黎元”的理想。但事实上,他们命运多舛,人生艰难。由“家”到“国”不仅存在自然距离,这就必然有一个“游”的过程,而且还有更大的制度距离需要跨越。加上人生价值选择的单一化,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古代文人选择“宦游”,也就选择了悲剧人生。
诗的颈联、尾联由上文写景过渡到抒情。五、六两句写出诗人暮年多病,长期万里漂泊,孤苦伶仃的艰难处境和秋景萧瑟触景伤情的愁苦心情。“万里悲秋常作客”,是就空间方面说;“百年多病独登台”,是就时间方面说。两句承上启下,凸现全诗主旨。在其中,诗人采用了悲情同质元素的叠加叙事手段,将千愁百绪之感聚增于诗行,造成一字一悲,一唱三叹,让悲情元素层层叠加,愁绪步步递进,将悲情的抒写发挥到极致,产生动人心魄的震撼力。
同样,年老体衰,垂暮之年,本已有“四十明朝过,飞腾暮景斜”的惊惧和“百年秋己过,九日意兼悲”的迟暮之恨,又加上了“多病”的长痛。杜甫在长安为官时就为疟疾、肺病、风痹、头风等病所困扰。但现时的诗人己年老体衰:“牙齿半落左耳聋”,连行路也困难:“缓步仍须竹杖扶”。人生中有千般痛苦,但对生命有深重影响的则为数不多,佛学中将其归纳为“八苦”。年老和疾病就是其中的两大人生之苦,每一种苦都是生命难以承受之重。“百年多病”是病老交加,垂暮与长病两重相叠,将悲情升级到人生大痛大悲。但诗人似乎并未就此满足,又乘势再下一层:“独登台”再将一种飘零远方,举目无亲,只身孤独的凄楚叠加于垂暮之恨,长病之痛当中,直把生命不济演绎得哀惋九绝,锥心泣血。
尾联抒写“文士多岁数奇,诗人尤命薄”的贫士忧愤怨伤。上句写自己艰苦备尝,白发弥添:下旬写自己贫困潦倒,末路穷途的人生悲剧结局。“艰难苦恨”四个字不仅指诗人为了“济苍生”、“安黎元”的志向,万里作客,长期漂泊,历经人生冷暖,遍尝世态炎凉的苦苦求索,同时也指诗人天涯沦落,衰年多病,孤苦伶仃的艰辛境况和身世遭遇。而这一切“艰难苦恨”的执著,所得到的除了一身的劳顿,满头的白发和贫困潦倒外,一无所有。高远志向的破灭,一生追求的徒劳,由此产生的怀才失意的怨愤,壮心未酬的失落,更加上天涯沦落,时光不再,岁月蹉跎,贫困潦倒的种种人生苦涩汇聚成一种殊深的感伤。而这种生命难以承受之悲因诗人衰年多病,戒酒停杯,无法排遣降解,使悲情更加酸楚和沉痛。两联四句,“无限悲凉之意,溢于言外”。
在抒写过程中,诗人将千般悲情意象层层叠加,万般苦绪步步递进,像压紧的弹簧,似充足了气的皮球,造成了诗歌文本内部强大的势能和紧张状态,形成“张力场”,使艺术品达成非常的语义或意境,也就是在艺术功能上的骤增甚至“核聚变”。从天涯飘零到白发弥添;从垂老多病到穷愁潦倒,诗人写尽了自己人生的大悲大痛,浓缩了生命的百恨千愁,并且将每一种悲情都演绎得透心彻骨,至深至极。
悲情作品承载了古代诗人乃至汉民族的感伤世界。无疑,生死的尖锐冲突,对大限的忧患和惶恐是“悲情”最为深层的抒情动机。传统农耕生活的习俗和观念习惯赋予了诗人强烈的时间意识和生死意味,而张力的营造,悲情的聚变更使作品荡气回肠,感人殊深。如是,《登高》以营造非常语义和意境的张力诗学模式的典型样本,成为“拔山扛鼎”式的悲歌。
作者简介:
周吉本,四川宜宾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文艺文化研究与教学,发表学术论文三十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