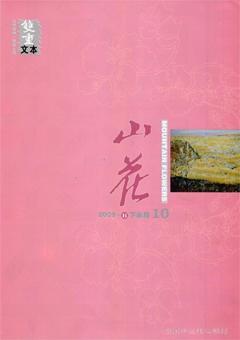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鲁迅研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镇,今天,沈从文研究己成显学,关于二人的比较文章也颇为可观。将鲁迅看成启蒙理性的先驱,视沈从文为反启蒙的精英,瞩目于二人的相异之处,是迄今比较鲁迅与沈从文的研究中最主流的观点与论述方式。从认识论角度臧否二人,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
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前有王国维、宗白华为生命美学筚路蓝缕,后有刘小枫、王乾坤等当代学人继起宣扬,方有生命美学越来越壮之势。它针对学界仅将哲学、美学视为一种知识性追问的缺陷,发出哲学与美学应具本体论意义,也即“形而上欲望”的疾呼,认为如果哲学、美学不以人的存在为根本的关怀对象,那么它们无异于伪学问,所以美学、哲学应是“生命的”。无论人们对文学有怎样不同的见解,“文学是人学”的观念已深入人心,文学与哲学、美学因此有内在精神的一致性:同样以人的存在为根本诗旨。只不过哲学以恩(概念、抽象与逻辑)的方式问鼎终极,而文学以诗(感性、具象与经验)的方式靠拢终极。
有论者指出:正是鲁迅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从认识论领域迈向了本体论范畴。同样,沈从文走上的也是一条审美人生的道路:他专注并出色描绘了“何为生命”、“生命何为”这个文学、哲学与美学的永恒主题、存在的元问题。他们在创作中建立起来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罕有的悲剧美学的世界。因此,本文试从生命美学的角度走进鲁迅与沈从文,更能深入理解两位作家精神世界与创作内涵的异同。
一切皆流
沈从文对天地充满深情。数片停云,满河橹歌,就能使他沉潜其中;他会把心爱的女主人公比作小兽物,将粗蛮的少年赞为小豹子:他会在小说中不惜笔墨描绘山光水色,让你疑心这也许是在做地方风物志。对万物的爱是楚人宇宙意识萌动的初刻,也是楚人旺盛的生命意识与深邃的悲剧精神产生的缘起。当个体处于宏阔浩渺的时空之中,必定会有孤独无依的苍茫感受。与宇宙意识同时觉醒的就是对生命悲剧性的彻悟。因此,沈从文面对“明窗绿树,已成陈迹”会心下凄然:听几声小羊绵软的叫唤,几欲垂泪。沈从文对万物的赞美之下流露出的分明就是“日月忽其不淹兮,恐美人之迟暮”的感伤。这里,不得不提及“水”之于沈从文的深切影响。“水”在中国是一个满蕴深意的文化母体。古人对时间的流逝、生命有限性的认识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忧生之嗟”均与这一派清波有很大关系。孔子之“逝者如斯”、李煜之“流水落花”、张若虚之“春江花月”的感兴。苏轼“赤壁”悲风的抒怀,水、时间、生命流逝连在了一起。同样,“水”教会沈从文认识美、思索宇宙和人生,“水”带给他文字上的“忧郁气氛”、情感上的悲悯阔大。而对汤汤浊流,沈从文感叹千古不变的是流逝,万世不移的是寒暑无数次来临、四时循环交替下人类庄严残酷的死生,必得负担的那份悲剧性命运,于是说“历史是一条河”,沈从文“渺渺兮愁余”的宇宙意识未尝不是因水而生。“唉,上帝。生命之火燃了又熄了,一点蓝焰,一点灰。谁看到?谁明白?谁相信”我是谁?我存在过吗?我往哪里去?古往今来的诗哲们都思考过这样的思想母题。人无法违逆被弃的命运,无法逃脱在时间面前永远失败的罗网。我们可以将沈从文这样的认识读作——一切皆流。
当我们如此判断时,会很自然地想起鲁迅关于“中间物”的著名论断。它导源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却不是一个认识论意义上的命题。“坟”是鲁迅最爱用的意象,他不仅将自己的杂文集命名为“坟”,也将自己过去的一切看成刚筑起的一座座“新坟”,更视未来为“坟”存在。鲁迅在浓愁袭来、星光惨淡的暗夜追溯以往,感知一切皆如云烟过耳,不可盈握,也似乎全无意义,也许最真实的就是悲剧生命一路踉跄、不得不抵达的远方——坟。“中间物”意识出现在充满生之凄凉、遍布坟之意味的语境中,绝不是一个与人的存在无关的外物,而是与作家有切肤之痛的生存体验,其内涵首先就指向了存在论的本体意义。所谓中间物,不过是一个“向坟的存在”,人是随时等待死亡的瞬刻。如果有所谓的永恒,那么时间的流逝是永恒不变的;如果有所谓的终极,那么死亡与坟,才具有如此绝对与终极的意义。于是,我们仍可把鲁迅的如是观解读为——一切皆流。
作为一个终生以立国为志业的伟大作家,鲁迅不可能完全超越现实做彻底的形上玄思。他对生命本体的思索始终和对本民族文化的考察联系在一起。在鲁迅看来,讳言死亡的民族文化培植出国人“不敢正视人生的瞒和骗”的苟活哲学、喜爱虚设“大团圆”般“极境”的心理顽疾。回避现实的悲剧处境,从而导致了生命意志的萎缩颓靡,造成了国民性格中根深蒂固的惰性与奴性。
鲁迅愤懑于窒人生机的“吃人”文化,沈从文则因天生的楚人性情而须臾未离对时间与死亡的倾心眷注。当“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思想占据文明的神龛,南中国仍是满天神鬼巫风四溢。也许我们应该感谢这样的分庭抗礼,在神话的怀抱中吸风饮露更易接近世界的本真与生命的本源。所以李泽厚、刘小枫才会说是屈原进入了被先秦儒学忽略了的生命的形上领域。“我正感觉楚人的血液给我一种命定的悲剧”,此言说出了以思索时间与死亡,关怀人的存在为诗旨的巫楚文化对沈从文深入骨髓的影响。因此,同样洞穿了生命悲剧的本质,沈从文的篇什有如因“存在失去支柱”而发出的“天问”;鲁迅的小说近乎因看透“人性之坟”而唱出的歌吟。孔乙己、阿Q、魏连殳的死莫不有具体的历史、文化与现实的因素,而老船夫的溘然长逝、天保葬于水底的背后却是翻云覆雨的命运黑手。沈从文是“反高潮”的圣手。七老在初八日幸福地准备迎亲娶媳,也正是在初八日意外身亡。《旅店》里的野猫子将自己苦熬多季的青春奉献之后,却又永远地失去了爱人。也许过早过清过深地了解到“爱与死为邻”这一人生的真相,沈从文写这些生死悲剧时才会平静如常,没有鲁迅面对国人“拥抱”、“赏鉴”屠戮时所感到的忧愤与苦楚,不是大浪滔天般的悲壮,而是静水流深式的伤怀。
生如夏花
鲁迅与沈从文均从时间入手,确立死亡终极与绝对的地位,建立起生命美学的起点——毁灭感。“中间物”意识把人们虚无缥缈的彼岸幻想、对过去的仰慕,拉回到现实,拉回到感性生命本身,拉回到正视而非自欺、承担而非逃避、反抗而非接受的精神层面。它强调的是当下与现在,不承认与当下或感性生命对等着的独立实体与绝对实在。祥林嫂关心地狱之有无与本体论层面上的生命关怀无关。“也许有罢”,我的不忍于心的回答,无异于饮鸩止渴。“其实,究竟有没有魂灵,我也说不清”,则全没了企图粉饰生命真相的念头。中国人并不缺乏生的执著,但正如挂于驴子唇吻前诱其前行的红萝卜,生之动力来自于这可以想见却永无法碰触的来生。所以鲁迅疾呼:“仰慕往古的,回往古罢!想出世的,快出世罢!想上天的,快上天罢!灵魂要离开肉体的,赶快离开罢!现在在世上的,应该是执著于现在,执著于地上的人们居住的”。鲁迅自己就是身先士卒的“叛逆的猛士”:“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意去: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
世间万物美好,但人只是渺小尘埃,好比满天星河,万千世界中的微小沙粒。面对此景,沈从文的歌诗里怎能没有悲凉,它反映了沈从文对无尽空间的景仰与敬畏。但他如鲁迅一样并未因此寄望彼岸、畅想来生,而是希望释放所有生命的欲望与创造力,拼尽全力地生活在当下。是他让我们明白,水上山间恣肆怒放的情欲爱意、荒野僻壤里好侠尚武的狂野气息、浊浪滔天中回响的纤夫之歌,“生物中求生存和繁殖的神性”,才是湘西最深刻的人文,也是生命最深刻的印迹。“爱有生的一切”,沈从文是一个只为生命痴狂与寂寥的诗人,他对感性生命的刻骨相思当是震撼中国人贫弱心灵与生命的雷霆。
“逝者如斯”,面对生死,孔子悬崖羁束,追求的是“止于至善”、“以德配天”,张大了“善”与“天”的权利,带来了淹灭“我”与“个体”的灾难,留给人们的是如何在审山悦水中获得宁静感思与道德力量。中国文人入世失败后,药、酒、仙、情爱成为抚慰其心灵创痛的良药。但“这里有自然生命而无神圣生命,有自由但是没有人,有解脱但是没有救赎。它通过取消生命索取意义的方式来解决生命的困惑”,西人在“生存还是毁灭”间狼奔豕突,国人则在入世与出世间沉沦下僚。因此,无论是沈从文诗情画意般地描绘“林无静树,川无停流”的生命本质,还是鲁迅深邃凌厉地揭示“向坟而在”的人生真相,都志在开启人类死亡意识的觉醒。而他们对感性生命至死靡他的爱,又使当下获得巨大的存在价值。立于现实而反抗死亡,从而获得本真的自我,真实的“在”,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与自由,也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限与永恒。海德格尔将此种人生态度称为“先行到死”,这不无悲怆的存在之美诞生于“真”——存在之无蔽中。对时间的重新认识,死亡意识的确立与对感性生命的眷恋是通向真正人生的道路。这注定是痛苦的生命之旅,然而你无法回避它。
冥思死亡
鲁迅在《野草·题辞》中写道“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远非空虚。”《野草》是冥思死亡的一部奇书。墓碣这块本该记录死者生卒、身份、功德的盖棺定论之碑,却铭刻着已死者最深挚的人生体验与最惨烈的灵魂搏斗。主体的历史性、现实性被模糊,取而代之的是对个体存在的哲性思考。同样,在《烛虚》、《长庚》等散文与家书中,沈从文凸显的也是一个蹙眉颦首沉思生死的诗哲形象。他指责庄子归自然,是忘却生死、佯作解脱;他赞美的是先人届子“众醉独醒,自沉清流”的生命选择。他甚至将屈原比作“疯子”。在他看来,诗化想象与追求终极生命并为之殉道的人才配称为“疯子”,这是所有天才哲人应有的精神境界。鲁迅与沈从文并不是要勾销形上追求,而是反对栖身玄远,忽视感性生命,湮灭人之主体性以逃遁悲剧人生的各种逻各斯传统。
1948年于霁清轩消夏的长日写下的书信中,沈从文已透露出倾慕魏晋风度,意欲佯狂以避世的心思,“灯息了,罡风吹着,出自本身的漩风也吹着,于是息了,一切如自然也如夙命”。(此时的沈从文真如他自言:是一只在行进中无可停顿的船,在慢慢下沉。1949年,沈从文终止了创作,走下了大学讲台,这加重了他的精神危机,严重时竟欲自杀。这一度神经错乱、几欲自毁的经历不得不让人想起屈子“临沅湘之玄渊兮,遂自忍而沉流”的山奔海立。其实沈从文的行止颇费思量,他并没有如老舍、傅雷般地走投无路,有非死不可的屈辱。这不可自拔的自毁超出了一般读者的想象,也为与之相濡以沫的妻子所不解:“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沈从文倡扬生之激情恢复了感性生命的丰富,同时又以近乎自毁的方式抵达了生命的形上层面。屈子千年之下,我们又一次在沈从文身上听到了生命热情复又悲情的歌哭。张兆和直到整理沈从文的遗稿时方才真正了解他,“斯人可贵”然“斯人已去”,我们是不是觉得孤独铺就了沈从文的一生?注定孤独的还有鲁迅先生。水上忧郁的孩子沈从文与青灯影中枯坐的鲁迅是诚挚的弟兄手足,他们生前互有抵牾,却不妨碍他们去后在“生命”的净空中促膝交谈。对鲁迅与沈从文来说,威胁最大的“不是死亡,而是夜莺”。鲁迅屡次说自己“热爱流血和隐痛的魂灵”,热爱辗转于风沙中被生命风暴鞭打出的瘢痕。因为这将使他感觉自己“在人间,是在人间活着”。)这也许就是鲁迅与沈从文面对悲剧时最大的不同。当生命已没有更高价值时,“那么死亡就负有新的使命”,它见证这个荒诞世界中生命存在的纯粹,于是沈从文倾心自毁。当命运的面容露出它骇人的深渊时,鲁迅却义无反顾纵身一跳,跃入深渊,发出是生还是死的诘问。他服鱼肝油以强身健体,但又“希望生命从速消磨”与光阴谐逝。他在生死间挣扎,却始终没有选择死亡,但又无时无刻不在倾听死亡的心跳,执意扛着“人间苦”,从黑暗中挺身而出又头也不回地走入黑暗,硬唱凯歌。对于一个始终毫不犹豫地举起黑手痛饮苦酒的人,这都是在走向“自设的祭坛”,也是比断然赴死的人更难承受的苦痛与折磨,然而这也是于悲剧生命中发出的最坚强的乐观之声。
《墓碣文》中我“欲知本味”,要“抉心自食”、“自啮其身”,然没有什么能参透这“终极的本味”,即使连死亡也不行。所以我“疾走,不反顾”,拒绝死亡“成尘的微笑”。“战胜命运只有死亡,克服一切唯有死亡可以办到”,这是沈从文超越命运悲剧的方式。然而在《阿黑小史》中,沈从文赋予主人公癫狂的结局,是否意味着在沈从文眼中,命运是连死亡也无法超越的?它冷酷地君临世界、蔑视众生。安息之所安在,唯死而已。众多的诗哲都在悲剧生命的绝壁前选择了自杀。“墓碣”中的“我”与疯了的五明却拒绝了死亡可以暂时逃脱原罪般痛苦的虚无本体观,实现了悲剧的超越。然而五明仅仅是沈从文小说世界中的一个意外,“我”却有鲁迅的影子赋形。就精神探索的深度与广度而言,鲁迅远比沈从文要走得远、走得无所依傍,也走得伤痕累累,它必定是以放弃俗世幸福为代价的。所以鲁迅一生孤独、愤激、偏执,所有的作品都看得见死亡的阴影、听得到灵魂惨痛的呐喊。即使温暖如《女吊》、《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其酝酿与创作均在鲁迅病魔缠身、心情晦暗、觉大限将至之时。回忆的格调、温爱的心境、死亡的主题和谐又冲突地共融其中,正像罗曼-罗兰笔下的圣者——约翰·克利斯朵夫,他在渡过生命的最后一条河时说道:“主啊,让我在你为父的臂抱中歇一歇吧,有一天,我将会为新的战斗而生。”鲁迅逝前流露出的丝丝温情其实只是一次心猿意马的停驻,短暂的休憩是为了更辉煌的重生。充满温情的同时仍积蓄着深深的伤悲,战斗的锋芒丝毫未得消隐。他终将弃岸,永远漂泊。死亡始自鲁迅,“境界遂大,感慨始深”。
作者简介:
罗飞雁,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