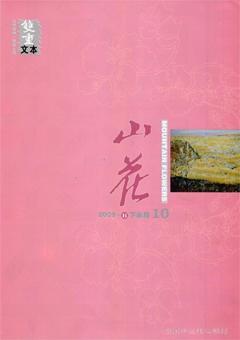父亲的岁月,老去的日子
7月7日上午十点,父亲咽下最后一口气,与世长辞。那天是农历五月十五,距他九十五岁寿辰只差两个月。
凌晨三点,我问父亲要不要喝水,他还摇头,到四点就喊不应了。从监测仪上看,血压、心律都还勉强,就是呼吸总是十五次以下,血氧饱和度只有四十多一点,医生用了呼吸兴奋剂也没多大作用,那时我就知道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自2007年8月确诊为前列腺癌晚期后,父亲就长期住在医院里,偶尔回家,也只是换换环境,陪陪同样年过九旬的老伴——我母亲也是重病缠身,身体极度虚弱,长年卧床不起,体重只有五十多斤。两年多来,疼痛一直折磨着父亲,他活得实在是太苦了!父亲落气那一刻,我本该号啕,但我哭不出来,心底有个声音在说“走了好,走了是解脱”。只是在我想给他合上嘴唇又无法办到时,我泪如泉涌,泣不成声……
儿子祭父,通常应该痛惜父亲离开了我们,但我宁愿说父亲离开的是这个世界——这个对他一生绝不公平更不慷慨的世界。中国人祟尚无疾而终,可是父亲却是大半辈子病魔缠身。从1960年患三十号病全身浮肿开始,各种难以治愈的恶疾接踵而至,硬是将这个当兵出身的汉子往绝路上驱赶,来到晚年,父亲被折磨得体无完肤,四肢凋残,就连体内的各种器官也没几样完好的,唯有生命在剧烈的疼痛中顽强延续。六十岁时父亲曾自叹“人过花甲,活也活得,死也死得”。七十岁那年也这么说,八十、九十还是这句话。可是近两年来他不这样说了,有好几次在剧烈的疼痛中叹息说他厌世了,一辈子活得委委屈屈的父亲已经期待着动身去另一个世界。
父亲黄体贤,1915年出生在贵州盘县两头河。我的曾祖父人称黄二铁匠,靠打农具、马掌为生,那个年代乡间铁匠日子还过得去,我祖父得以断断续续念了几个月私塾,他没继承父业,却去给兴义大军阀刘显世当了勤务兵。因为他体魄强健、勤快,会舞两下大刀,识得几个字,还用我曾祖母祖传的土方子治好过刘显世女人的肝腹水,当时还没做上督军的刘显世对他不错,在我曾祖母病重时许他退伍回家尽孝。
曾祖父和祖父两代省吃俭用先后买了几亩地,原想回归到土地上安居乐业,岂料就是这几亩地后来让我祖父弃家出逃,祖母悬梁自尽。
祖母是一个心灵手巧而又十分勤劳的农家女儿,那时祖父在外当兵,曾祖父已经年迈,曾祖母又多病,地里的活就靠祖母带着我父亲去干。祖母生了十个儿女,只有四个活了下来。父亲是老大,他平时要种地,赶场天要去卖自产的米糕,我都想象不出他的私塾和中学课程拿什么时间来完成。
十九岁时,父亲只身去昆明投考云南讲武堂,借宿在一个远房伯伯家。那个曾经得到我曾祖父帮助的伯伯进城以后看不起乡下亲戚,晚饭桌上闲言碎语实在不堪入耳,我父亲一怒之下掀了桌子愤然离去,在讲武堂附近找了一家小店落脚,每天揣两个烧饼到翠湖去温习功课。时值深秋,天气渐凉,父亲带来的夹衣扔在伯伯家又不愿回头去取,只好以跑、跳御寒。所幸那个季节翠湖游人不多,像他这样的学子也不止一个,没人见怪。
父亲从祖父那里继承了高大魁梧的身材,相貌又英俊,为他考上云南讲武堂带来便利。其间作为二手准备,他还报考了云南东陆大学,结果被两校同时录取。其时父亲正囊空如洗,他灵机一动,卖掉东陆大学那个名额,结了小旅店的账,买了几件冬衣,走进云南讲武堂那座“全世界最大的四合院”。
这件事在他后来遭受的好几次审查中都被“挂起”,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河南某地外调人员来查对,才知道早年买下父亲东陆大学录取通知书的人一直沿用黄体贤这个姓名,也就是说四十年来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两个同名同姓同龄同籍贯的黄体贤。
进讲武堂是父亲一生中第一个选择,他多舛的一生就从这里开始了。
云南讲武堂是朱德、崔庸健、武元甲、奈温这些总司令的母校,建校比黄埔军校早15年,我父亲在校期间改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五分校”。朱德曾把它称为“中国革命的熔炉”,就是说进步思想在那里是有生存土壤的。从乡间出来的父亲就是在那里了解到共产党的主张。毕业后不久就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后来又结识了地下党的同志。
我想地下党人交朋友绝不会感情用事,不经过严格的考查谁也不会和这个穿着马裤呢军装的国民党军官交朋友,他们一定是认准了黄体贤是个可信可用之人。抗战后期,父亲所在的部队要从重庆调往汉中,地下党组织要求他设法转回到贵阳为日后开展工作做准备。得到同情共产党的高级将领谭本良帮助,我父亲辗转在国民党十九兵团找到一个人事参谋的职位安顿下来。
我母亲出身在书香门第,父母亲虽然一个在城里一个在乡下,由于有点亲戚关系,自幼就是好朋友。1938年,母亲在青岩女师参加进步活动被中统关进监牢,父亲闻讯从重庆奔回贵阳,找了很多关系才把我母亲救出来带到重庆。因母亲学的是幼教,得以到宋庆龄办的“战时儿童保育院”就职。1945年母亲随父亲回到贵阳,在花溪小憩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为了方便日后的工作,父母婚后在公园南路租赁了一个小院,从家乡接来一个保姆,一个挑水打杂的男工,准备安置外来的地下工作人员。
弄不清抗战胜利后这一届中共贵州省工委是什么时候组建的,只知道1946春开始就有外来的同志陆续住进我家,按他们的要求,我父亲在城乡结合部比较清静的地段另找了一所独立的院落把家搬过去。那小院子周围是菜地,又有一条少有行人的阡陌小路直通父亲供职的地方,对于地下工作很便利。我父亲身着国民党中校军装,迎来送往都可以大模大样;那时省工委几位负责人都住在我们家里,从外县回来汇报工作的同志也常在那里落脚。我母亲写得一手漂亮的钢笔字,刻蜡纸自然而然就成了她的专职;父母亲的几个尚在读书的弟妹、侄女都担任了传递信息送达传单和地下读物的工作。
后来的党史资料把这所小院称为“花香路4号贵州地下党联络点”,照片还放在省博物馆长期展出过。有一本党史资料在写到一份重要的历史文件时提到“刻印是在花香路4号黄体贤家完成的”。据说那时地下党工委的机关在另一个地方,我不知道当时的“机关”应该是什么规模,机构如何设置,但我想花香路4号至少还应该有一个称谓:省工委宿舍兼食堂,而我那个在土改中被逼悬梁自尽的老祖母就是这个食堂不拿薪水的采购兼厨师,还兼望风放哨。
父亲清楚地记得他入党是在1948秋天的一个傍晚,但是后来他受处分时通知书上写的是1949年,不过这无关紧要了。1949年11月,当二野五兵团进入贵阳后,找不到党的地方组织,只听一位著名记者也是地下党一位领导的妻子说我父亲把地下组织成员送到盘县并由我祖父带路投奔祭山树罗盘游击区。二野五兵团的同志问明父亲的公开身份后颇为怀疑。把我父亲“请”到小上海软禁起来,直到地下党组织回到贵阳说明情况才放他回家。
父母亲曾说,解放军进城那天是他们最高兴最轻松的一天,觉得这些年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的生活总算有个美满的结果。1949年,父亲被任命为解放军二野
五兵团兴仁代表团秘书,以后又回省委统战部做干事,那是父亲一生中最惬意的日子。可惜好景不长,就在他从土改工作队回到省委统战部时,“三反”开始了,当时无事,可到1952年运动基本结束时父亲却无端受到一个“开除党籍”的处分!
那是父亲的人生转折点,就是那个处分,决定了他一生不再有欢乐。
据我所知,1950年或1951年中央政务院有一份文件,大意是说凡国民党起义人员中营长以上的旧军官如果已经入党的要劝其退党。“三反”开始不久,就有领导同志找我父亲谈话,劝他主动退党,理由就是这个文件。当时我父亲据理力争。他不属于起义人员,坚持不申请退党。
很可能因为父亲的固执得罪了更固执的人,那人暗地里较劲:不听话?看老子怎么收拾你!果然,没多久处分就下来了。岂止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简直是振振有词!罪行七条,条条都可以置人于死地。
耐人寻味的是七大罪行振振有词一大篇,个个字吓得死人,可是当它被否定时只需要轻描淡写。从1952年父亲被开除党籍到1980年恢复党籍,父亲在党外苦苦申诉寻求公平长达二十八年,书写的申诉状说著作等身一点也不夸张。而1980年那份平反通知书竟然只是薄薄一张打字纸,全文仅有二十八个字,换句话说老父一年的政治生命只值一个字。
然而,这二十八年父亲还有我们这一家是怎么过的啊!
我最清楚地记得的是那一回我们家第一次被抄家。那年我只有六岁,刚能记事。有一天夜里我忽然醒来就再也睡不着,心里慌慌的又不知道是为什么。那时候湘雅村还属于郊区,驿马路上连路灯也没有,夜里窗外漆黑一团,听得见河边水车的叽嘎声和附近田土里蛙鼓虫鸣,我就这样趴在窗前一直到天亮。一大早,抄家的就来了,祖父弄清这些人的来意后飞也似的跑了出去,母亲接过通知泪如雨下,她抱起我那尚在吃奶的二妹,拎一只小板凳坐到门口,把家让给人家去翻箱倒柜。
从“三反”、“五反”这个角度来推测,当时抄家第一个目的应该是钱,是浮财,可是一个解放前每到月尾要靠典当衣物来交房租买粮食,解放后和所有公职人员一起吃供给制的家庭哪里会有多少积蓄?抄家的结果让人家失望了,那一次抄家就搜出两样东西:第一件是一支生锈的手枪,后来我想父亲以前是军人,而且为地下党谋划的武装暴动提供过部分枪支弹药,在1952年那个时候家里有一把手枪看来算不上什么罪过,如果有罪他当时就该坐牢了。第二件是从一方带框的镜子后面找出两份文件,一份是地下党的不定期刊物《真实》,一份是省工委印发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都是我母亲亲手刻印的。当时,那个年龄稍大的抄家人员不小心把镜子撬破了,出于对这两份文件的敬意,临走时写了一张条子认赔。当然,写条子也就是走个过场,不要说我母亲,就是那人自己也知道只是写着耍耍而己,弄坏的又何止是一面镜子?
从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父亲都没回家,小小年纪的我不懂得为什么,只知道盼啊盼,盼父亲给我带洋画回来。也不知过了多少日子,等到父亲回家了,却一点欢乐也没有,那时二妹正在生病,老医不好,母亲已经不知垂泪多少回,见了父亲虽没抱头痛哭,可是父亲母亲连同祖父那几张愁苦不堪的脸已经描绘出家庭的变故,让我再也不敢开口要什么洋画。
不久我二妹就夭折了。
1952年父亲被调离省委统战部,到一个建筑公司去当施工队长。时值新中国成立之初,省城建设也有些轰轰烈烈,父亲从在兴仁代表团当秘书起就感到行政机关难以适应,被贬到这里反而觉得有一份使了劲看得见“形象进度”的工作,心里还轻松了一些日子。殊不知那个在暗地较劲的幽灵认为这结果对黄体贤还是过于慷慨,于是在一年多以后将他一次降七级——从十八级降到二十五级,调到砖瓦厂去做统计员。
现在的人们多半搞不清楚二十五级干部是什么概念:一个机关里的成员只要不是工人,最低最起码的级别就是二十五级。可是人家认为二十五级还是便宜了父亲,终于在大跃进来临时以支援农业的名义把他发配到一个农场里种地去了。
没有哪一级法律机构判我父亲劳改或劳教,他还没失去自由,可让他去的那个农场却多数是改教人员,仅这一条就足以说明有关方面已经把他打入另类。当然,那个假想的较劲者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命运,是父亲无法摆脱的厄运,也许这一切早在他来到这个世界以前就已经注定了……
农场我去过,离城十多公里,那时我进初中,走路要花三四个小时。父亲和十多个跟他一样稀里糊涂被发配到这里的人同住在小河边一栋简易的油毛毡棚子里,棚子用泥土筑成四面矮墙,山墙的上半部分是空的,透光且通风,所以也无须窗户,只有一个门洞让人出入。夏天还凉快,冬天可就同住在露天坝子里没什么两样了。为了挡风,每个人都把自己的铺位围成一个类似鸟巢的东西,用的是搜集得到的各种材料:瓦楞纸、水泥袋、破床单,不一而足。那年代还没塑料布,每个人的小笼子顶上都一式地覆盖着打背包用的土黄色桐油布,看上去居然有些整齐划一。
大跃进年代每个单位、每个人都想方设法要弄出些响动让上级兴奋一阵子,农场虽然承担着改教重任,也还是要做出点惊人之举。有一条小河沟流经农场,常年流量不超过零点五,不知谁突发奇想要筑一道堤坝把它栏起来做一个小水库。一旦水库形成,将要淹没这个农场本来就不多的好地,但不要紧,这个农场本来就不讲究效益。
很多年后农场改成了公墓,这个小水库还是个卖点,可是当年那一波已不年轻的干转农“工人”在没有任何先进设备的情况下,用锄头挖肩膀挑来筑成一道土堤是多么艰难可想而知。也不知是什么时候开始动工的,只记得到困难年间堤坝还只有个雏形。有一次母亲让我给父亲送点吃的去,他不在棚子里,我到水库工地去找,父亲正在那里挑土,他脚穿草鞋,一身都是泥,两粪箕黄泥显然太重,他躬着腰在泥泞中跌跌撞撞……那年父亲才四十多岁,可看上去已经有些衰老了。
父亲在农场里一共干了五年。五年,在人生旅途中算不上多么漫长,然而,就是这五年,他的身体彻底垮了。
父亲是1963年因病退职的,从农场跛着脚回家,带回六百块钱退职费、一肚子委屈和一身疾病,计有腱鞘炎、腱鞘囊肿、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肝肿大,还有与堤坝没关系的牛皮癣。
退职回家,算是他从1946年开始参加地下工作以来的一个人生段落。说是不再为五斗米折腰也行,反正是实在干不下去了,只好回家,回家来可没你种菊花的份,退职后再没有人给你一分钱薪水,要活下去得自己想办法。那不是市场经济年代,丢了工作要想再找简直就是做梦。父亲想好了:他在军校读书时学过剃头,退职回家就买一套理发工具走街串巷去给不愿上理发店的老人孩子剃头。
想归想,做起来却没那么简单,父亲以前给同学们刮光头推平头还行,剃学生头、剪偏头怎么也做不好,拿我们三兄弟还有常来家里的同学做了好多回试验也剃不好,俗话说少年木匠老阴阳,学手艺年纪大了还是吃不通。
20世纪60年代初我们这个家是父母、祖父加上六个儿女一共九口,父亲自从降级后每月三十多块钱薪水再没涨过,母亲当幼儿园园长可以拿到六十来块,就这点收入养活一大家人实在捉襟见肘。从进初中起我每个假期都必须去敲石子、割马草为自己挣学费。父亲退职后家里更窘迫了,就母亲一个人的工资,每个铜板都掰做两半也不能解决问题。母亲倒没叫苦,父亲却越来越心焦。
父亲后来养过鸡,买了三四十只鸡仔,无论怎么细心还是一只只死掉:后来养猪,那猪更滑稽,只见掉毛不见长大,喂了七八个月居然不足三十斤。一气之下宰了自己吃,吃完才听邻居一个老头说这种长不大的猪苦胆里肯定有猪砂,那东西比金子还值钱。苦胆呢?
父亲说狗叼走了。
1965年我高中毕业,那时候已经开始提倡上山下乡,学生会的人到家里来动员,无非是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之类,我父亲听来人把话说完才平静地回答:你们说的我都懂,我的情况你们是知道的,这几个儿女看来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了,就让他们在城里找个饭碗吧。事隔好多年我才知道,就因为这个“情况”,班主任在我的报名单上填了“建议不予录取”。大学既无望,只好进一家建筑公司学木匠,学徒工资低得可怜:每月十三元!不过蚂蚱也是肉,再低也算是有收入了。
当学徒不到一年,我的手艺已经胜过我师傅,可以自己接活路了。那时公开接活叫“飞机工”,单位上察觉了要处罚的,只能悄悄干。这下父亲总算找到点事做了,他虽然腿瘸,但手还没萎缩畸变,还有些力气,我接回活路后白天要上班,父亲就帮我改料子,刨粗坯。有一次有个地下时期的老同志从外县来贵阳上访,到我家投宿,看见我父亲光着膀子嗨哟嗨哟刨木板,大为感慨,说这样子一点儿也不像中央军校出来的军人,倒像个老木匠。
其实父亲光着膀子刨木板还算体面的,“文化大革命”中三天两头被揪去挂着牌子游街的形象就更惨不忍睹了……
比较起来1952年那次抄家只能算是搜查,1966年那次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抄家。来的是街道办事处造反派和贵阳第十二中的几十个学生,带着梭镖、棍棒、锄头、铁撬、语录本和几辆板车。我们家屋子在一块洼地里,学生们高呼着口号来到我家时四周很快就站满了围观的人群,母亲不在家,运动开始不久她就得不到回家了,父亲和当年抄家时母亲的表现不一样,他站在屋前,扬着头,用尽可能大的嗓音声嘶力竭地向四周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们讲述自己的革命历史,讲述自己的冤屈。
那是真正的挖地三尺,屋里铺的青石板全部撬开都不算,还把泥土刨开看看地底下埋藏着什么。其实家里一贫如洗,有些可能惹麻烦的东西运动一开始就烧掉了,比如军阀刘显世书赠我祖父的“墨宝”,还有一些父亲身着国民党军装的照片,特别是那张父亲和蒋经国的合影,那是当年蒋经国来贵阳检阅青年军二〇五师时接见做值星的父亲留下的。
不过折腾了大半天的抄家队还是有收获:他们把当年地下党存放在我们家的几千册进步书籍当做“四旧”,用两辆板车装着,挥舞着语录本高呼口号凯旋,留下如同轰炸之后的现场,屋里屋外到处是土坑土堆。
从1952年开始,父亲就不断向各有关部门、有关领导递交申诉书,有好多个夜晚,父亲在灯下把申诉改来改去,总担心有什么重要的情况被遗漏,总想把词语写得更有感染力。另外的无数个夜晚再由母亲或我用复写纸把改好的申诉一字一句誊正。在我印象里,这一次誊的和上一次几乎一模一样,下一次又和这次没多少差别。
这种申诉前后交上去数百份,始终是泥牛入海无消息,极有可能的是那几百份申诉根本不曾被翻阅就扔到字纸篓里。据我所知,1946年以后这一届贵州地下党没有哪一个领导在解放后手中有权,他们自己的政治生涯都步履维艰,当然腾不出手来拉我父亲一把。我记得大约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赋闲在家的前中共贵州省工委书记把当时还健在的地下党同志召集到我家,当众宣读了他撰写的一份关于中共贵州地下党历史情况备忘录。前工委书记感到自己已经病入膏肓,恐不久于人世,可是他的这些部下全都在落难,“文化大革命”中个个挨整没有一个逃脱,不知什么时候才有可能拨云见日。写这份备忘录的用意就在于时机来临时,还活着的人要按照它去向有关部门为解放后屡遭冤屈的贵州地下党讨个公道。那天的气氛与其说是悲壮不如说是悲苦:事前就说好,到我家来时各自分头前往,不要邀约:走的时候也要陆续出门,以免引起左邻右舍的注意。前工委书记身体状况确实很差,读文件时有气无力,声音颤微微的。他宣读完毕后问大家还有没有需要补充的,好一阵子谁都没有说话,只听见有人压抑地啜泣。
那天的情景让我明白:贵州地下党的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我父亲再写多少申诉都没用。事实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胡耀邦批发了一个关于解决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的文件,我父亲的问题才被有关部门提上日程。
那时我父亲已是年近古稀。
拿到平反通知书那天,父亲、母亲还有我们子女,谁也没有欢呼,一点喜气也没有,反而是情绪沮丧、心情沉重。那时候父亲的类风湿已经很严重,疼得厉害,手指关节开始变形,地下党的一个老同志给他弄了些草药包着。他用缠满绷带的手捏着那张便条大小的通知看了一眼,就放回茶几上,目光呆滞,什么也没说。隔了好久,我总算想到一句不轻不重的话:以后有公费医疗了,爸爸得赶紧去把手治一治。
在父亲的冤屈得到昭雪以前,疾病早就对他构成威胁,长时间没有公费医疗庇护,各种疾病肆无忌惮,来了就不去。好像是命里注定他这一辈子要在苦难中度过,八十岁时他拄着拐杖一步一挪走在路上竟会被一辆中巴撞倒在地,撞得一身是血还断了两根肋骨:九十岁时在自己家里从电脑桌前坐到床上没瞄准位置,跌坏了股骨头,只好动手术换了一根人造的;2007年确诊为前列腺癌晚期之前几大医院一直把他当成前列腺增生来治,治了两年多,保列治、哈乐吃了几十斤,毫不见效。最后这次入院,他已是元气丧尽,将近一个月吃什么吐什么,全靠点滴维持,医生说,看来你父亲这一次是出不了院了,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父亲走了,从医院动身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们不敢让母亲知道,她老人家也是元气将尽,寸步难移,要是把她搬到父亲灵前,可能她一分钟也活不了。所幸——本该是不幸——母亲的老年痴呆已经很沉,偶尔问及父亲,那念头也是倏忽而过。瞒一天算一天吧……到那一天,我灾难深重的父母会在另一个世界重逢,那时父亲的腿一定不再瘸,手一定能伸直,母亲也会重新健步如飞,就如同当年他们在花溪小憩举行婚礼时一样。我相信,在那边他们将不会再遭受苦难。
作者简介:
黄祖康,1946年出生,19岁前读书,19~28岁在建筑公司做木匠,28~36岁在剧团里拉小提琴,36~40岁在该剧团做编剧,40岁以后在《山花》当编辑,一生从事过的职业相去甚远,写过一些文学评论。60岁退休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