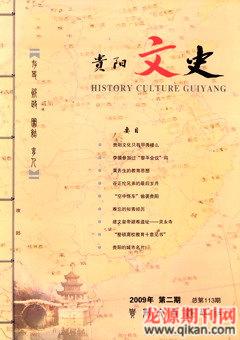走出来的作品
周 静
有人说王大卫的作品是走出来的,恐怕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他52岁就从仕途上走了出来;二是他在《天地无极》和《寻找那些灵魂》写作过程中分别深入到云南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江并流区域和云贵乌蒙山区徒步寻访的时间竟达一年之久。
云南报业集团《大观周刊》总编辑杨鸿雁在采访王大卫时说:“我觉得你的内心世界是非常复杂、非常丰盈的,如洛桑益世活佛所说,‘蕴含的东西太丰富了”。
A、走出红尘
王大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就从我退休后谈起吧,那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分水岭。
王大卫2000年新世纪伊始提前退休。比法定退休时间提前8年,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早在青年时代,他就有了一个梦想、一个做写作者(作家)的梦想。但他的选择,并没以他的意志为转移,他最后被命运颠簸到了仕途上。既然走上仕途,他也认命了,在仕途上认认真真、尽心尽力。然而经历了十多年仕途生活后,他越来越觉得不适应仕途生活,先是萌生退意,继而果断做出抉择。于是,他于2000年毅然离开了生活十多年的“围城”。同年,他对自己10多年的仕途生活做了个总结一出版了《追赶生命》。这是他的第一本书。而王大卫认为,“比这本书更重要的是身心自由了、轻松了、清静了,有属于自己的空间了,可以有时间有精力有条件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了。”也许是“天音”成全他,从2001年到2008年这七、八年间,他先后出版、再版了4本书。第4本书出版时,正好是他的“法定”退休时间。王大卫说,“这一天,我心泰神宁,甚至洋溢着一种喜悦感;我为8年前那个明智、果断的选择做了一个深长的祷告。”
王大卫在《追赶生命》里说:“我的人生在路上,天堂也在路上。”所以,他要坚执去寻找他的天堂。他的第二本书,就叫《寻找天堂》。
外表平静内心炽热的王大卫究竟要寻找什么样的“天堂”呢?他说:我写作,很大程度上只是完成一个内心的使命,了一个夙愿。因此,他对题材选择十分审慎,甚至寻寻觅觅、风雨兼程去寻找。他说:“我寻找、选择的题材,必须是对人类历史、文化、教育、精神等领域有杰出贡献的人物,简言之,就是对人类文明有杰出贡献的人物。人类文明需要志愿者、需要有使命感的人共同去构建、推动。”
王大卫认为,写作是一种与读者的知识、思想、心灵交流,既然是一种交流,就应当把真善美的信息、思想及其理念传达给读者。他说:“好的作品是对人类文明的启迪和助推。好的作品就像是在幽暗巷道里点亮的一盏明灯。”也许是认真读了王大卫的书稿,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国际纳西学学会会长白庚胜亲自为王大卫的《天地无极》写了数千字的序言“与天堂同在”。
我在采访王大卫前,阅读过他的三本书,每一本书,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乃至令我产生一个巨大的疑问:王大卫怎么从未获过奖?
王大卫大概看出我的疑问,平静地说:“我不获奖是正常的,获奖反而不正常了。首先,是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决定的;其次,我从未送作品去参加评奖;其三,我的作品不仅是非主流的,而且内涵了所谓‘敏感思想。”
出于某种意念,记者问王大卫:面对社会生活,有什么感慨?近期还有何写作计划?
王大卫沉默一会后说:我用心理和精神“元素”,构建了一个属于我自己的、远离尘世的生态环境,一个属于我自己的精神家园。心态平静了,情绪亦平静下来。于是我又开始寻找题材。我想寻找一条江、一个人的历史来反映大历史大社会,抑或说,让一条江、一个人来见证一段历史一段社会命运。目前,我正在收集相关资料,天气好些后,就会出行。我认为,好的作品,是行走、体验、感动的结果,是文学、思想与理论综合的结果。纯粹的文学写作,完全形象思维的写作,很难出有深度有生命力的作品。
王大卫是我所采访的“影响力人物”中唯一没有获得过任何奖项的作家,但这并不妨碍他的《寻找那些灵魂》和《天地无极》成为央视电视片的文本,也不妨碍他的图书在北京、上海、浙江、云南、深圳、香港等地区有不少的读者。在北京王府井书店、北京国际书店乃至在丽江飞机场侯机厅和海拔4000多米高的玉龙雪山景区休息大厅,都有王大卫的《寻找天堂》和《天地无极》。
王大卫应该感到欣慰,社会也应该感到欣慰。
B、生命之旅
2001年8月,《追赶生命》出版后,王大卫想休息几天,于是,去了云南丽江。在丽江,他看见很多书店里,都有关于美籍奧地利植物学家、探险家、学者约瑟夫·洛克的图书,便买了几本,比如《沿着洛克的足迹走进香格里拉》、《孤独之旅》、《马蹄踏出的辉煌》、《灵魂居住的地方》等。每天下午和晚上,他都在古城“谈世乐”客栈里阅读这些图书,尤其是在阅读了洛克的《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后,他感动了,决定沿着洛克半个多世纪前行走的主要线路,深入到云南滇西北三江并流区域去。他想去发现、挖掘一些更动人、更深刻、更鲜为人知的东西,同时,以一种独异的形态、独异的理念来表达他认为是“深刻”的东西。
基于这一思考,王大卫在新世纪到来之际,便先后五次去了云南,总计行程数千公里,历时近一年。除了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及其流域。还远行到了与缅甸、西藏接壤的独龙族人聚居地区——独龙江流域的龙元,绣切和孔嘎。
这是一次体验式苦旅。王大卫不仅对滇西北三江并流地区历史、文化、自然生态进行了深入考察。对生活在这一地区的纳西族、彝族、藏族、傈僳族、普米族、独龙族、怒族等民族的历史文化、生活习俗、民族风情,也进行了深入采访。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王大卫对纳西族、傈僳族、独龙族、怒族人的未来命运,投入了深挚的关切。除了对这些民族做了缜密体察之外,还为这些民族的未来发展做了思考。对生态环境的潜伏危机,王大卫也在忧虑的同时,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当他在勐腊南贡山和南腊河流域的纳卓、勐伴、曼蚌看到大片的树林被砍伐、烧毁时,竟发出了“不是恐惧大自然,而是恐惧人类自己的愚昧与野蛮”的仰天叹惜。
在云南时,云南美术出版社旅游编辑部主任张晓源对王大卫说:“不要再拿生命去跑了,多少人为此耗尽了一生积蓄,有的甚至一去就走上了不归路……”
王大卫说,他听了张晓源的劝告后,眼睛湿漉漉的。他感谢张晓源,感谢他的肺腑之言。但他回答张晓源:“我的生命在路上,我的‘天堂亦在路上;离开思考、离开行走,我会感到虚空,像天边的流星。瞬间即逝。”
两年后,王大卫的《寻找天堂》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出版社给了他9%的高版税。出版社的评语是:这是一本图文并
茂、风格独异、洞察深刻的记述云南滇西北历史与地域文化的精致之作,优雅的描写与理性的思索,令人赏心悦目、深长思之。
2005年,香港文汇出版社出版了《寻找天堂》修订版《天地无极》(上下集,繁体版)。2006年,中国工人出版社又买断版权在内地出版了简体版《天地无极》。
《天地无极》(繁体版)在香港印制时,王大卫又风尘仆仆、跋山涉水去云贵乌蒙山区了。他又物色到一个具有史诗般意义的题材:一个近百年前在云贵乌蒙山区创建“文化圣地”的英国传教士塞缪尔·柏格理。柏格理1887年3月到中国,在中国西部云南和贵州贫困地区艰苦卓绝地生活、工作了28年,1915年9月,因救助贵州威宁石门患伤寒的苗、彝族学生,溘然长逝在那片巷凉、贫瘠的土上,年仅51岁。柏格理先后在滇、黔毗邻的昭通、彝良、威宁等地区传教、办学、办医院历时28年。
其实,记述洛克、柏格理的图书已出过不少,但王大卫说,他想用纪实、文学与学术交糅、整合的样式来写,以纪实散文为主要体例。
资料、提纲以及确认文体等准备工作完成后,他毅然拖着他那条患有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右腿,往中水、石门、彝良、昭通等地区去了。去乌蒙山区采访、考察,与去云南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和独龙江流域采访、考察一样,不仅异常艰苦,而且充满了危险。
当我问王大卫,为什么偏偏要选择到这样遥远、苍凉的地方去?王大卫说:“我对柏格理、对那段发生在近百年前以石门为中心的文化现象的追寻,完全是基于两个感动:为柏格理和他的同事的献身精神感动;为含辛茹苦深入到石门和乌蒙山区去考察的中外学者感动。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他们的精神品质和生命意义,已远超越了物化世界”。
因为这两个感动,王大卫在50多岁的年龄段,数次深入到那片交织着贫困、苦难和神秘的高寒山区去。每次回到贵阳家里,都是心力交瘁、疲惫不堪。
也许是被王大卫的精神所感动,也许是被王大卫书稿中记录的那段令人欲泣的历史所感动,香港文汇出版社在出版了上下两册的繁体版《中国石门》后,又跟进出版了简体版《寻找那些灵魂》。
为了写作《天地无极》和《寻找那此灵魂》,王大卫先后在滇西北、黔西北高山大河、荒原草泽上步履蹒跚地苦行了近两年时间。王大卫说,“其间苦乐悲欢,只有我与同行者体悟、心悟最深。这两次追寻,这两次生死之旅,使我对洛克、柏格理以及人类精神和人类生命意义的认识,产生了一个飞跃性的思考,乃至演进为有明确价值取向的生命之旅。”
C、天道酬勤
令王大卫“稍感欣慰”的是,他的苦旅是有结果的。他自信地认为,“每一个看了这几本书尤其是看了《天地无极》和《寻找那些灵魂》的读者,都会与我行走和写作时的感觉一样,激情、温馨、感动地体会到审美、情感和思想的颤动。”
王大卫的自信,获得了积极反应:
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国际纳西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白庚胜在读了《天地无极》后写道:毫不夸张地讲,作者对纳西族历史及现实的透视是空前的;作者让我们享受了太多的雄奇: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独龙江的风雨阳光;玉龙雪山、格聂神山、梅里雪山有灵性的生命;甘孜高原与天空是“亲密融和在一起的,仿佛一伸手就可以触摸到天空”;理塘的天空,“既纯净又温柔且强烈,纯净是像蓝眼睛一样清澈的苍穹,温柔是飘逸的云影,强烈是太阳的光芒”……《天地无极》是我至今所见到的记述洛克、记述纳西民族、记述三江流域自然与文化的不朽佳作。(《天地无极》序)
贵州省文联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何光渝在读了《天地无极》后,感慨地写道:王大卫踽踽独行于滇西北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江并流区域纳西、傈僳、独龙、藏、彝、怒等民族世代栖息之地。这一自费进行的备尝艰辛的旅程,历时四年:行走、求证、核实、写作,再行走、再求证、再核实、再写作——单是玉龙雪山下一个小小的雪嵩村,就先后去了五次!
显然,大卫并不仅仅只是喜欢或满足于“在路上”的感觉。若不是全身心地去行走、追寻,这书里那些出自心灵、坦率真诚的文字、并非人云亦云的感触和识见,怎么可能产生?怎么可能在质朴生动的文字描述和丰富传神的图像表现中,记录、再现出如此丰富而真实的历史和现实生活场景?这样的写作,是对历史文化的抢救,是对民族文化的生动保存,明显地带有“史志”性的意义,具有非常的文化历史价值。在这部感觉是一气呵成的长篇纪实散文中,虽不能说是篇篇“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却也是才情洋溢,笔墨挥洒着知行与智性。我从其间读到的,不仅是牠的文笔、文饰、文采,更还有他的文情、文气、文理,他的精神人格的积淀,文化旨趣的能指所指,以及对人生哲理的不舍探求。(2006年2月10日《贵州日报》)
贵州大学中文系教授黄俊杰在《忧患于天地之间的“思想织物”——评王大卫的长篇纪实游记(天地无极)》(《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03期)中说:《天地无极》叙写如行云流水既灵巧又自然,更重要的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情境撞击生发出多少随缘、随观、随感、随思、随想的心灵火花,有如不同色彩的横线来回穿梭于这块思想织物之上,让读者看到了“一片淡淡的微光已经照亮了这张思想织物的背景,它的另一端则还深锁在浓云密雾之中”。《天地无极》以其精致的“思想织物”反作用于“本事”,让读者思考着“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在缓慢地改变着思想颜色的伟大运动在不远的将来仍将会继续么?在时间十分活跃的织布机上命运之神将在这块织品上织出何等颜色呢?是白的?还是红的?”——我们一时还说不上来。但在全球化语境下的忧患意识,却充分地显示了一位知识分子作家所拥有的时下愈益难能可贵的正直品格。
贵州民族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新闻传播学教研室主任喻健(子涵)教授,读了王大卫的《天地无极》和《寻找那些灵魂》后写到:王大卫纪实散文的诗性,是由他的“行走”而产生的。“行走”意味着“寻找”,寻找一种灵魂、一种精神、一种价值、一种信念、一种理想,这“行走”与“寻找”的本身,就充满着强烈的诗意的壮举。他的行走是沿着一条历史的路径进行的,《天地无极》是沿着美国学者洛克半个世纪前在滇西北三江并流地区生活与工作28年的历程线索进行的。《寻找那些灵魂》是沿着英国传教士柏格理近百年前在云贵乌蒙山区创建中国西南“文化圣地”的足迹进行的。大卫的行走是极其艰难的,但是由于心存博大的爱心,于是将艰难化为了愉悦,化为了力量。在王大卫看来,人的一生是行走的一生,“人类文明之旅,既涵盖了痛苦涵盖了希望也涵盖了幸福。”他的“行走”是为了“寻找”,因此,“行走”与“寻找”,便构成了王大卫纪实散文创作的核心内容,而这种核心内容正是一种诗性精神的呈现,在自然与人的关系中,他坚信自己寻找到了一个关于生命、精神与灵魂的丰富世界。正因为有这种人文精神的支撑,所以才有苦旅与写作的强大力量。王大卫的纪实散文也是“神圣忧思录”,也是“大山的呼唤”,通过考察、体验,他为文明的衰落、生态的破坏和苦难的蔓延而痛心疾首。这种体验与思考是深刻的,这种痛心与呼唤是真诚的,作家的良知与责任不由自主地涌流出来,而其诗性也奔涌于文字,直通心灵,直逼事物的本质。(2008年4月25日《贵州日报》、2008年第8期《民族文学》)
《寻找天堂》、《天地无极》出版后,《光明日报》、《西部开发报》、《云南日报》、《民族时报》、《春城晚报》、《贵州日报》、《贵阳日报》等多家报纸及时予以了报道,并发表了相关评论文章。云南报业集团《大观周刊》总编辑杨鸿雁对王大卫做了长篇专访(《天地无极》访谈:关于《天地无极》的对话)。中央电视台“发现之旅”拟定了2009年摄制纪录片计划。
《中国石门》(繁体版)和修订版《寻找那些灵魂》出版后,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和香港电视台分别做了专题片和纪录片。
行走、阅读、思考与写作,已是王大卫追求的一种生命形式。我们祝福王大卫及其作品。一路好走。
(作者单位:贵州日报)
责任编辑:罗万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