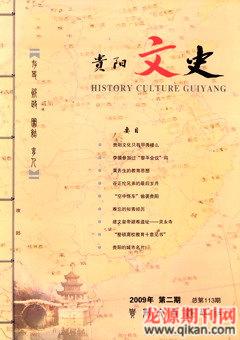我在北平的那些日子
张楚原 张启安
迈入晚年,过去经历过的许多事情已经黯然失色,能长期留在记忆中的并不多,而我少年时代曾经在北平的那些日子,对我而言真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我是遵义湄潭人。1932年,我初中毕业,时年16岁。为供我读一点书家里已经够艰难,自己实在难以开口向整日劳作不息的父母亲提出读高中的事。同年9月,我与十姐经人介绍到湄潭的鱼泉镇小学教书。到次年开春,学校生员大减,需要的教师相应减少,我刚教一个学期的书就失业了。此时,正值广东燕塘军校招生,军校不收费可节省家庭开支。几经请求父母。他们终于同意我去报考军校。
1933年3月的一天早上,我辞别了父母,踏上了赴广东之旅,几经辗转到了广州堰塘军校,因军校已提前招满,报考愿望落空。在人地生疏、举目无亲的异乡,我踯躅在街头,想在车站、码头找个小工做,积攒点回家的路费,由于语言交流障碍而不能遂愿。在天字码头客运站我无意中瞥了一眼轮船时刻表,其中有广州至天津的客轮,五等散席票价便宜,于是萌发了何不乘船经天津去北平找五哥的想法。五哥时任军政部长何应钦的侍从副官。3月,何应钦以军政部长兼北平军分会主任,五哥随其到了北平。主意定下来即买了船票,当天下午乘江轮到黄埔码头上了海船。行程中,船在香港、厦门、上海、青岛等地停靠过,经三天三夜达到天津塘沽港,换乘小船进天津。
我赶上天津到北平的火车,到前门车站下车出站即打听北平军分会的所在地。刚开始问,一位拉洋车的,不容分说,把我推上车拉着就跑,到了一座红墙黄瓦的门楼前,拉车的人告诉我,军分会到了。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中南海新华门。我向卫兵讲,想进去找我哥哥烦请通报一声。传达室里面有位军官好像在找信函。他连头都没有抬,用国语问我,“你哥哥是谁?”我回答,“我哥哥叫张涛。”他抬头看了我一眼改用贵州话问,“你是他的兄弟?”在得到我肯定的答复后,他拿起电话摇通总机接副官处,听见他说,“文渊,你兄弟找到这里来了。”五哥的字他都知道,想来他们很熟。他挂断电话告诉我,“你哥哥快下班了。他叫你先回家去。”拉洋车的走上来讨车费,我也不知道该给多少,后来这位军官代我付了车费。他对拉车的人说:“你知道流水音吧,送他进去。”洋车再次载上我,绕过一扇大影壁进了园子后景色豁然开朗,高墙阻隔了外面的喧闹,波光粼粼的湖面上映着参天古木的倒影,湖心有一小岛,后来我才知道是曾经囚禁过光绪的瀛台。顺着南海东行,湖滨一长满青草的土台上假山托着一座亭子,里面一位身著旗袍微微有些胖的妇女怀中抱着小孩,傍边还有一位用发网将头发挽在脑后的妇女,穿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浅兰色父母装,她对身著旗袍的那位扬了扬下巴彷佛说了点什么,两人朝我看了一眼,相视笑了笑。不经意中,洋车将我送到了绿树环抱的庭院建筑群前就回去了。我不知道五哥住在那座院子,不敢贸然地去敲那些镶着半圆形铜钉的红门,只能静静地等待。不一会,远远的一位军人从中海和南海之间岛上朝我这边快步走来,渐渐地看清楚了是五哥。五哥是1926年春节刚过就去广州投考黄埔军校五期,离家后一直没有回过家,我们已有7年未见面了,弟兄见面百感交集。五哥领着我跨进了庭院进了屋,他叫了声,“你看谁来了!”没有人应答。他接着对我说,“你五嫂可能还在园子里。”话音刚落,就听见有人在说,“先生都回来了。”这时看见方才在亭子里抱着小孩的两位妇女进来,五哥给我介绍是五嫂和他们家请的保姆严妈。五嫂爽朗笑了笑,说,“严妈方才还指我看,洋车拉进来个土包子,原来是七弟来了。”五哥又打量了我接着说,“怎么这身穿着?”我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的这套旧西服是在香港停船时买的,脚上的剪刀口布鞋从家里一路走来已经破损。吃过午饭,我洗了澡,换上五嫂找来五哥的旧衣和鞋。五哥叫严妈把我的旧西服扔了,安排五嫂和严妈带我去西单的商场买了一套学生服和一套夹克衫。那天我还给五哥说了洋车的车费是那位打电话的军官付的,要还给他。五哥告诉我不用管了,以后要我叫他龙大哥。
后来,我渐渐熟悉了在园子里与五哥交往的人。那天给我付车费的叫龙念钊,是贵州朗岱(现在的六枝)人,与五哥同是黄埔五期同班同学,一起参加北伐东征、龙潭战役,黄埔五期的学生大量在龙潭战役中阵亡,是早期黄埔军校毕业生中较少的一期,他与五哥遂成生死之交,现在也在北平军分会副官处工作。他常到家里来玩,后来我与他熟悉了,他悄悄向我打听十姐的情况,我告诉他,“我家十姐人长得漂亮,歌也唱得好。”我离开北平以后,再次与他见面时,他已经成了我的姐夫。在北平军分会还有几个贵州人,随着我在中南海居住的时间长了和他们渐渐的熟悉。时任何应钦政治秘书的刘建群,就是那个时候认识的。1946年11月,刘建群竞选立法委员时我陪同他回过遵义。还有后来在张涛任八十九军军长时任参谋长的赵文华,有一次我跟随一批贵州老乡去西单吃饭,那家餐馆的宫爆鸡做得不地道,他亲自下厨做了这道菜,此后餐馆的菜谱上把这道菜改为“赵先生鸡”。
来北平都几天了,想继续读书的事还没有什么消息。我很少上街,整天在园子里,沿着中海、南海不知道都绕了几圈,除了居仁堂有卫兵守卫,其他的像清音阁、赢台等地方都可以去。有时向中南海管理处的那位老头借条船划。一天,我看见老头与一位军官争吵,凑拢去看,原来那军官在海子边偷着钓鱼,老头要没收他的鱼杆。当时中南海里面管理还是比较严的,包括一些人把园子里的花钵搬进自己寓所都会被管理处的人追回。
很快,五哥托人给我联系到一所中学,经过简单的考试,学校同意我去插班进高一。军分会门禁森严,为了出入方便,五哥给我找了个军分会的证章,佩戴这个证章乘电车、大巴可以免票。我倒是比较注意分寸,证章只是出入使用,平时取下来放在衣兜里,极少去乘电车、大巴。五哥对我的要求近似“严酷”,除了每天必须完成的功课,还要求我背《大公报》上每期登载的社论。那正是长城抗战中国军队在喜峰口一带抵御日军打得激烈的时候,《大公报》上的社论都是针对时局呼吁一致对外全面抗战,饱含爱国激情具有战斗力的文章。此时居仁堂那边经常通宵达旦亮着灯,五哥常常很晚才回家,我不敢随便乱跑,做完功课,熟读报纸上五哥指定要我读的文章以备他查问。五嫂晚上常去找同住在园子里的女眷们,多数的时间家里就剩下我和严妈。背书渐渐犯困时,严妈总会悄悄地走到我的书桌旁递给我一串冰糖葫芦或几颗糖炒栗子这类吃食,她给我说:“念书苦,易犯困,吃点东西解解乏,实在熬不住就去睡,明天早一点起来再背。”
严妈常提醒我不要去清音
阁,那边不清净。其实,我已经去过清音阁,那是位于中南海东岸建于乾隆年间的一组建筑,琉璃瓦上都长了杂草、窗棂间布满了灰尘,显得“吴宫花草埋幽径”般的苍凉,没有发现什么不清净。到五月下旬,长城抗战告一段落。随后是较长的对日交涉,那几天时有日本军人进出中南海。
渐渐进入了夏天,海子边已是绿柳成荫,不知不觉中我在北平念书已经三个多月了。我每天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小侄女抱着到园子里去玩。让五嫂和严妈腾出手做饭。有时候我抱着侄女走得远了,严妈找到我们时就会抱怨地说:“叔,你可不能走得太远,我就是远远看见你们也不能叫,你知道不?园子里是不准高声喧哗的。”
一个星期天的清早我刚起床,五哥要我换身干净衣裳,随他们去颐和园。我跟着五哥来到居仁堂,已经有三辆轿车停在路上,还有几名卫士站在车旁。一会儿,何应钦等一行人从居仁堂的台阶上走下来,闲时我随五嫂在园子里散步远远的看见过何先生与其夫人王文湘。何先生朝我看了一眼,紧跟在何先生身后的五哥急忙叫我上前见过何先生。五哥告诉何先生,我是他兄弟在北平读高中,一直没有时间带我出去,今天想跟着出去玩。何先生说:“啊,在读高中,很好”。这是我第一次与何先生见面。五哥和何乘一辆车坐在副驾驶坐位上,我与其他人员上了后面的车。汽车由中南海西门驶出,经府佑街西行,出西直门再往西北方向行驶一段路,来到颐和园。进了颐和园,五哥告诉我可以自由活动,但不要走得太远,要远远地跟着他们,什么时间回去还不知道,别搞丢了。园子里还有其他的游客。我与五哥他们渐渐的拉开了些距离,正顺着昆明湖边的长廊走着,传来的京胡声将我吸引过去,原来湖边有一群人在唱京戏。我挤在人群后面踮着脚,伸长脖子往里看,那位唱花旦身边的男子不就曾经是我姐夫穆德生吗?再一看,正在唱着的女士是他再婚后的妻子朱木兰。他们婚后应该居住在贵阳,怎么也来北平了?朱木兰唱完,我挤进去与他们打招呼。他们看见我十分惊奇,我简单的讲一下我的情况。分别时他们给我留下了地址,要我抽空去他们的寓所好好聊聊。
从颐和园回来,我给五哥讲了遇到穆德生夫妇。五哥也诧异居然会在茫茫人海中遇见他们。他给我说,既然是老亲你也可以去看看。
那天晚上我转辗难眠,勾起许多回忆。记得我还在童年时,我六姐银娣与穆德生成了亲,他们夫妇十分恩爱。一次土匪来抢窃,他们到穆家乡下亲戚处躲避土匪,遇到晚上下暴雨,墙垮了,砸在六姐的床上,六姐再也没有醒过来。悲痛之余的父亲,见这个女婿哭得呼天唤地,痛不欲生,反倒过来安慰他,节衣缩食送他到贵阳念高中,让他改换环境,减轻一些痛苦。他高中毕业后,投考了黔军,从司书做起,此后节节高升,在黔军占领川南一带时做过四川古蔺县长,重庆铜元局局长,后来川军联合起来把黔军驱逐后又回省做过黄平县长。其间,他也带些钱回去,要我父亲代他置办些产业。后来在贵阳娶了朱木兰,婚后曾带着他们的儿子“哥儿”回老家看望过父亲。不知何时,他竟一声不吭地卖掉了老家的产业,从此杳无音讯。不想今天竟然在北平遇见他,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学校放了暑假,我去看望穆德生夫妇。我找到了棉花胡同2号穆的寓所。棉花胡同北起罗尔胡同,南至护国寺街,虽然是一条不长的胡同,可一个个四合院中住的都是有名气的人。靠胡同北边的一个院落曾经是蔡锷将军的故居,与穆的寓所比邻的是欧洲某国的领事馆,门口站着一个用布缠着头,留着翘胡子的卫兵。出棉花胡同往南是护国寺街,再往东不远是梅兰芳先生的住宅。穆德生住的也是一个四合院,要上三级台阶才进门,大门上的朱漆虽有些剥落,从门槛两边的石鼓和门头上曾经用来悬挂匾额已锈迹斑斑的铁钉可见过去这里住的也不是一般人家。院子的设计也独具匠心,它的大门不是面向胡同的,而是往东突进去形成一段小胡同再开门使房子成为南北走向。还在门外就听见京胡伴奏下“咿……啊……!”的声音飘过墙来。敲门进去后,原来是朱木兰请了一位琴师在调嗓。还有一位留着分头相貌英俊的中年男子在为她辅导动作。我叫了一声“朱大姐”,她看见我应了一声就朝屋里唤着,“哥儿,带你舅舅到你爸屋里去,我这里快完了。”接着,琴师拉出一段西皮二六的过门,朱木兰继续随着那中年男子后面模仿着动作吟唱“劝君王饮酒听虞歌,解君忧闷舞婆娑……自古常言不欺我,成败兴亡一刹那”,穆德生听见我来了,从屋里出来迎我进去。他对哥儿说,“快叫舅舅”,哥儿叫了我一声,却显得有些腼腆,渐渐的有些熟了,他告诉我他已经念初小了。几年没见这孩子,个头长高了,长得眉清目秀,他一直陪着在听我与他父亲谈话。穆德生对我说“没有办法,你朱大姐就是喜欢唱几句,连我都跟上了,北平的一些名流、票友也时常来玩玩”。他向我问起老家的人事,却很少谈及自己的情况。朱木兰送走了琴师和教戏的老师,也进来加入我们的谈话。午饭后我们一边喝茶一边继续谈话,他们家的佣人给我续了几次水,涨急了肚子,我叫哥儿带着上了回厕所。哥儿领我穿过正房进入后院围墙下的厕所,出来才发现后面围墙上一个圆形门里面还有一个院子,院门紧闭,只能看见高出墙头露出的房檐角。我往圆门那边走几步试图想看个究竟。突然,哥儿跑过来扯着我的衣角悄悄的说“您千万别过去,门里有个守门的可凶了,他不认识的人不开门的”,我止住脚步,倒不是因为哥儿的这句话,而是觉得好奇归好奇,总不能唐突地窥探别人的秘密。回到家,我向五哥五嫂谈起在穆寓的所见所闻,五哥问,“他们有这样大的宅子、家里开销应该比较大,有些年没有联系了,他们在这里干什么营生呢?”这个问题我倒是答不上来,只是不解他们夫妇现在怎么会对京剧饶有兴趣,乐此不疲。五嫂说。“这你就不懂了,在北平,一些公子哥、少奶奶喜欢做做票友,唱几句显示风雅”。收拾屋子的严妈接过话头“肚子里有了油珠珠才唱得起,你见大街上拉车的还能请个琴师风雅、风雅?”大家听后都笑了。
五嫂给我说,“你空着手还去道谢了人家一餐饭,下次去要记住给哥儿带点糖果”。暑假期间,我又去了几次棉花胡同,每次去都给哥儿带去点心、水果。记得有一次是下午去的,穆氏夫妇都在。他们住的是正房西屋,中间隔着堂屋,东屋是客房,里面有人在打牌。一会儿,有人在安排摆饭,我起身告辞。穆德生抖一抖手中象牙烟嘴上的烟灰,对我说,“吃了饭再走吧。”说话间。堂屋里准备的人通知,西屋的牌局已散可以开饭了。主人陪同客人入席,餐桌是一张八仙桌,胡陪着主客坐在上首,餐桌两端一边是苏大姐带着哥儿坐,另一边是两位男客,我与一位年
龄长我几岁的男子坐在下首。穆德生向我介绍主客,“这是余洒度先生,听说过吧!”,穆又向余先生说起了五哥的名字和工作的地方。余先生听了,“啊!”了一声,点了一下头,胡接着介绍了旁边的两位。余先生向我指了指坐在我身边的那位“这是我的老弟”。他的话带有较重的湖南口音。席间,大家的谈话内容说的都是“东来顺”、“西来顺”、“又一顺”这些北平有名餐馆字号的由来和菜的特色,或是长安剧场在演什么剧目,没有涉及其他的内容。饭后,余先生离席站起来主动邀我“到我屋里坐坐打打广”,不解什么是“打广”,穆德生笑了笑说,“这是余先生的家乡话,就是我们说的摆龙门阵”。余先生给那两位先生说,“你们就在这里坐一会吧”。他又回头对他的弟弟说,“你也赶紧去准备”。他弟弟穿过堂屋往后面去了,看来他们对穆家的环境十分的熟悉。穆氏夫妇陪我随余先生进了他住的东屋,落座后佣人重新沏上茶。这时,他弟弟和那两位进来与余告别,余起身只是说了句“抓紧赶车去吧”。他们走以后,我们重新坐下来。穆德生冷不丁地冒出一句“过去一直没有给你说,我和余先生在天津有个商号,如果你愿意可以来做事”,我一点准备都没有,就没有作答。突然,朱大姐沉下脸朝着穆德生瞪了一眼,说“你就别造孽了,让七弟安心读书”,她对我说,“好好的读书,别听你穆大哥胡扯”。这时,穆德生与余先生都没有再说话。我趁此瞥了一眼这间屋子,窗明几净,陈设简单,床边立式衣架上一枝挂钩上挂着一套军服,另一枝挂钩上悬着的皮带上套着一把手枪。余先生端起他的茶碗并没有喝,只是用茶碗盖刮了几下茶水,又放下了。朱大姐会心的对我笑了一笑,我顿时明白,想起闲时读小说,官场里的“端茶送客”,看来他们切实是风雅之士。已经是晚上了,我即起身告辞。出门正好有一辆洋车停在离穆家大门不远与胡同正街交汇的地方,我坐上了这辆车。本来从南长街中南海东门回家要近一些,过去回去晚就关门了,于是我要洋车绕了一点道,在府佑街下车。回到家,家里人都歇息了。
第二天晚上,五哥问起我昨天为什么回来得晚。我说穆家来了客,留我吃饭耽误了。我说起余洒度时,五哥愣了一下,接着问我,“是不是近四十来岁,带湖南口音”。我作了肯定的回答,然后详细的讲了昨天在穆家的情况。五哥听后,若有所思地说“他们怎么会搞在一起了呢?”他接着对我说,“我还在给你五嫂说,找个时间聚一下吃餐饭。看来穆德生的社交太复杂,你以后少去他那里。”五哥叫五嫂带着我侄女先睡,打发严妈也去歇息。这时候,五哥才给我谈起了下面的情况。
(待续)
(作者单位:贵阳市云岩区人事劳动局)
责任编辑:李守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