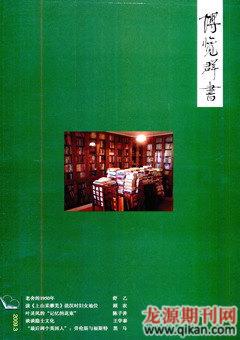夏承焘与朱生豪的师生情谊
朱洪斌
“一代词宗”夏承焘先生(1900—1986)的日记《天风阁学词日记》,起自1928年7月20日,迄于1965年8月31日,时间跨度近四十年,虽略有缺佚,但大体完整。在20世纪中国学人日记中,《天风阁学词日记》的特色及价值,早已赢得学林的肯定和重视。受晚清名流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的启发,夏承焘从16岁开始写日记,直至暮年停笔,现有《天风阁学词日记》并非夏氏日记全部,仅是历尽世劫之后的烬余。自30岁后,夏氏立志专攻词学,即注意记录师友之间的学术往还,凡对己有益的启迪,大小不捐,一一笔录,故这部日记真实地保留了学人之间议政论学的稀见资料。夏氏以词人作日记,文笔凝练雅丽,流光四射。类似的文字,今天颇难寻觅,可谓旧式文人日记之绝唱。译界奇才朱生豪(1912—1944),曾为夏氏弟子,日记中存有二人交往的一些动人片段,吉光片羽,弥足珍贵。将这些资料勾稽还原,那位远去的天才少年的影像,似乎又悄然活现于我们的眼前。
1930年初,夏承焘到杭州之江大学国文系执教,讲授“词选”、“唐宋诗选”、“文心雕龙”、“文学史”、“普通选文”等课。这一年夏承焘30岁,已在之江就读二年级的朱生豪18岁。朱生豪选读了夏承焘开设的部分课程,课外还参加了夏氏任社长的“之江诗社”,由此两人结下师生之谊。
朱生豪个性沉默,寡言少语。从夏氏日记看,他在之江念书期间,只去过夏承焘家一次,私下往来并不特别亲密。但夏氏在朱生豪历年的试卷中,敏锐地发现这位少年对传统诗词有着精妙的鉴赏力。1930年11月5日,“夕阅考卷,朱生豪不易才也。”12月8日,“阅卷,嘉兴朱生生豪读晋诗随笔,极可佩,惜其体弱。”1931年1月13日,“夜阅文科学生试卷,朱生豪止十八岁,真可钦佩。”6月8日,“阅朱生生豪唐诗人短论七则,多前人未发之论,爽利无比。聪明才力,在余师友之间,不当以学生视之。其人今年才二十岁,渊默如处子,轻易不肯发一言。闻英文甚深,之江办学数十年,恐无此未易才也。”6月16日,“阅卷甚忙。朱生豪读词杂记百则,仍极精到,为批十字曰:审言集判,欲羞死味道矣。”
在夏氏眼中,年方弱冠的朱生豪无疑是天资聪颖,诗才超卓,故他每以“不易才”加以赞赏,甚至说朱生豪的聪明才力,“在余师友之间,不当以学生视之”。有一次还克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写下一段评语:“审言集判,欲羞死味道矣”。唐代大诗人杜甫的祖父杜审言,在初唐与李峤、崔融、苏味道并称“文章四友”,杜审言自命不凡,但以官阶在苏味道之下,相当愤懑,便当众宣称:他的文笔足以令苏味道羞死。夏承焘巧借这一典故,亦庄亦谐,于戏谑中透露由衷的欣赏。
当时夏承焘正研究南宋大词人姜夔(号白石道人)的词,日记中摘录了朱生豪对姜夔词格的分析。1931年6月18日,“朱生豪谓‘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白石词格似之。此语甚当。”“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是姜夔《点绛唇·丁未冬过吴松作》一词中的名言。王国维《人间词话》论词境有隔、不隔之别,曾专门举出这两句,说明白石写景词的缺陷是一“隔”字。朱生豪用这两句概括姜夔词格,夏承焘以为极其精当。这是师生相互启发的一个例子。朱生豪英文出色和体质孱弱,也引起夏承焘特别关注。后来朱生豪英年早逝,既是因抗战时期生活艰困所致,也和他从年轻时就“体弱”有关。
1933年,朱生豪大学毕业,进入上海世界书局任英文编辑。1935年与世界书局签订合同,开始投入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艰苦工作。夏承焘一度曾为诗友邵祖平(1898-1969,字谭秋)售书稿事致信朱生豪。1935年3月24日,“发朱生豪信,言谭秋卖稿事”。1937年底,之江大学决定迁往上海租界继续办学,夏承焘暂时回温兰老家。居乡期间,接到任铭善(1912—1967,字心叔)的来信,1938年6月29日,“接心叔函,示和朱生豪词。云从亦有和朱词”。任铭善、蒋礼鸿(1916—1995,字云从)都是夏氏在之江的得意弟子,与朱生豪往来颇密。常有诗词唱和。
8月,夏承焘重回上海,再度执教之江,直到1942年之江停办。朱生豪供职的“中美日报”馆,也遭日军的封闭。沪上四年,师生间的交往日益密切。夏、朱二人不愿为汪伪政权服务,曾商量过一起回乡。1942年1月16日,“朱生豪来,约同行”。之江停办后,校方设法以补习班的名义,继续招收学生,维持教育事业。夏氏曾约失业在家的朱生豪来授课,2月7日,“早赴校开会……午后,心叔、蓀簃、朱生豪来,共排定功课”。不久,朱生豪与校友宋清如预备结婚,二人来请恩师夏承焘担任证婚人。4月27日,“蓀簃偕朱生豪来,谓生豪与宋清如亦五月一日结婚,请予证婚”。4月30日,“朱生豪来,五月一日与宋清如结婚,邀予为介绍人,以行期不可改,辞之。”因当日下午夏承焘便要动身回乡,无法参加次日朱生豪的婚礼,这次分手,等于诀别,师生从此天涯悬隔。夏氏后在日记中屡屡提及,颇有遗恨。
朱生豪、宋清如结婚后,夫妻俩先去常熟岳母家居住,1942年底又返回朱生豪的嘉兴老家,从此闭门不出,呕心沥血翻译莎翁全集。1944年12月26日,朱终因患肺结核病不治,含恨辞世,时年32岁,手译的37部莎翁全集还剩6部半的历史剧来不及翻译。别后夏承焘一直不知道朱生豪的音信,直到抗战胜利,才从任铭善、蒋礼鸿处辗转惊悉朱生豪去世的消息,这时距未去世将近一年。1945年12月7日,“得心叔杭州书……义云:得云从川中书,朱生豪去夏以伤寒去世一予往年离沪之日,彼来请予为其与宋清如结婚作证婚人。予以上道辞之。不谓遂为最后一面。”
1947年,朱生豪倾注心血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由世界书局出版。这年10月10日,宋清如来杭州浙江大学探望夏承焘,夏向宋殷殷询问朱生豪身后的遗著,并庆幸弟子存有后嗣,“骆允治偕宋清如来。予问朱生豪译著,云:所译莎氏乐府全集,已由世界书局出版。病中尚有蝇头细字《左传分类目录》(与《左传事汇》不同),又尝与清如合选一词选,尚藏于家。忆六七年前予离上海返里之日,二君来请予为证婚。予以匆匆上船,不及践约。不谓别来变故若是。幸小郎已五龄,甚聪颖,清如不致寂寞。”朱生豪短暂的一生,其精力尽萃于莎翁全集的翻译。此外,据夫人宋清如所说,遗著尚有《左传分类目录》和夫妻合编的《同选》一种。今这两种遗著都未见面世,不知是否尚存于天壤间。近年由范泉选编了朱生豪在《中美日报》上发表的新闻短论,辑为《朱生豪小言集》一册。朱生豪哲嗣朱尚刚(即夏氏日记中所谓的“小郎”)收集父亲致母亲的情书,编成《朱生豪情书》一书。以上两书,是朱生豪除莎翁译著之外可见的文字。
1948年10月7日,夏承焘借阅莎翁全集中的一册,对弟子平生志业做了深沉恳切的论定,深盼其弟能继承遗志,完成全部莎士比亚戏剧的翻译工作。“过定豹,借朱生豪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一册,阅《罗密欧与朱丽叶》一过。灯下读生豪自序及宋清如之《译者介绍》,记生豪尽萃此书,卒以身殉,语甚动人。此子亦完成其一生以去,无可憾矣。前六七年予偕眷离上海,生豪偕清如过予泰来里寓楼,请予次日为其证婚,予以行色匆匆辞之,即以写成一联与之。二君未坐,惘然即去,此为最后一面。生豪以肺病卒于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年三十二。译此书前后共十年,得各种莎集版本,及考证注释批评诸书一二百册,至死尚未泽完,遗命嘱其胞弟文振为之续成。文振亦之江学生,亦工中英文。当为书属其不负所托。生豪临死,谓若早知一病不起,悔不不顾性命,为一气呵成。此语可佩。亦可悲矣!”昔年临别时,夏氏送给朱、宋二人的对联是:“才子佳人,柴米夫妻”,希望他们琴瑟相和,相携到老。岂料天妒奇才,这场美满婚姻仅仅延续了两年。
1951年6月14日,任铭善与夏承焘聊起朱生豪,“心叔过谈朱生豪译莎氏乐府,谓近人治此业者,允以生豪为第一。梁实秋、曹未风皆不能及,惜此子不永年。”朱生豪的译笔,在当时已获学界之公认。这无论对于逝者(朱生豪),还是生者(夏承焘),大概都是最大的宽慰。朱生豪走得那样匆匆,但他的天才和勤奋,却给国人留下了永久的文化遗产。夏、朱两人的故事,也许并没有多少传奇的色彩,但细细品味之下,苦涩中还夹杂着些许暖意,犹如在冷雨凄风中,枝头上两朵争艳的梅花,相映成辉,余香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