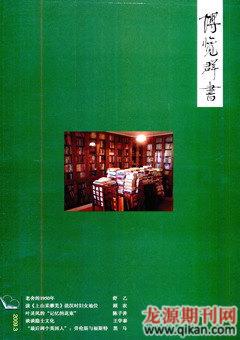沉重的翅膀
潘 殉
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是一位政治思想上错误多端、艺术成就却很高的复杂人物。他的一生,是将文学和感性化政治调和在一起而精心绘制的一幅撼动人心的油画。在这幅充满了诡异的油画中,“美”——凌驾于他的文学与政治人生之上。在很多人看来,1970年三岛由纪夫的切腹自杀,应归咎于他“企图发动政变”的失败。但笔者认为:三岛由纪夫是一位对世界文学有着独特贡献的杰出作家、是一位对独特美学执着追求与大胆实践的作家;三岛由纪夫的美学精髓渗透在他文学作品的字里行间,并影响着他一生的创作;他的切腹自杀是他文学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他是死在自己一生所营造的美学悖论中。
一
三岛由纪夫原名平冈公威,1925年1月14日生于东京的祖父母家。祖母永川夏子对三岛由纪夫寄予了极大的希望,出生后的第49天,就夺走了抚养的绝对权力。永川夏子出身贵族武士世家,从小生活在与明治天皇血缘很近的亲王有栖川宫身边。自小形成的高傲、严谨的性格,使得永川夏子对三岛由纪夫的抚养格外精心和严厉。由于和祖母生活在一起,三岛由纪夫的童年便与母亲、自然界和同龄的男伙伴儿隔离(永川夏子身患坐骨神经痛,对声音极为敏感,禁止三岛由纪夫和男孩儿玩耍,以免发出响声,引发病痛)。因此,三岛由纪夫便在绘画与童话故事中寻找现实中无法找到的世界。屋内的童话世界和屋外的现实世界交织的幻影,执拗地追赶着年幼时代的公威,而追赶他最多的就是一种“异样性的东西”,是血与死。超常而奇怪的生活方式,使得鲜血与死亡成了三岛由纪夫童年热切的愿望,并发展成为一种“特殊的嗜欲与浪漫的憧憬”。这种嗜欲与憧憬,渐渐地形成了他的文学沃土,酝酿和给予了三岛由纪夫独特的文学养料,也造就着三岛由纪夫的文学人生。
少年时代的三岛由纪夫,身体十分赢弱,怯于介入同龄男孩子中。敏感的个性,使他从小遭受着自卑的困扰,也影响着他成年以后的性格:极其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
母亲倭文夺回抚养权后,对三岛由纪夫百般关爱,尤其是在文学兴趣上的培养,给予了他很多的鼓励与帮助。母亲的潜心培育,极大地激发了三岛由纪夫对文学的热爱和对创作的渴望。15岁时,三岛由纪夫拜著名诗人川路柳红为师,学习写诗;16岁时,他发表处女作《鲜花盛时的森林》。可以说,处女作的发表,让三岛由纪夫在创作中第一次真正实现了自我认同,找回了自信。此后,三岛由纪夫在创作中按照自己的美学价值观,不断地将这种“美”蔓延在日后的作品中。随着时光的推移和作品的相继发表,他的自卑不知不觉中衍生成了自恋。
在三岛由纪夫的一生中,油画《塞巴斯蒂安殉道图》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画作中塞巴斯蒂安强悍的身躯和俊美的脸庞,让三岛由纪夫为之倾慕。在《假面自白》一文中,三岛由纪夫承认这是令他第一次有性冲动的画作。在此之后的文学作品中,三岛由纪夫常常描写同性恋情节。后来有很多人认为三岛由纪夫是同性恋者。笔者认为,三岛由纪夫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同性恋,他最初的同性恋倾向,源自从小与同性接触较少而引发的好奇,而后随着他对唯美主义与古典美学的欣赏,这种同性的美便成为他美学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和唯美主义与古典美学的接触,源自三岛由纪夫中学时期的师长清水文雄对他的影响。
高中时,三岛由纪夫在清水文雄的影响下开始涉猎东西方古典文学。首先占据三岛由纪夫审美意识的是日本传统中的放荡之美,即以井原西鹤为代表的“好色”的审美。三岛由纪夫在其中融合了弗洛伊德的性倒错说,从而构建了自己唯美、浪漫的古典审美标准。三岛由纪夫在其文学作品中常描写的性爱,并不以展现欲望为目的,而是致力于挖掘在奇异的情欲下所呈现的真实的人性和身而为人的本能。他关注的是人,不是色。《假面自白》、《爱的饥渴》都是将战后人们的心理压抑转为一种颓废、诡异的状态,从而发现其中潜藏的真实的美。
其次,三岛由纪夫从唯美与古典美学中,提炼出的是在矛盾中展现“临界值”峰顶的真实与美丽。《假面自白》中,主人公对近江的心态就极为矛盾:他一方面憧憬近江生命中具有的惊人力量并产生了同性的爱,同时又对近江产生了强烈的嫉妒;《金阁寺》中,“人容易毁灭的形象,反而浮现出永生的幻想;而金阁坚固的美却反而露出了毁灭的可能性。像人那样,有能力致死的东西是不会根绝的;而像金阁那样,不灭的东西却是可能消灭的。”在矛盾与逆反中,三岛由纪夫企图在死中意识生、在丑中发掘美、在伪善中寻找诚实、在暴烈中展现优雅、在违道德中弘扬道德。这种落差意识的交错,即是矛盾的“临界值”。三岛由纪夫从中为人们展现了肉体快乐与精神痛苦的对立,以及被压抑的性欲与病态的焦虑之间的矛盾。在《我经历否认时代》中,三岛由纪夫说:“眼看肉体与理性的均衡将被打破的时候,就会在难以打破的紧张中产生美。”
与此同时,三岛由纪夫还倾迷于王尔德那种否定宗教、道德和唯美的艺术至上精神,崇尚用世界文学视角来审视日本的古典文学。三岛由纪夫喜欢日本近代作家古琦润一郎的肉体恶魔主义,泉镜花的病态性的幻想,伊东静雄的浪漫的空幻,北原白秋的妖艳语言以及立原道造的爱与死的诗的戏剧性等等,从而确立了一种信念,那就是“日本古典具有一种力量,执拗地盘踞在日本的现代人的心中”(《师生》)。(《20世纪日本文学史》,叶渭渠唐月梅著,青岛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第346页)
可见东西方古典主义的碰撞,支撑起了三岛由纪夫独特的美学思想。
在西方古典思想中,对三岛由纪夫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希腊古典主义。三岛由纪夫接受古希腊追求英雄主义和男性裸体造型的宏大气魄,以及在艺术上表现出来的严谨的完美性与理性。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他的《潮骚》,完全模仿古希腊朗戈斯的古典主义,从他那里汲取主题、情节、类似的矛盾冲突和人物性格,并且注入了新的文化内容。其实,在崇拜古希腊男性肉体的过程中,我们还是能看到三岛由纪夫对日本武士道的倾慕,也就是说,他是以日本传统为根基,同时用希腊的古典主义来不断丰富其美学体系的。
二
作品的不断问世,让三岛由纪夫在创作中享受着快慰。写作无疑成了他证明自己的最好方式,甚至是他人生的救赎。写作虽然痛苦,却被三岛由纪夫视为存活下去的唯一方式。如果不写,他认为就无法得到认同,就很有可能再次回到原来少年时代那个渺小、孤独的自己。这种潜意识里的自我保护,来自于他从小就根植于心的自卑。在疯狂的写作中,三岛由纪夫陷入了自己的美学窠臼,使作品中的世界逐渐与现实世界相混淆,由此埋下了最后看似因政治而自杀的悲剧。
三岛由纪夫在《文化防卫论》一文中,反对美军战后制定的象征性天皇
制,同时也反对“复活政治概念的天皇制”。他说:“政治概念的天皇,大概不得不牺牲更加自由更加概括的文化概念的天皇。”可以说,三岛由纪夫思考的天皇,不是政治权力的象征,而是作为悠久的传统文化的象征,而且他说“将天皇包括在全体主义的政治概念里,正是日本和日本文化的真正危机”。所以三岛由纪夫要恢复“文化概念的天皇”是恢复自神代(神武天皇即位前,由神支配的时代)以来的传统天皇观,以天皇作为精神权威实体和天皇的神格实体,以维系日本国家与民族的统一和日本历史与文化的传统。他对文化天皇的顶礼膜拜,让人倍感这文化的天皇,其实就是他自己所推崇的独特美学。这一点,从他后期的文学作品中就可以看出。
60年代,三岛由纪夫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化概念和新的天皇观,并以此作为创作的中心,辐射出《忧国》(1961)、《十日菊》(1961)、《英灵之声》(1966)三部曲,以及《太阳与铁》(1965—1968)、《文化防卫论》(1969)等评论文章,这些作品将其破坏性的冲动与暴力美学的情趣结合,运用了冷嘲热讽、逆历史潮流的言辞来构建新的文学模式。从《忧国》不难看出,此时的三岛由纪夫已将他的美学寓于其政治思想中,这种政治思想是感性而主观的。同时,他又将这种“三岛由纪夫式”的政治寓于文学创作之中。《忧国》讲述的是年轻中尉竹山被派遣偷袭组织“2·26事件”的叛军,而叛军的主要头目又是自己的好友,面对两难的选择,竹山最终选择了剖腹自杀。血腥的描述,透露出三岛由纪夫的美学观。小说字里行间流露的是三岛由纪夫对法西斯军事政变“2·26事件”的肯定,他认为这些年轻军官是在反对政党政治腐败、经济失败、外交软弱。所以说,他赞美的不是“2·26事件”本身,而是参与政变的青年军官的“灵魂的奔腾”、“正义感的爆发”。此时的死亡在其笔下已表现出尼采式“对生命力的无穷无尽、无比欢乐的喜悦”。三岛由纪夫的精神价值通过死被承认,作为偶像被顶礼膜拜。“作者试图在抒写死亡带来灵魂净化和精神世界的积极意蕴,而没有把笔墨集中在生命消逝的叹息惋惜,意欲表现一种愚君的政治气节。”(李德纯《抱残守缺的“武士道”说教——三岛由纪夫论之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3年第5期)
其实,看《忧国》让人感到的是三岛由纪夫似乎在用这篇小说为他几年后的自杀进行排演。到了1965年的夏天,三岛由纪夫开始着手他文学生涯中最主要的创作——6年时间写一部四卷长篇小说。这部超长篇小说就是《丰饶之海》(包括四卷《春雪》、《奔马》、《晓寺》、《天人五衰》),时间跨越了60年。《丰饶之海》的主人公本多繁邦贯穿于四个故事的始终,他的朋友松枝清显却以命运轮回的方式,同样存在于每一卷里,可以说本多繁邦见证了松枝清显的四次生死。小说运用东方佛教轮回的永恒观,将整体构成一个大网环。《丰饶之海》把死亡的趋势分为已生、死和再生三个自我否定阶段,方死方生,已死已生,生命在逃去,生命在延续,给人印象是主题的恢宏和深远,讲述了一个生命冲破时空不断再生以至永恒的故事。可以说《丰饶之海》让三岛由纪夫掏空了他灵魂中的全部。1970年,他寄给一位英国朋友的信中说“写完了这部超长篇的小说(《丰饶之海》),让我感觉像是走到了世界的终点”。终结篇《天人五衰》可能就是三岛由纪夫末年的绝望思想,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便是“以大灾祸为终结”。大灾祸又是什么呢?就像他在结尾将主人公置于人生的最后一程,却用离奇的情节对主人公和他自己提出这样的疑问:是否漫长的一生终究是毫无意义呢?以缅怀历史和瞩目未来的全部悲剧性和虚幻性,唤醒执著于现在时的时间意识,并对在死的困扰中,追求死的精神价值,渲染为“忠君爱国”的永恒观,这才是贯穿这部小说全书的主旨所在。
三
1970年11月25日,三岛由纪夫在完成《丰饶之海》的《天人五衰》之后,与盾会组织的四名青年,以观赏宝刀“关之孙六”为名,挟持了自卫队东部的益田将军,并提出在自卫队发表演讲。三岛由纪夫的演讲只进行了10分钟左右,便切腹自杀了。
笔者始终将三岛由纪夫的死,看作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为追求自己信仰的美学而死。其实,人的本性中都有想实现自己实现不了的愿望,这就好比许多唱歌跑调的人想当歌唱家一样。虽然这是人生的一种悲哀,但却不失为人生向前的动力。身为一名作家,他可以拥有双重的人生,正像作家余华所说:
写作与生活,对于一位作家来说,应该是双重的。生活是规范的,是受到限制的;而写作则是随心所欲,是没有任何限制的。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将他的全部欲望在现实中表达出来,法律和生活的常识不允许这样,因此人的无数欲望都像流星划过夜空一样,在内心里转瞬即逝。然而写作伸张了人的欲望,在现实中无法表达的欲望可以在作品中得到实现,当三岛由纪夫“我想杀人,想得发疯,想看到鲜血”时,他的作品中就充满了死亡和鲜血。
可是,三岛由纪夫却将文学写作与现实人生重叠到了一起,甚至混淆得连自己都无法分清现实与写作的界限,他的自杀就是最好的佐证。
从另一层面说,三岛由纪夫又始终生活在悖论之中:在众人面前,他常用开朗自信的面具,虚张声势的追求异国格调。但在大多的时日里,他又埋头疯狂工作,偶尔袒露(无法掩饰)病疾似的疲惫和紧张。他的生活在其精心安排下,无论是事业还是家庭看似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成功。尽管这样,还是有一个本质性的矛盾让他无法解决,而且是使用任何面具都无效——肉体变成美的任务,接着就是美的宿敌,而灵魂只在冷眼旁观。他毕生追求的美学目标,令他感到无论如何都无法实现。
矛盾越尖锐,带给他的力量也就越强大,少年的自卑厚厚地郁积在他心中。于是,他用一生的努力、追求绝对的畅销、绝对的功名、绝对的身体的美,以此来覆盖那深厚、却阴暗矮小的人格内核。从这个角度看,三岛由纪夫不仅写出了叹为观止的文学,也以艺术化的方式塑造了他的生生死死,这俨然是一种用生命做材料的行为艺术。当他塑造肉身和名誉的时候,也许固然有着虚荣心,足以让别人将他归入俗人之类,但最终的血泊和残尸证明那凡俗软肋下实则有着修罗般不可仿效的勇猛,这让他足以成为传世之说。他如心所愿,建成一座完美的神庙,再毁之,以壮年自戕之尸收下世间所有过于轻易的贬抑、过于草率的质疑。他抛弃的文字,便成了灵魂。书本犹如无法销毁的存在感,鲜活丰满又如肉身。他的话和他的死加上死后流传的文字,构成另一番蛇咬蛇一般的悖论。(《美与暴烈:三岛由纪夫的生与死》,亨利·斯各特·斯托克斯,于是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7月第一版,译后记《凄厉,便由他去演》,第353页)
纵观三岛由纪夫的一生,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想张开带着理想和热望的翅膀,像一只文学王国里振臂高飞的山鹰,按照独特的运行轨迹执着地奋力向上。但是,由于他内心充满了矛盾,深受煎熬和躁动的心灵总让他倍感沉重。所以,他时常表现出不满、忧郁、痛苦、反叛、激进。如果把三岛由纪夫的惨烈自杀比作一幅灿烂而又具华丽之美的马赛克拼图,那每一块马赛克上既有他辉煌的创造,又有他惊人的毁灭。三岛由纪夫是为文学而死,他的自杀,是他文学创作的延续,也是他对自己生命意义的注解。他死在自己的笔下,活在了读者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