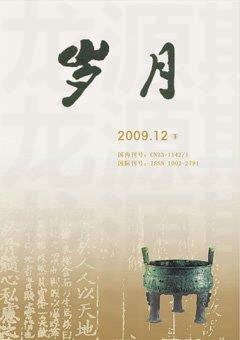从净化理论来看位格宗教体验
仲 凯
《圣经》是西方文化的主要构建力量之一。西方的两大思想文化根源中,希伯来的思想是动态的,希腊的思想静态的。多布舒茨认为希伯来思想是时间性的,希腊思想是空间性的。不讨论多布舒茨的看法是否正确,这种认识能说明一点,即希腊与希伯来的有根本的区别,甚至可以说在默写方面,希伯来的精神气质的反希腊的。不同民族的气质精神是由其思想为基础构建的,因此,可以说由希腊和希伯来建构的现代西方的精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互反的。
尼采《悲剧的诞生》里通过日神阿波罗和酒神狄俄尼索斯来解释幻想的美和严肃的哀伤。尼采用日神的名字来统称美学外观的无数幻觉,即是说内心类似梦境的幻想是通过外在美的艺术展现。可以说这方面主要是形式上的,而在关乎内心自我的本质上则由酒神通过狂迷的醉态而达到。通过酒醉的状态达到了忘却自然和自我的隔阂、自我和他者的隔阂,最终达到物与我的统一,我与他的统一。
《悲剧的诞生》里“采纳的是悲剧英雄的概念” [1],尼采借助酒神精神,试图解释人与世界如何沟通。他认为悲剧不是一种能够一起共鸣的情感净化,而是原本的接受生活。这种情况下,人们似乎达到了一种乐观的态度,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乐观而是“对严酷生活现实性的大胆接受” [1],于是在加缪那里,他让默尔索在行刑前一天对着神甫几近歇斯底里地发泄以达到和世界融合沟通的效果,最终达到心灵的安宁:“好像刚才这场怒火清除了我心里的痛苦,掏空了我的七情六欲一样,现在我面对着这个充满了星光与默示的夜,第一次向这个冷漠的世界敞开了我的心扉。我体验到这个世界如此像我,如此友爱融洽,觉得自己过去曾经是幸福的,现在仍然是幸福的。为了善始善终,功德圆满,为了不感到自己属于另类,我期望处决我的那天,有很多人前来看热闹,他们都向我发出仇恨的叫喊声。”[2]
世界、个人和人类的关系似乎在现代社会才变得紧张和敌对。但是在《圣经》中,似乎可以看到,远在以色列民族形成之初就已经出现了这样的矛盾:“选民”与“外邦人”之间的矛盾。其实,也就是属于神圣领域和世俗间的矛盾,或者用希腊化的表达为理性和感性的矛盾(这里先淡化了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的互反性,忽略了希伯来精神的非构建性和其对周围环境和谐体验的忽视,而注重道德行为的合法性)。“选民”成为一个特殊的类别,是被上帝挑选出来要成为圣洁的一群。这些是少数得到了上帝青睐的,有别与其他未被拣选出来的人群。且不论上帝在这些被拣选的人身上的计划(比如让他们成为圣洁的榜样),就其选民自身而言,他们尚没有脱离人的本性,成为神人,因而在他们身上保有“选民”身份的同时也承受了人作为普遍意义上的类而存在。可以说,在这些“选民”身上,戏剧性的因素更为强大,更容易产生一种荒谬感。一方面是特殊身份带来的骄傲,一方面却是作为普通人类的一份子而不断陷入道德思想上的困境。圣徒保罗便真实的记录了这样的挣扎“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 …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3] 分析看来,这段话可以归结为三种对抗:一是个体内心中自我精神与意志的对抗;一是个体和群体中他者的对抗;一是个体和社会生活的对抗。实际上,个体和他者和社会生活的对抗很多情况下是因为自我的矛盾和混乱。舍勒认为自我意识是具有对象性的,而位格作为人的根本属性而非对象性的存在着。他认为人的意识来源于人格的行为过程中,反思只是达到认识是一种途径,而人格应该是诸意识的统一。他将这种整体性的、自足性的人格生活于其中的所有行为总体领域称为精神。或者可看出一个人体将其看做自我的时候,也是用对象性的观察方式和角度,因而很多时候会造成自我的缺失和否定,并不是以作为一个完整的位格而存在。在基督教看来,这种问题是存在的。上帝在伊甸园造亚当和夏娃时候他们还没有犯罪,虽然具有犯罪的倾向(理论上只有上帝是不会犯罪和没有犯罪的可能性的),但是同时也具有拒绝犯罪能力,而拥有拒绝犯罪的能力的人便拥有完美的人性。但是随着始祖的堕落,人类也走上了不归路。由此,人类因为遗传而具有的人性是不完美和不完整的。
作为宗教,不能只告诉人类的处境,而是在其之后指出一条解救之路。宗教的神秘主义的审美体验成了解救人自我对抗的主要途径。即宗教的神圣体验,而这种体验是不能至少是很难被证明的,是一种不能被量化不能被有效归纳总结的体验,这种体验也不同于一般的经验事实,但就整本《圣经》来看,似乎能找到某种共性。
自亚伯拉罕始,人和上帝关系的建立,是以契约的形式展现。也可以说,这种意向不是单方面的来自上帝的意愿强加于人身之上的,而是平等和民主的(早期希伯来文化在契约的认识上似乎和希腊文化相契合,而希伯来的契约更可看成是现代契约的一个最终保证。因为人和人的契约是建立在人和上帝的契约之上的)。《圣经》可以被看成由两部分组成,分别被称为旧约、新约。也即为旧的契约和新的契约,可见契约性在基督教中的地位和作用都是显著的。
但是这样的契约何以制定,人为何会接受这样的契约?对于上帝的本质来说,人类要认识其属性是不可能的。舍勒说:“这一原理就是:即使神性之物的本质中有某种东西实在地存在,对有限位格来说,这种东西的实在性也只能以一种方式获得(某种)被给予性,即:它自发地给出自身而为这些有限位格(或其中的某一位格)所认识,或者在接受或回应行为中为它们所把握。”[4] 这里所谓的有限位格即为人之本质。舍勒用以说明人类的本质去认识神性本质是不可能的,唯一可能的途径就是神性之物的自我展现,或是说,这一神圣的事物通过启示向人传达自我,唯有如此才可能认识和得到经验。因而可以说,人类和上帝的契约也是通过上帝的亲自启示而来,可以说是一种上帝对人的自我显现过程。而这种由上而下的启示,便是宗教神秘审美经验的体现。
恐惧感在亚里士多德的《诗论》里是一个主要的概念,悲剧的净化作用首先以一种震慑心灵的恐惧感而引发。其对恐惧的定义为:“恐惧是某种痛苦或不安,它产生于对即将降临的,将会导致毁灭或痛苦的灾祸的意想。”[5] 当上帝向人显现的过程中,人也是伴随着巨大的恐惧感。当耶和华在西乃山上向摩西和众以色列人显现的时候,“到了第三天造成,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角声甚大;营中的百姓尽都发颤。”[3] 保罗在追捕基督徒的路上,忽见意象,吓得立刻伏地,之后眼不能识物(可参看《使徒行传》9章)。渔夫约翰在拔摩岛上见到大量意象,写成《启示录》。当其看到意象时“,就仆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 …”[3]人类在面对上帝的神启时的恐惧更多是来自对完美全善和正义的惧怕,因为人类的堕落而在善面前的羞耻感。可以说这样的一种境况,在作为一个道德意义上的人都或有经历,因此可以说哲学上认为人天生具有向善性,在内心都渴望达到一个更高的道德领域。这里看到的首先是一个在哲学领域的道德前设。用舍勒的观点来看,即在道德价值领域存在着等级,而这一价值等级中,存在着一种先天的结构——纵横性。纵横性指的是两个方向,一个是纵向的不同等级间的互通,一个是横向的同等级间的互通。其中纵向的关系的单独向上的,不可逆的。这个先天结构的前设就是来自宗教认为的人天生的向善性。
舍勒通过大量的事例揭示出,羞感作为一种保护个体自我的必要性感觉,是个体在回顾自身时,面对较低级的本能追求与较高级的普遍性冲突中进行价值选择时表现出的两种意识等级的对立,这种感觉分化出两种不同的形式:身体羞感与精神羞感。身体羞感作为生命之爱是指向愉悦之物的感官感觉的本能冲动,是人在面对生命感官的本能感觉中产生的,因而性爱是这种生命之爱或身体羞感的集中体现;精神羞感则表现为精神和灵魂之爱的价值选择功能与生命本能之间的冲突,它是人面对精神人格、思想或神性存在时产生的,其目的是为了提高生命力。两种形式的羞感在本质上都是个体在面对普遍性时对个体自我的呵护。具体说来,羞感具有两种功能:一是抵制较低价值的侵犯或诱惑,使人免于沉沦其间;二是呵护更高的自我价值,使之免遭侵袭或亵渎。
在舍勒看来,羞感的实质是自我感觉的一种形式,是一种“转回自我”的感觉。如果一种指向外部的强烈兴趣排除了对自己的自我意识和感觉,那还不一定产生羞感,而当注意力转回自我时,羞感才会随之产生。通过人自发的向善而产生的羞耻感,可以说达到了亚氏在《诗论》中悲剧所带来的净化作用。而这一净化的作用是远远超于一般意义上的感动,是带有颠覆性的彻底改变。通过恐惧所带来的羞耻感成为人摆脱罪感的内在动力,回归到神圣而强大的力量的庇佑之下而感到的心灵的安宁,从而也摆脱了肉体(欲望)和灵魂(理性)的对立,达到统一和和谐。
【参考文献】
[1] 罗素.西方的智慧[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
[2]加缪.局外人[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
[3]圣经和合本
[4]舍勒.舍勒选集下·绝对域与上帝理念的实在设定[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9.
[5]朱立元,袁晓琳.亚里士多德悲剧净化说的现代解读[J].天津社会科学,2008,(2).
(作者简介:仲凯,西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西方哲学研究生,主要从事德国近现代哲学与舍勒现象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