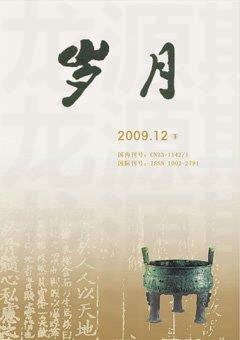论俄罗斯文学对中国的影响
泰京华
作为中国的邻国,俄罗斯文化曾深深地影响过中国的一代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给我们送来了丰厚的俄罗斯思想与文化。我们的耳边还回荡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红莓花儿开》动人的旋律;“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他临死的时侯就能够说:‘我已把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这段话深深地烙在我们脑海里。
较之于中国与其他邻国如印度、日本等之间的文化交往,中俄间的文化交往姗姗来迟,其主要原因是两个国家的文化类型差异较大,其文化关注的朝向也长期迥然不同。两国最早的文化交流应该是在1759年,我国的元剧《赵氏孤儿》被译成俄文。若干年后,收录若干中国寓言的《中国思想》一书在彼得堡出版,这是俄国出版的第一部中国文学作品的单行本。而中国对俄国文学作品的翻译起步较晚。据戈宝权先生考证,最早进入我国的俄国文学作品是发表在上海广学会校刊《俄国政俗通考》中的3篇克雷洛夫寓言,时间约在1900年。而上海学者陈建华先生通过考证,最早的汉译俄国文学作品应该是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翻译的《俄人寓言》,该译文于1872年8月载于《中西闻见录》创刊号。到现在为止,俄罗斯文学进入中国的历史已经有了130余年的历史。
鲁迅曾在《祝中俄文学之交》一文中称“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但俄罗斯文学真正成为中国人和中国文学的“导师和朋友”,恐怕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在中苏蜜月时期的20世纪50年代。在“走俄国人的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社会大背景下,“老大哥”苏联的一切都成了我们的模仿对象。苏联文学对中国文学产生巨大的辐射力至少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文坛和中国读者高度关注苏联文学
中国文坛和中国读者对苏联文学表现出巨大的热情,新译出的苏联文学作品如潮水般涌入中国。短短十年译出了上千位苏联作家的几千部作品,其总量大大超过了前半个世纪数的总合。1959年,有人作过一个统计:人民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和少儿出版社等当时几家主要的出版机构在近十年时间译介、出版了三四百种俄苏文学作品,各家印数均在一二千册。从1949年10月至1958年12月,中国共译出俄苏文学作品达3526种,印数达8200万册以上,它们分别约占同时期全部外国文学作品译介种数的三分之二和印数的四分之三。
这个时期苏联文学的翻译的热情是空前的。涉及的确作品数量极大,译者人数之多和传播范围之广也是空前的。再加上当时正处于中苏政治关系的“蜜月期”,把苏联的一切都看得十分崇高和神圣,全盘接受,盲目照搬的现象比比皆是。当时由于大量出版苏联文学作品,以致译稿紧缺,连人民文学出版社都要派专人到译者家坐等稿源。由于政治因素,译者十分关注的是在苏联获奖的作品,因此历年获斯大林文学奖的苏联作品大部分被翻译出来了,但其中很多并非佳作。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海鸥》等以新时代作为主要描写对象,以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为主旋律的文学作品,在中国读者中间引起了强烈反响,他们从这些作品中受到了教育。此时,青年们对苏联文学的爱好达到了狂热的地步。
二、“全盘苏化”在文艺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这一阶段,苏联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政策几乎未遇到任何阻碍,直入中国,“全盘苏化”在文艺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当时主管文艺的中央领导人明确表态:中国要坚定不移和不能动摇地在文学艺术上学习苏联。在建国初期,首先学习的是日丹诺夫主义,也就是用政治宣判的方式来评判文学,用政治斗争的方式来干涉文学。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苏联文坛盛行日丹诺夫的文艺思潮。日丹诺夫是苏联文艺领导人,在他的文章中,他将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等作家称为“市侩”、“荡妇”、“为艺术而艺术的谬论的典型”。同时,他还将象征主义等艺术流派划入“反动的文学流派”,把西方的文艺理论和现代派文学艺术统称之为“资产阶级的没落颓废货色”。与此相应,有的杂志被下令停刊或组改,有的影片被下令停止放映,有的作家被开除出作协,还有更多的作家受到残酷的迫害。五十年代初,中国文坛对文艺作品的批判(如1951年批判《武训传》)显然受其影响。总之,在日丹诺夫主义的影响下,五十年代的中国文坛,文学为政治、为政党服务成为主潮,这也导致了赞歌式的文学越来越多,批判性的文学几乎绝迹。
苏联文学在文学体制上也为中国提供了借鉴,如建立具有官方色彩的作家协会,将文学纳入国家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管理和监督,为作家的创作制定一个总的创作方法,让作家在社会上既享有崇高的地位、同时又受到严格的监督等等。可以说,中国文学界的组织管理模式基本上是苏式的。
三、苏联文学影响了中国青年的个性塑造和精神成长
在整整一代中国人世界观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50年代的中国青年很少有人没有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青年近卫军》等“苏维埃经典”。视文学为“生活教科书”、视作家为“灵魂工程师”的苏联文学,与当时弘扬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国社会大背景相呼应,极大地影响到了中国青年的个性塑造和精神成长,那一代人身上后来所谓的“苏联情结”,在很大程度上就来自于俄苏文学的长期熏陶。
在学习苏联中,保尔·柯察金这个角色,印在了每个中国年轻人的心中。他坚强、勇敢,而且充满革命斗志。在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来往密切的日子里,北京的中学,不仅有“金日成班”,也出现了“保尔班”。保尔的画像,被悬挂在教室内。这些班的学生,大多品学兼优,他们聚在一起,学习保尔。大家一起朗诵《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最广为传诵的那一段: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他临死的时侯就能够说:‘我已把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这段话,大概也是当年出现在“格言摘抄本”上频率最高的一段话,也是学生作文中最喜欢引用的“名言”之一,它还走进了初中语文课本。这些留在陈年日记本扉页上的已经化开了的蓝色钢笔墨迹,成为那个时代最鲜活的表情。
中苏关系破裂后,“保尔班”逐渐消失。但保尔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依然是青年人最主要的精神力量源泉。
四、在创作上对中国作家的直接影响
当时的中苏作家往来频繁,相互之间非常熟悉,在苏联发表的每一部稍有名气的文学新作,几乎都会被迅速地翻译成中文,这使得两国的作家和读者似乎过着同步的文学生活。加之,苏联文学所再现的现实又是中国人心目中的理想国,苏联作家的创作方法又被视为毋庸置疑的典范,因而,中国作家在自觉和不自觉之间所受到的苏联同时代作家的影响的程度,也就不难揣摩了。
作家王蒙在《苏联文学的光明梦》这样叙述着苏俄文学对他的影响:“我们这一代中国作家中的许多人,特别是我自己,从不讳言苏联文学的影响。是爱伦堡的《谈谈作家的工作》在五十年代初期诱引我走上写作之途。是安东诺夫的《第一个职务》与纳吉宾的《冬天的橡树》照耀着我的短篇小说创作。是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帮助我去挖掘新生活带来的新的精神世界之美。在张洁、蒋子龙、李国文、从维熙、茹志娟、张贤亮、杜鹏程、王汶石直到铁凝和张承志的作品中,都不难看到苏联文学的影响……,这里,与其说是作者一定受到了某部作品的直接启发,不如说是整个苏联文学的思路与情调、氛围的强大影响力在我们身上屡屡开花结果”。在文中,王蒙不仅坦陈了他自己深受苏联文学的影响,而且还指出了他同时代的一大批作家都受到苏联文学的感染与孕育。
在具体的创作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们之间的对应关系。例如,张贤亮的《肖尔布拉克》和艾特玛托夫的《我的包红巾的小白杨》,古华的《爬满表藤的木屋》和艾特玛托夫的《查蜜莉雅》,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和利帕托夫的《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乔良的《远天的风》和艾特玛托夫的《一日长于百年》,徐怀中的《西线轶事》和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苏俄文学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题材选择、主题开拓乃至具体的艺术技巧与形式探索等方面,都或隐或显地昭示这种影响的存在。也可以说中国作者的创作意识中有种挥洒不去的“俄罗斯情结”。
【参考文献】
[1]陈建华.20世纪中俄文学关系[M].天津:学林出版社,1998.
[2] 刘文飞.俄罗斯文学:姗姗来迟的“完全别样的风景”[N].中华读书报,2006年5月18日.
(作者简介:秦京华,合肥工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