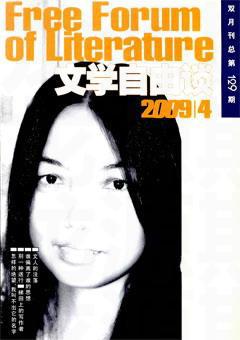《孤独骑士之歌》的诗意担当
郑小琼
中国诗坛正面临着一个可怕的现象,小镇的优秀诗人忙着放弃自己独特和独有的方向、价值取向、语言,去模仿大城市的诗人去同大城市的诗人们接轨,而中国的“大”诗人们不断地放弃中国独有的民族传统与社会现实去同西方的强权接轨,在这场诗人自诩为走向世界的诗歌面子工程中,一个个理应具有独特品性的中国诗人逐步变成了一个个可怕的诗歌怪物。纯粹的诗歌理想正在逐渐丧失,诗人们对物质与功利的追逐像毒菌一样深入到中国诗人们的思维中。我对这场人为的机械性的中国诗歌走向世界持怀疑态度,这样的接轨根本不能让外人真正理解中国诗歌,从诗歌中窥探到一种属于中国式的民族精神,也不能真正地唤醒人们对汉语诗歌的热爱。接轨不能改变现状,就象商业不能解决穷人,权力不能解决奴隶,造反不能解决皇帝一样。记得我早期读到伊沙的诗作时,包括《饿死诗人》等,我对这个充满自信的伊沙怀有相当高的眺望,当我读到《唐》时,我终于读到了一个对自己写作充满自信的伊沙死去了,同时一个忙于接轨忙于获得西方世界承认的诗歌怪物诞生了。可喜的是在这场可笑的中国诗歌走向世界的运动中,还有一部分诗人保持了自己独有的品性,他们远离热闹的中国主流诗歌在中国最为僻远的地方默默地进行诗歌写作。无疑,第三条道路诗派主要推动者庞清明便是这样一位值得期许的诗人,他新近出版的诗集《孤独骑士之歌》(四川民族出版社)印证了他一贯的美学追求与诗意担当。
庞清明从较为偏远的川东北迁居到这个南方繁华的边地乡镇,并没有丧失一个大巴山之子天生的悲悯之心。他没有像许多诗人们那样绞尽脑汁去与大城市的诗人接轨,以获得那些虚假的承认或者虚空的名声,来贩卖诗歌拓本,争取一个可疑的江湖地位。他的诗歌文本还站在他正处的社会现实生活中,还在诗歌中直面自己真实的内心,还保留着一个诗写者纯粹的诗歌理想精神,还在写着社会批判最为实际的文本。我们还能从他诗歌找到这样的句子,“这丰娆之躯集合起所有的美誉/一半坦露一半保守密底/在声色光影间盈科而行/若隐现在时间麾下的植物兽/三姐妹昼伏夜出
仿佛,颓废的蝙蝠
展开搜捕的良辰/……”这些诗句印证了他在自己的诗集《跨越》中说过的一句话:“在这个堕落物化的时代,诗人肩起拯救灵魂的天职,以个体面对大众,唤醒普遍的良知。”而这些正是我们当下诗歌最为缺少的那一部分。有时作为一个诗写者,一个知识分子,我会不断地想起左琴科说过的一句话:“我们知识分子对这时代的堕落负有责任。”可是面对这个时代,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中产生的是什么呢?沉浸在虚构的寓言与赤裸的性欲中的小说家们!自慰似的下半身与填字游戏的诗人们!灯红酒绿的小资与麻木的田园牧歌的散文家们!一群没有骨头在故纸堆里贩卖着西方的壮阳药的思想家们!躲在背后当着独立董事的丧失同情心与怜悯心的经济学家们!在这个诗歌只是一个悲剧的年代里,作为诗写者,他应该是一个纯粹的理想者,他应该有勇气去揭示生命的渴望、揭露生存的悲喜根源、揭开生活中人性的异化与困惑,这是诗人也是诗歌本身应当承受的责任。
中国当代诗歌写作,诗人们的作品不是越来越深人人的内心,而是越来越趋向于肤浅的感官刺激——或者是下半身们的肉欲感官,或者是所谓知识分子写作表面技巧,表面化的形式越来越令人不得不怀疑,中国当代诗歌越来越像一只只红漆马桶,外表是何其的耀眼炫目,里面却是充满了一股腐朽臭味。而那些所谓的诗歌江湖“大佬们”从来没有打算去清理这个诗歌马桶中的腐臭味,而是一次又一次地去将那只红漆马桶不负责任地刷红漆刷绿漆做外表处理,或者干脆“江湖义气”地捂住腐臭,以维护他们可耻的诗歌江湖马桶地位。中国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不仅仅造就了一些在政治上、经济上外强中干的自娱自乐的自我麻醉狂,他们为了一个个可疑的面子,不断地在抽打着自己的耳光,在自我制造的谎言中生活着,在文化上同样也造就了这样一批人。××主义与流派在诗人们手中不知举过多少茬了,还是没有拯救质量日益下滑的诗歌。在这个年代里,只有扎实的感人的诗歌文本才能唤醒人们对诗歌从内心上的热爱。同时一个真正的诗写者没有必要为自己诗歌创作的自由心灵去找一个主义、流派、旗帜之类的枷锁,使自己的创作不自由起来。他面对的应该是自己广阔的内心与社会现实以及数千年沉淀下的民族文化传统,他是为自由的内心而写诗。读庞清明诗歌便让我有了这样的一种感受,他用时而口语,时而知识分子化的语言来言说自己的内心与社会现实,语言只是服务与服从于他诗歌真实的内心,只是作为表达他内心的一种工具而已,决不会成为诗歌本质。在他的南方乡镇系列中“升降机传递置业者的酣梦/大理石砸向废弃的木料/倒悬的原油桶滚落阴沟/断续的啸叫若遗漏的水……”在当代诗歌的语境越来越趋向于当下日常的鸡零狗碎叙事性的流水账中还能读到如此秉持诗歌理想,并且不断追问生命本真意义,有着沉重的使命感的诗句,是很令人意外的。在这个物质文明以及商品化高度集中的南方开放小镇上生活了十多年的庞清明还以一种中国传统的道义精神在诗歌中固执地呼唤我们正在逐渐消失的人性良知、家园归宿感、生命和谐感的人文精神。虽然我知道他是第三条道路上最为重要的诗人之一,但是第三条道路在庞清明的眼里只是一片打碎了知识分子写作与口语写作等主义的精神枷锁与幻梦的自由写作者的开阔地,它只是一群不满于诗歌江湖功利的霸权之争的纯粹的自由诗人的出入地,它从来不会提倡某种狭隘的主义、宣言以及一些所谓方向性的诗歌拓本,更不会是一群自由的诗歌心灵带上某种方向性的枷锁。
阅读庞清明的诗作,我为他诗歌中的那种宗教精神感怀着。一直以来,我认为中国诗歌最为缺少的不是先锋或者其他,而是缺少一种诗歌宗教精神,缺少诗歌宗教中那种容忍、坚韧的气息,虽然有不少人企图用流派或者主义的狂热代替这种诗歌宗教的坚韧,结果注定失败,因为诗歌流派在中国当代诗坛往往成为一种诗歌夺权运动的代名词。而另外一些人常常把诗歌当作一门技艺,诗歌创作不再是源于诗人内心的冲动,而是源于技艺的炫耀。诗人在写作过程中把诗歌当作一条木凳一把椅子一样不断地打磨。我一直反对把诗歌当作技艺,中国诗坛上充满了外表让所谓的技艺与技术打磨得光滑平整却没有诗人内在真实感情的虚伪诗,翻开各大诗刊,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大多数是那些虚伪的乡村诗,虚假的下半身,虚构的日常主义……它们跟这个虚荣的时代是如此接轨。阅读庞清明的诗让我知道一个真正的诗人从来不会把他笔下的诗歌当作一种器具,也不会当作一种手艺,诗歌对他来说是一种内在的生命,一种具有血性的生命。他不会让他的诗歌从他的真实生命中抽身而出,去进行外表的打磨,虚伪的遮掩,他总是不断地在他的诗歌中挺身而进,将内心真实的呼吸、节奏、思维在他的诗作中呈现出来。作为一个抛离故土的漫游者,他在诗中是如此挺身而进,如此与他的现实见证相拍相合的,“麻雀浪掷的生命烟枪戳害的君子,饕餮之徒的美食靓汤/如鱼得水的奸商抽空法律……他看见/裸肩露腹的小姐逶迤在仿欧柱廊/游戏从霓虹的迷蒙开始”。作为一个世俗化的基督教徒,一位自认为迷途的羔羊,宗教意识在他的诗中不断涌动:“古老的还乡者——大地的影子,变成树树成河/高处的圣杯濯洗一世的裸足”,从这样的诗句中我们可以窥探到,作为一个诗者的庞清明是不断将自己真实生活插进诗歌中,并且在那里找到了它们生存的位置,它们是如此生机勃勃,充满了生命的血肉感,与流行在诗坛上的那样装饰得美轮美奂的僵尸诗有着何其大的区别。
阅读庞清明的诗歌,我常常会感受到他是那样不由自主地陷入到词语所带给他的节奏中和现实的幻影中。南方的快节奏使得他的语言充满了焦灼,因此在他的诗句中常常会感受到由词语对现实的撞击所产生的恍惚的幻觉的迷醉之美。小报记者的生涯又培养了他对现实敏锐而细致的观察力,使他能够在现实的细微之处找到一种令生存在眩晕中的真实体验,这种体验源于他城市生活中物件转变为诗中意象而产生出一种隐喻、夸张、变形的语言幻美,更重要的是他借助这种幻美感观完成一个记者式的冷静态度——客观地处理当下现实,完成他诗歌中对当下生活的介入与揭示。
诗歌在更多方面来说是一个诗写者内心的抒情,虽然叙事的介入拓展了诗歌的视野,但是它同时带给了诗歌伤害,因为诗歌本身对叙事的局限以及叙事对文体的要求,使得叙事常常破坏诗歌内在速度与整体性的完整,使得诗歌呈现出枝枝节节的琐碎,哪怕这种琐碎在诗歌中是感人的。叙事最为动人之处是细节带给我们的感动,而细节的描述常常会在要求简捷的诗歌中呈现出语言上的哕嗦与结构上的累赘。庞清明的诗歌同样因为这种叙事从另一方面带来意象与视觉上的繁琐。在诗歌中叙事,最为重要的是叙事对象的选用,不是所有的叙事都能进入诗歌。相信庞清明在以后会逐步体味到在诗歌中叙事的典型性的微妙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