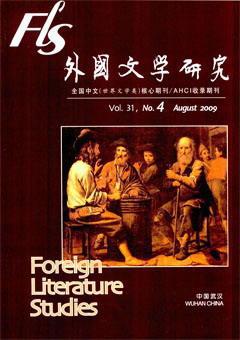流放即归家:论阿列克斯.米勒的《祖先游戏》
马丽莉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探讨澳大利亚作家阿列克斯·米勒的小说《祖先游戏》中有关流放的主题。这部小说在连接和断开之间,过去和现在之间,移民和移置之间,都有所描述并达到和解。对于书中人物双重文化下的流放生活,米勒的观点是积极乐观的。他认为,这种“二态”性的生活是一种神圣的礼物,而非生活的障碍。这与赛义德“双重凝视”的观点是不谋而合的。
关键词:《祖先游戏》流放双重凝视
阿列克斯·米勒出生于英国,16岁移民澳洲,毕业于墨尔本大学英文和历史系。《祖先游戏》是米勒的第三部小说,是作者四年辛苦劳作的结晶。此书获1993年迈尔斯·弗兰克林奖、联邦作家奖以及芭芭拉·拉姆斯登最佳小说奖。故事的起因来自一个老朋友浪子的自杀。叙述者史蒂文·缪是一个居住在澳大利亚的苏格兰作家,在英国安葬完父亲,回到墨尔本后,深深为一名澳大利亚华裔美术教师浪子错综复杂的出身所吸引;同时,他也正为自己父母的疏远而困惑。这种情形下,史蒂文开始了为朋友浪子寻找身份和祖先之旅。小说的结尾似乎给这位自杀的艺术家朋友提供了一个暗示:完全地属于某个地方即是失去了个人的自由;要想获得绝对的自由,就不要隶属于任何地方。这与米勒自身的经历息息相关。他也是从英国移民澳洲,最终对自己身处异乡的境遇处之泰然的(Carbines 9)。故事取材于作者本人的真实经历,因此,这部探讨种族身份归属的小说充满现实意义。
小说打破传统的对亚洲“滞定性”的刻画,运用“超出亚洲形象之手法,把澳洲和中国的历史进行连接”(Whitloek 25)。米勒为流放的人群提供了积极正面的选择而非将他们刻画成缺乏的和处于劣势的群体。小说是有关背井离乡的人在复杂纷纭的世界上寻找自己地位和身份的主题。并且,由于小说涉及两个国家、多重文化、祖先后辈,必然涉及双重视角这一主题。本文借用赛义德关于放逐的论述,探讨《祖先游戏》中有关流放的主题。通过解读小说的主要人物及其流放的生存状态、心理等方面的错位后指出:对于双重文化下的生活,米勒的观点是积极乐观的。他认为,这种“二态”性的生活是一种神圣的礼物,而非生活的障碍,正如他在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对有些人而言,流放是唯一可以忍受的境地。对他们来说,流放即归家”(264)。
一、浪子的“流放”与迷失
《祖先游戏》中故事与故事层叠,主要线索为冯氏和黄氏家族;浪子是连接这两个家族的人物,也是本书的起始和终止。从一出生,浪子就过着双重的生活。一方面,他的学者画家外祖父希望向他灌输中国的传统;另一方面,他的崇洋反古的父亲决意要把他按西方的方式养大。在他身上,承载着两代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希望。因此,他在杭州,讲国语,着汉服;而到了上海却讲英文,穿西装。这对于幼年的浪子来说,无疑是一种撕裂、一种身份的无所适从和地域的无所归属。恐怕那个时候,已经种下了浪子后来无法摆脱的放逐感。
浪子往返于杭州上海,却不属于任何一个城市。孩提时的浪子开始寻求自我身份。他首先毁掉祖先牌位,祛除先辈影响。六岁时,他把外祖父的经书焚烧,把他的古镜抛到河里。那是一面伴随着整个家族数世纪的一面镜子,上面雕刻着两只凤凰,象征着和谐,代表着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也许正是这一抛弃祖先的举动,才使得后来的浪子,在异乡中一直缺乏安全感,精神上无根无基,无所依靠,最终走向自杀。浪子和他的朋友史蒂文·缪一直有一种美好的期许:那就是浪子回到中国,与他的祖国母亲团聚。这一愿望最终没有得以实现,也许正因为此,浪子才客死他乡。
的确,两个地方同时作用于一个人身上,会让人产生一种错位的感觉。原因即斯图亚特·霍尔所说的“相似和连续以及差异和断裂(的同时作用)”(Hall 113)。对于浪子来说,穿梭于两个城市之间,使得他产生“差异和断裂”,从而感觉到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个。只有在和母亲独处的第三空间里,他才有家的感觉,觉得是属于母亲的。“在上海和杭州之间的上百次旅行,惟有和母亲一起呆在包厢里,他才感到温暖安全,这是一个他唯一可以在所谓自己的地方享受家的感觉的时刻”(193)。
这种安全感浪子在澳大利亚39年从未经历过。这可能源于浪子试图摆脱祖先的桎梏。从童年到成人,从古老的杭州到现代的墨尔本,这种摆脱祖先、抛弃传统的心理始终伴随着他,也使他付出了代价:那就是无所不在的无根状态和心理错位。透过浪子最终自杀的结局,米勒似乎在暗示:一个脱离祖先的人是不可能有健全的异域生活的。换言之,流放的生活不是以弃绝祖先、失去故土而存在的;积极的二态生活应该是祖先与后辈并置,传统与现代结合的。
二、莲的二态生活
小说中的女性试图在新的环境下发现自我,确立身份,但并不完全与过去隔绝。新的环境不仅带给她们错位感,更能使她们产生新的“混杂”身份。女性角色既重现祖先的历史,又变为后辈的祖先。她们在承上启下,连接历史上的积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这一部分我们探讨以莲为代表的女性人物的二态生活及其历史使命。
身为浪子的母亲,莲在中间也过着二态的生活。她是联结儿子浪子与父亲黄玉华的纽带——她以自己的错位为代价在两个世界之间达成妥协与和解,她的命运分成两部分。一方面,她是一个反抗父权机制的具有现代意识的女性;另一方面,她也是一个游弋在传统中国与西方工业文明之间的个体。
上海和杭州两个地方对于莲和浪子母子都具有双重意义。传统的杭州是母子精神之避难所,能带给二人安全温暖;而上海则了无生气,甚至令人失去生育能力。因此上海的大都市生活反而扼杀新的生命:莲的两个儿子生下就死亡这样的事实也说明上海之新生活离不开祖先杭州的养育;新兴的现代化不能替代古老的、有根基的中华文明。
莲是女儿又是母亲,是新旧世界的联结。她的父亲唯恐失去她:父亲希望父女俩的世界不受任何打扰,甚至不想在这个世界中加入浪子。因为他觉得浪子的眼光代表其父亲“在嘲讽我们中国式的生活方式,等着看我们的毁灭”,他去祭拜祖先时欲抛开浪子,莲因此感到进退两难:既不愿违背父命,又不想“背叛”儿子(182)。
与浪子不同的是:莲对这种二态的生活运用得较好。她在父辈与晚辈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能够自由穿梭来往,并产生新的创造力。莲觉得活在自己身上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人。对于这两个人,最终莲都能接受(85)。莲的故事似乎在暗示:虽然挣扎,游移,新旧两个世界是不可切割的。就像苏菲·梅森所说:我们的过去造就我们的今日,形成我们的行为或思想(Masson 5)。如史碧斯大夫所说:新生命来自老生命。两个生命合二为一。俩者既分开又联合。由一个肉体分离而来。她的纽带作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她女性的身份。一个女性,在上个世纪的中国,要想反传统,并非易事。虽然困难,她还是传承了传统,展望了未来,在一个中间地带构建了自己的身份和归属感。
小说中的另外两位女性维多利亚·冯以及格特鲁德也是父辈文化的联结者和继承者,从她们身上,人们似乎可以看到“充满生气的晚辈,不负父望,担负起祖先的重任,重新将逝
者的空间填续。这样一来,她们不但了却先辈遗愿,也同时成就了自己”(299)。
以莲为代表的女性们在续写父辈的历史中,发现自己,了解祖先;既传承了历史,也完成了个人的成长。这不能不说是对女性承载历史使命的肯定和期望。她们没有像浪子一样面对异域生活无所适从,因而选择自杀;她们的选择是积极的、具有开创和建设意义的。对于我们现实社会的中国移民们,仍然具有非常正面的启示意义。
三、祖先与后辈错位与传承
《祖先游戏》中,父辈的生活也有所描述。作为祖先,他们与后辈的关系,他们以及晚辈所经历的错位,他们自己给与后辈的遗留,都在小说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他们作用的描写,更加深化了小说的有关流放与二态生活的主题。
史蒂文和浪子与其父辈的不和在小说的前三分之一非常明显。但是当史蒂文意识到格特鲁德将她父亲,维多利亚将她父辈的生命融入自己的生命时,他似乎比从前更能理解自己的父辈。浪子被父亲邀请到屋顶眺望台的时刻,两代人之间似乎达成了和解。这一点在浪子来到澳大利亚之前更加明显。父子俩站在楼上的屋顶可以嘹望到很远,似乎可以穿越墙壁,越过地平线,看到此生之外。浪子与曾祖父认同这一点也许在暗示:他来到澳洲正是完成生命旅程而非与之隔绝。换言之,他来到澳洲既是“归家”。正应了史碧斯大夫所言:浪子的意思是远行的儿子。他有一天会踏上寻根之旅。如果他幸运,他会如我一样,在奔向终点时永远地奔向起点(116)。遗憾的是,浪子始终未能巧妙地利用自己的二态身份,未能在两种文化中达到和解而最终走向自杀。在他身上,人们更多地看到错位,没有发现传承。
在现代社会,流放的感觉不独产生于远离故土,它同样可以产生于家庭内部。米勒书中使用了眺望台这个概念。这个能指的所指为“进入其他世界的通道”(158),从里面出来后,浪子感觉到:在眺望台内,经历过独处的冥思后发现独处的魅力——这些眺望台里面的人可以站在一个比普通人高的角度,产出更好的“文学作品”(157)。赛义德关于背井离乡(流放)的论述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小说中的人物:
事实是:对于大多数背井离乡的人来讲,难题不仅仅是被迫离开家乡居住;而且还,有更多的内容。生活在现今的世界上,有太多的提示物告诉你你是一个背井离乡者,你的家事实上就在不远的地方,当代生活的每天的正常交往都不断地让你离老家既近,却又触摸不到,徒然着急。因此,流放的人处于一种中间境地:既不完全属于新的环境,又没有完全摆脱旧的,在半卷入,半超然的状态下徘徊;一方面既怀旧又感伤,另一方面却既是表面上娴熟的模仿者,在私下里确是被遗弃的人。
事实上,远离人群(祖先),远离熟稔的文化(祖国)能使人暂时沉静地思索从前从未思索的东西。这恰恰是“流放”的优势:距离感和与他人的疏离关系可以使人炮制出具有混杂特征的作品。就像米勒所理解的:“出世和离家正是文艺创作的开始。这也是文明的开始。历史的开始”(157)。同样地,萨特丹·南丹也曾说过,距离和抽离是非常重要的——抽身远离是使人产生超凡脱俗的观点的先决条件之一(Nandan 61)。对米勒而言,澳大利亚正是这样一个可以经历不同文化和混杂的眺望台。
《祖先游戏》中叙述方面的错位与其他错位比肩而存。米勒使用了许多的叙事技巧:意识流、日记体、信件、翻译和画作。这些叙事形式表明:一个人的身份也像语言一样需要超越和翻译。同样,对于语言的理解,要加上说者和听者双方的共同参与。因此,对于小说的理解,读者身上的担子也很重。小说表面上的松散结构,也促使读者不得不重新安排故事情节。这一点又反过来强化了时空的错置感。如果重塑得好,才会领略到故事之间是有机结合,构成整体的。正像黄源深所说,小说中的祖先情结具有三个方面的含义:普世的、本土的以及象征的。
海伦·丹尼尔认为,《祖先游戏》是一个具有双重凝视的双面神般的小说。它的内里总会映出外部时空的全部风景(Daniel 9)。赛义德也认为此种“双重凝视”是优势。对他而言,流亡是一种模式(萨依德57)。它的积极意义在于可以从“双重”的而非“孤立”的角度看待事物。从这一点上,米勒和赛义德是不谋而合的。他们都认为:“流放的知识分子不必应合传统的逻辑而可以大胆前行,他们代表变化,代表前进而非原地踏步”(Said 47)。同样地,法裔澳大利亚作家苏菲·梅森也把移民境地描写为“祝福”。她指出,在自己的祖国和宿主国居住都令人不安的确是一种诅咒,但它可以转化为“祝福”。她认为移民们应该感到“强壮”、“无惧”,“移民完全可以坚定大胆地让现实进入他们的生活,但要有所质疑,在了解之后进行选择”(Masson 5)。
总之,移民或日流放,是远离熟悉的事物。这就要求人们不但有胆量还要有能力:有胆量承受孤独寂寞,以及无所适从感;有能力适应新生活,接受差异性。不一定要弃绝某种旧的观念,而要装入新的内容。在这种承受和接受中进步。将诅咒变为祝福,就像米勒笔下所引用的凤凰涅槃一样,获得新生,获得生命和创造力。
在《祖先游戏》中,米勒将现在的时间置于历史的旁侧,从世界不同的地方收集资料,叙述流放生活积极的意义。在现代社会,我们都在追寻。然而我们继承的和我们经历的或许同样重要。它们共同作用于我们的生活。必须承认:我们的祖先对于我们现代的生活是有正面的影响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的生存方式多多少少都有某种被流放的印记。如何巧妙地运用这种生存方式而非为它所囿;如何变诅咒为祝福,也许是小说的主人公以及我们每个现代人要学习的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