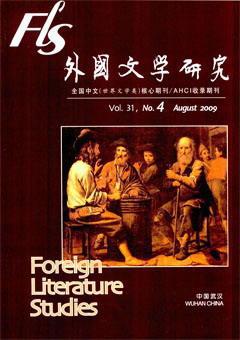乔叟《公爵夫人之书》中的“自然”
李 安
内容提要:《公爵夫人之书》是乔叟的第一部重要诗作,它包含的神学观念和人生追求在诗人以后的创作中被不间断地延续了下去。从诗中的“自然”一词来看,它首先指作为创造者的自然之神,这位神祗运用和谐的自然法则呵护和指引万物合理生存,赐予人类爱的天性,使人类因爱而品性高贵、生活美满,还用人性的、现实主义的方式抚慰人类的痛苦和创伤。“自然”的丰富内涵使这首悼亡诗最终赞美了人性的美好、讴歌尘世世界中的幸福。
关键词:乔叟《公爵夫人之书》自然
杰弗里·乔叟(Geoffrey Chaucer,约1343-1400)约于1368年创作的《公爵夫人之书》(Book of The Duchesse)是为他的庇护人兰开斯特公爵的妻子患黑死病去世这一事件而作的,它采用中世纪常见的梦幻框架,其内容是叙述者在梦中遇见一位忧郁的黑衣骑士,骑士描述他的美丽高贵的意中人以及和她相爱的经历,但她已经去世,骑士只有悲伤。这部作品向来较少为国内研究者关注,作为诗人第一部长篇英语诗作,它的探索性和试验性色彩很重,但仍旧显示出了诗人独有的创作风格,理解这首诗对于认识他后来更为成熟的作品很有帮助。本文从作品中的“自然”一词人手,探讨由这个词折射出的乔叟的神学观念和人生追求。
单词“自然”(nature)在诗中共出现七次(18,467,631,715,871,908,1195),其中四处的首写字母是大写(467,871,908,1195),指由概念“nature”拟人化和神圣化而成的“自然之神”。还有一个与“nature”相近的词“kynde”(kind),一共出现四次(16,56,494,512),首写字母都是小写。此外,其衍生词"kindely”出现了两次(761,778)。
一、作为创造者的“自然”
“nature”在诗中最首要的功能是创造生命(715,1195)。第1195行的“自然”是大写,意指自然之神,而且从第871行"the goddesse,dame Nature”的用法来看,应指女性的神。第715行提到的“自然”用的是小写字母,但此处的“是它创造了你的生命”(716)用的与第1195行的“自然”完全相同的术语“form”和“creature”,因此应当也是指自然女神。
在骑士向诗中的叙述者夸耀他的意中人的部分中,指出其美丽的容颜和良好的德性都来自自然女神(Nature)的打造。容颜的好坏体现神对此人喜爱的程度,骑士的意中人是“自然女神创造的美丽的首要的模本/和她的所有杰作的首要的典范/以及原型……”(910-912)可谓世间最美丽的女子。这位女性除了外表极为美丽之外,待人接物平等慷慨,举手投足中处处可见其端庄、真诚:[她的眼睛里]没有丝毫虚假,她的纯真的眼神,是那位自然女神(dame Nature)使她的双眸适度张开,再适度闭合。她也从不快乐得过头,她的眼神既不愚笨,也不轻率,即使是在游戏时;我想,她的双眼似乎总是在说,“上帝知道,我的罪过将得到宽恕!”(869-877)
眼睛是了解人物内心之美的一个窗口,可见她的外在形貌和内在灵魂的和谐状态是完全一致的。这种适度的模式折射出自然女神创造万物时采纳的方式。诗人大约创作于1380年的长诗《百鸟议会》(The Parliament of Fowls)中,更明确地显示了这一创造理念:“自然女神,全能上帝的(人间)代理(vicaire),/把热与冷、重与轻、湿与干/按照和谐的韵律结合在一起”(Chaucer,The Works of Geoffrey Chaucer 314)。把不同性质的东西按照和谐的原则调制出节制、适中的道德品行,这种创造方式使自然女神的创造物的性质复杂起来,而能够成为万物的“典范”或“原型”的骑士的意中人的形象也有着丰富的生命内涵。乔叟在其他作品中赞美的女性形象基本上都与她类似,如《百鸟议会》中的雌鹰、《特洛勒斯与克丽西德》中的克丽西德、《贞女记》序言中的女王阿尔赛丝、“医生的故事”中贞洁的维吉尼娅、“学士的故事”中的侯爵夫人格里泽尔达、“平民地主的故事”中骑士的妻子道丽甘等。由此可知,自然女神认为完美的女性应当具备这样美丽的形貌和适中的德性。同时,《百鸟议会》中自然女神拥有的代理人(vicaire)的称号直接与创世的上帝产生关联,并且在诗人最后的作品《坎特伯雷故事》中有更具体的解说:因为创造了万物的至高之神把他总代表(vicaire general)之职派给我担任,让我对世上的大小万物负责,按我的心意给他们赋形、着色,因为月亮下的一切归我照料。我干这工作并不求任何回报。我主的看法与我的完全一致,我使她(引者注:维吉尼娅)美,为了对我主表敬意。其他的万物,无论形象或色彩,也全都出自我的手,无一例外。(乔叟,《坎特伯雷故事》428)
自然女神的“代理”(vicaire)的头衔在里尔的阿兰(Alan of Lille,约1116-1202)的《自然怨》(De panctuNaturae)的第453、476行和中世纪叙事诗《玫瑰传奇》的第16872、19507行中都出现过。这里显示出自然女神与上帝之间的主从关系。骑士意中人的心语“上帝知道,我的罪过将得到宽恕”说明上帝认同和赞许自然女神的创造活动。“我干这工作并不求任何回报。/我主的看法与我的完全一致,”可见上帝与自然女神两者功绩的同一性。“对我主表敬意”强调了自然女神对上帝的从属地位。“全都出自我的手,无一例外”这句似乎是指上帝退居幕后,不再亲自受理人间事务了。但自然女神来自抽象概念“自然”的拟人化,这个寓言式的形象只是上帝的理念在尘世世界中的一种具体表现而已,也就是说,自然女神的行为就是上帝的行为。
但自然女神的创造活动遇到一个强劲的对手———命运女神,在关于她的诗行中也有一个"nature”:“她最大的荣誉和最出色的表现/是撒谎,因为这正是她的本性(nature)”(630-631)。非真即假,撒谎的命运女神没有信念、行为准则、节制(632-634),所以她给人带来的只能是厄运。黑衣骑士用自己与命运女神进行的一次对弈比喻他痛失意中人的事件,因为命运女神是用欺诈的方式取胜的,所以招来骑士的痛恨和咒骂。这是自身无过错的人类与采用卑鄙手段的神祗的交锋。诗人对命运的成熟的思考应该是在翻译波依修斯(Bo—ethius)的《哲学的慰藉》(De Consolatione Philosophiae,约1381-1386年翻译)后才形成的,在差不多同一时期创作的《特洛勒斯与克丽西德》(Troilus and Cryseyde)以及短诗《命运》(Fortune)中,他和波依修斯一样把命运置于上帝更为宏大的计划之中,使它与宇宙的内在必然性联系起来。与之相比,本诗中骑士遭遇到的命运女神是一种更加偶然外在的侵犯力量,命运女神作为一种邪恶势力来自何方,在宇宙的必然世界中处于什么位置,上帝对这位
神祗的所作所为的态度如何,在这次交锋中人类自身是否也存在过失,等等,诗人没有谈及。可以确认的内容是,骑士知道在与命运女神的博弈中他必输无疑,但他从不认为与之抗争是浪费时间,而只是希望能让他正大光明的抗争更有力量些,并坦率地承认如果和她交换角色,他也会同样吃掉对手的棋子。这显示出骑士相当冷静现实的一面,也从另一个角度展现了他不屈不挠、积极进取的精神。叙述者还用苏格拉底的典故进行点评:“他(苏格拉底——引者注)认为命运女神所做的一切/都不值一文”(718-719)。在谴责了命运女神之后,骑士紧接着又赞美自己的意中人,感谢自然女神的恩惠,可见自然女神作为上帝的代理人的统治地位并未受到影响。
命运女神的本质是虚假,所以她的外表丑陋,行为邪恶。赐予万物生命、创造一切美和善的自然女神执行上帝的旨意,真实是她的本质。在很大程度上,这是抽象的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对立。诗人在赞美自然女神的同时,也赞美了人类世界。
二、呵护生命的自然
前文已述,自然女神越喜爱、越悉心打造的生命,就越是美丽动人、品德高贵,并使之成为其他被造物的原型和仿效对象,她必然希望这种美善能够被延续下去。
在这首诗一开始,叙述者抱怨自己忍受了八年失眠的痛苦,肉体与精神都倍受煎熬,以至于自然女神警告他有丧失生命之忧(16-21)。而叙述者在梦中遇到黑衣骑士时,发现他独自一人远离人群,吟诵一首哀怨的诗歌,神情极为悲痛,叙述者很是诧异,想到“自然之神”不可能容忍一个人如此悲伤(467-469)。从自然女神按照和谐的原则创造万物的模式来看,她并非仅仅提倡欣喜、欢乐而完全排斥愤怒、悲哀等负面的情感,对于人体的生理机能也是如此。重要的是不同的情感和元素调配得宜。诗人强调超越了适中的自然原则的失眠和悲伤可能会导致死亡,而自然女神出于善的动机在尘世间创造美好的生命,她期望这种美善能够被表现出来并延续下去。
虽然乔叟在诗中三次提到了死亡,骑士表示希望和意中入一样死去,感叹自己命中注定遭受不幸,把蒙受的损失归咎于命运女神对他的幸福生活的妒忌和背叛,这些是传统悼亡诗中常见的主题。但这首诗与传统的悼亡诗相比有明显的不同,“其中首先令我们印象深刻的是诗中没有已经成为悼亡诗的‘传统主题的某些不变的特征,例如对尘世万物的短暂、死亡的无情、以及最重要的对来世的沉思”(Clemen 45)。甚至骑士在悲叹自己幸福生活的结束时,也没有否定已经历过的幸福生活的意思,可以说,越是死亡带走了他曾经拥有的幸福的爱情生活,他越是强烈地回顾和讴歌这种生活,由此使得“《公爵夫人之书》成为一首关于死亡的诗,它歌颂了生活”(Pearsall 89)。参照乔叟后期重要的诗作《特洛勒斯与克丽西德》的结尾,不遗余力地追随爱情的特洛勒斯在失去爱情、战斗身亡后,他的灵魂在天国俯瞰地球,否定了自己生前付出的全部努力,“对比天国那完美的幸福,/尘世只是虚空和徒然”(乔叟,《特洛勒斯与克丽西德》374)。由此看来,《公爵夫人之书》的确可以说是“完全世俗的”(Brewer 58)。在这个基础上又可以推理出自然女神与死亡的对立关系。
自然女神除了亲历亲为地创造和保护她的创造物之外,还为她的创造物们设置了一定的延续生命、自我救治的功能。在诗中,叙述者目睹了骑士过度悲痛的情绪影响到他的心脏,他从生理学的角度解释这一现象:“由于极度悲伤,他的血液涌向心脏/使他温暖起来[恢复活力]——/因为血液感觉到心脏受到伤害——/这也可以明白为何自然(kynde)感到担忧/并且努力使它(自然——引者注)宽慰……”(490-494)人体内部各个器官之间能相互感应,血液察觉到心脏受到的威胁后,马上促使全身的血液都涌过去予以保护,诗人还引用脸部因此而缺血、脸色苍白这一症状来佐证血液的流向。此处的“自然”(kynde)一词没有使用大写字母,但“自然感到担忧”、“使它宽慰”这样拟人化的语言表明了它应该与神性自然存在某种关联,而以下引文能显示出kynde和nature两个术语之间的关系:你们知道,[这样的生活是]违反自然(kynde)的而只有依照自然的方式[我们]才能生活;自然(nature)不会允许地上的生命长时间忍受着没有睡眠且深陷痛苦[而没有死掉]。(16-21)
前文已述,“kynde/kinde”一词在本诗中出现四次,除了前面引文中两次之外,另两处是指古典时期的自然法则(the 1awe of kinde)(56)和把古典异教神话中的牧神潘(Pan)称为“自然之神”(god 0f kynde)(512)。除了异教神一处之外,其他三处都是指世俗世界中存在的某些功能、规律或法则。在基督教世界中,异教神当然是被排斥或贬抑的,所以诗中在提到牧神潘时,还要用不确定的口气说是“人们称之为自然之神”。此外,诗中两次出现的副词“kyndely”(761,778)指的是人的天性中的自然情感倾向。但“nature”在诗中没有相应的副词。前文已述,大写的“Nature”是在基督教神学语境下抽象的“自然”概念的神性化表达,而小写的"nature”在诗中还指同样由抽象概念神化而来的命运女神的本性。而命运女神在诗中具有与自然女神相同的威力,随时可带给人类灭顶之灾,这灾难即使是人类的保护者自然女神也阻止不了。相比而言,牧神潘在诗中仅仅起到一种装饰性的作用,“kynde”活动的领域不可能超出尘世的范围。
在这个意义上,第16至21行诗中“kynde”和“nature”两词分开使用不是诗人任意所为,二者各有所指。这里的“kynde”是自然之神为人类安排的生活模式,用神的命令确定下来要求人类遵守,目的在于保护生命安全。第490至499行诗所描述的人类生理上的自我救治功能,也是神意的结果。
从人类生理上的自我救治功能能察觉到自然女神对人类福祉的善意呵护,除此之外,还能发现自然女神借此给人类自由意志的发挥留下了足够的空间。从她的和谐的自然法则来看,她不是暴君式地命令人类奴隶式地服从她。能否享受到她赐予的幸福,还在于人类自己的选择。而人类独立自存的能力能够保障这种选择的权力得到实施,无论善恶、贵贱、成败、喜悲,人类都可争取到充分的回旋余地。所以,人类不但是自然女神温顺的臣民,也可以成为积极进取的自由人。
三、爱的天性
作为副词的"kindly”在诗中的运用也是对“自然”内涵的补充。这个词集中出现于黑衣骑士向叙述者介绍自己对爱神的服侍:“先生,”他说,“自从我年轻时开始有一点头脑,或者自然形成的(kyndely)看法,在自己的脑子里多多少少地了解一些爱情的知识,毫无疑问,我就从不间断地服从和供奉着爱神,完全出于虔诚的意图,并以作他的仆从为乐以虔诚的意志、躯体、内心,和所有的一切……”(759-768)
骑士如此心甘情愿地臣服于爱神,听从爱神的指令,目的在于取悦爱神,祈求爱情。服侍爱神、作爱神的侍从是典雅爱情(courtly love)诗歌中不可缺少的传统主题,副词kyndely
在这里修饰骑士服侍爱神的行为,它的意义应当从这一部分内容产生的背景和源头中追寻。基特里奇在20世纪初就指出第759至776行诗模仿纪尧姆·德·马肖(Guillaume deMaehaut,1300-1377)的法文诗《波希米亚王的公断》(Le Jugement dou Roy de Behaingne)(Kittredge,“Chauceriana”467),第777至804行模仿马肖的《命运的治疗》(Remede de For-tune)(Kittredge,“Guillaume de Machaut and The Rook of the Duchess”16-17)。但基特里奇同样指出这些内容也不是马肖的原创,更准确地说,事实上是“马肖熟知《玫瑰传奇》,乔叟也是”(Kittredge,“Guillaume de Machaut and The Book of the Duchess”14),两人共同的源头都应该在《玫瑰传奇》那里。
乔叟在14世纪60年代后期翻译了13世纪的法语诗歌《玫瑰传奇》(The Roman de laRose),乔叟的译稿题为The Romaunt of the Rose,现存于苏格兰城市格拉斯哥(Glasgow)的亨特列尔博物馆(Hunterian Museum)的译稿分A、B、C三组,共7696行英文诗,其中A组(1-1705)和B组(1706-5810)分别译自原诗第1至5154行,C组译自原诗第10679至12360行,一般学者都确认A组译稿的确为乔叟所译,但德里克·皮尔索坚持认为乔叟已经译出全文,只是它们没有完整地留存后世而已(Pearsall 81-82)。虽然今人只看到断片,应该可以肯定乔叟熟知《玫瑰传奇》的全部内容。《公爵夫人之书》写于乔叟1368年10月底由欧洲大陆返回英国之后,兰开斯特公爵的夫人布兰茜是当年9月12日去世的,所以一般学者认为此诗完成于1368年底或1369年初(肖明翰95),此时《玫瑰传奇》在诗人头脑中仍旧占据很重的分量。而C.S.路易斯更是肯定地认为,“在这首诗中,痛失爱人的情人经历了与《玫瑰传奇》中的做梦人经历的完全相同的所有阶段”(Lewis 168)。即服侍爱神,遇见意中人,求爱,被拒,始终如一地继续追求,被接受。路易斯亦举第775至778行诗为例证明两人的相似之处。
诗中骑士服侍爱神的这一段描写主要受到《玫瑰传奇》第1881至2022行的影响。在它的作者纪尧姆·德·洛利斯(Guillaume de Lorris,?-约1235年)笔下,做梦人通过爱之泉内的水晶石看到了玫瑰花丛中的一朵玫瑰花苞,觉得异常美丽动人。已经跟踪良久的爱神举弓向做梦人的心脏射了五箭,然后又为他的伤口涂上油膏,伤口虽然愈合,箭头却留在体内,所以做梦人既深感痛楚又饱尝甜蜜。这是第1881行之前的内容。紧接着爱神告诉他已经不可能逃走,不如心服口服地做他的囚徒。做梦人表示投降,并说:“我听到过太多关于你的美德的事迹,所以我交出我的心灵和身体为你效劳,完全听从你任意支配,因为如果是按照你的意愿行动,我不可能产生任何抱怨。我还相信,因为我心甘情愿地跪倒在你面前,终有一天我将得到我等待的恩惠”(de Lorris and de Meun 57)。爱神很满意他的服从,告诉他虽然做他的仆人会很痛苦和繁累,但他的仆人会从这服务中远离邪恶,变得高雅,获得巨大的声誉。经过亲吻和握手,臣服仪式完成,接下来爱神要求做梦人立誓永不背叛,做梦人回答说自己的心已经受爱神捆绑,再无他人能够支配,如果主人爱神不放心,就为它配制一把钥匙好了。爱神认为有理,取出一把金钥匙锁住他的心。最后,做梦人再次表示将尽忠于爱神,因为“一个战士如果不能让他的领主感到满意,他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他的服务没有任何价值”(de Lorris and de Meun 58)。第2022行到此为止。
骑士与做梦人相同之处在于服侍爱神的方式:像《圣经》中基督宣示的诫命“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太22:37,路10:27)一样,交出自己的全部肉体、灵魂、意志效劳于神,丝毫不以之为苦,但求得到神的喜悦和回馈。但《玫瑰传奇》中的爱神借助箭和锁的手段才降服、教育、约束和命令他的臣服者,并对臣服者的忠诚表示过怀疑,在乔叟这里,箭和锁变成了“自然而然”的方式。黑衣骑士作下侍奉爱神的决定时,自己并不知道其中的原因,“我相信这[决定]是自然而然地(kindely)来到我心里的”(778)。他还解释说,这一举动是由于自己无知轻率,容易接受其他事物,而爱情刚好最先占据了他的心灵,虽然他也有可能会去学习其他技艺或者研究一门学问。所以,没有伟大的神亲自出面引导,没有高尚耀眼的动机,没有深邃的关于爱的知识——他虔诚地供奉爱神的行为不需要原因。这不仅仅是一种乔叟式的谦虚,也是诗人对如何提升人的世俗生活价值这个问题的一种看法:通过发自内心的对爱的追寻,人生变得高贵和幸福。
前文介绍的“Nature”和“kind”都直接涉及自然女神,而诗中副词"kyndely”则指向爱神。在乔叟看来,人对爱神的臣服是指全心接受爱神的引导,而爱神对人的妥善引导能使此人变得高贵。当臣服者的行为达到足够的正确和高尚时,爱神会感到喜悦,赐予美好的典雅爱情。人类变得高贵、获得世间最美好的爱情,是自然女神乐于看到的。也就是说,自然女神创造生命、予人各种天性(包括爱的天性)、执行自然法则,而爱神则激活爱的天性,以其爱的法则敦促人达到言行举止优雅有礼,精神因虔诚向神而高贵,基督教的爱的诫命在人世间开花结果。因此,本诗中的“kindly”是自然女神制订的自然法则的一种扩展。
四、欢愉的大自然
《公爵夫人之书》中还有一个涉及古典异教时代典故的“kynde”。在作品开篇处,叙述者受失眠之苦,晚上无法入睡,只好用阅读的方式消磨漫漫长夜。他读的书是古代的学者用诗歌的形式记载下来的神话和传说,诗人在此特意补充了一句:“那时的人热爱自然法则(the lawe of kinde)”(56)。由这一处“自然法则”可以追寻到诗人对古典思想和现实生活两个领域的态度。
他从这本书中读到的是国王塞克司(Seys)和王后亚克安娜(Alcyone)的悲剧故事:塞克司出海遇难,尸骨无存。王后见丈夫音讯全无,极为忧伤,向女神朱诺(Juno)祷告。朱诺施展法术使她入睡,差遣睡神莫菲斯(Morpheus)以塞克司的形象出现在王后梦中,告知国王已死的真相,王后几天后也伤心而逝。这个故事来自奥维德的《变形记》(Metamorphoses)第二章第411至748行,马肖在他的《爱之源》(Le Dit de la Fonteinne Amoureuse/Fountain ofLove)第544至698行中转述过(Lynch 7)。乔叟称这个故事为浪漫故事(romaunee/ro-manee)。在乔叟的时代,浪漫故事(或浪漫文学)一般涉及两个题材,其一是骑士游侠冒险
故事,其二是骑士和他所爱慕的女士之间的典雅爱情。两个题材也可结合在一部作品中,常采用的表现手段是寓言或神话。擅长典雅爱情题材的马肖在他的作品中写入奥维德的这个故事时,已经把它归人中世纪浪漫文学的范畴了。无论乔叟是取材于《变形记》还是《爱之源》,他对塞克司和亚克安娜的故事的看法与马肖无疑是相同的,所以他的改写专注于突出国王与王后之间深厚的爱情。
贯穿整个基督教历史的是对异端邪说的打压,在征讨异教徒名义下进行的十字军东征,以及从13世纪开始建立起来的宗教裁判所,等等,在这种宗教背景下的乔叟对古典异教时代典故的推崇容易让现代人心生疑惑。实际上,中世纪的人们以基督诞生为分界线划分信仰时代,古代的人没有受洗,因此被划入异教徒范围,没有永生的机会,这一点,他们是很清楚的。但那个时代的人同时也缺少历史感,他们笔下的古人言谈举止与他们自己时代的人毫无分别,如《特洛勒斯与克丽西德》中的特洛伊王子所思所行完全是一名14世纪骑士的特征,似乎古代与中世纪之间的区别仅仅是神学方面的,即是否受过基督教的洗礼,信仰的是一神还是多神,能否在基督教的意识形态下获得永生等。除此之外,世俗领域里基本上难分彼此。所以这又是一种“基督教的中世纪与异教的古代之间含糊其词的关系”(Fyler349)。
在这个意义上,应该把乔叟夸赞的古典时代的“自然法则”放在中世纪来理解,它是中世纪式的“自然法则”,与前文论述的呵护人类生命的“自然”(kind)没有冲突。具体来说,诗人在这个“自然法则”下介绍了一个悲剧故事:男主人公身亡,女主人公殉情。同样写过这个故事的奥维德和马肖都提到两人变形为飞鸟继续相爱的情节(Lyneh 257,291),乔叟却没有写进去,因为他写这首诗的目的是安慰现实生活中刚丧妻的公爵,除了不需要这一个神话的结局之外,还有其他更为现实的动机。故事中死去的塞克司劝告亚克安娜,虽然两人曾经拥有过短暂的幸福时光,但他如今确实已经死了,所以她应当接受这个现实,“不要再过着这样忧伤的生活'/因为你的忧伤于事无补”(202-203)。“确切地说,死亡就是‘自然法则,正如塞克司与亚克安娜的故事所证明的”(Boitani 46)。在这个“自然法则”之下,骑士口中的命运女神成为一个可以接纳的神柢或理念,而亚克安娜没有听从劝告以至于悲伤身亡,又成为一个拒绝接受“自然法则”的例子。天人永隔,忧伤无益,这是乔叟间接地向丧妻的公爵传达的信息。
在诗中,叙述者读完塞克司和亚克安娜的故事之后,也模仿亚克安娜向睡神祈求,没想到马上就入睡了,他的失眠症得到治疗。这应该是“自然法则”的功效之一:顺其自然,就可以恢复正常的睡眠,停止痛苦,不用担心死亡了。随后的情节中提出关于死亡与复苏的论题,叙述者在睡梦中来到一处非常美丽的树林,在五月的天气里鲜花盛开,绿草如茵。它(大地——引者注)忘记了冬天通过寒冷的清晨带来的贫瘠,那让它忍受痛苦,也忘记了那些悲伤,很明显,这一切都已抛诸脑后。整片树林都变成了绿色;是甜美的露珠使这绿色蔓延。(410-415)这几行诗描绘出一幅冬去春来、万物复苏并欣欣向荣的景象。万物随着季节变化而由活跃转向沉寂,再转向热闹,这是自然世界每年都在上演着的剧本。值得注意的是,诗中虽然用了不少富于想象力的语言来描绘大地,但诗人却没有把它变成一个神话故事,拟人化的大地只能用“忘记”痛苦的方式来解决它的悲伤,不是补偿,更不是复原。随着时光流逝,春天来临,冬天遭受到的所有痛苦和悲伤都告结束,欢乐重新充溢整个世界。在这片浓郁的诗情画意中蕴藏着令人惊讶的现实主义精神。
接下来,出现于这片美景之中忧伤的骑士受到批评:“尽管牧神潘,人们称之为自然之神,/认为他完全不必如此忧伤”(512-513)。牧神潘在这里的位置一向受到研究者关注,有的学者认为他统治的“自然”是指人类之外的自然世界,或者是指“人类与动物分享相同的本质(kynde)”的那个“自然”(kynde),或者“特定地与自然(kynde)相关的植物生长变化过程”,总之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地位比自然女神低。自然女神与上帝头脑中抽象的自然理念相关,而古典的异教神潘是“god of kynde”,完全是尘世性的。牧神与自然女神一样不准许黑衣骑士有损伤自己身体的行为,所以把两位神祗划入互不相干的两个领域,似乎没有必要。诗人与其说引用一位古典神来呆板地劝诫黑衣骑士停止悲伤,不如说是在充满欢愉的自然世界中再加入一位活泼的神祗,并希望这种生机勃勃的气氛能感染黑衣骑士,把他从悲伤的情绪中拉出来。
乔叟作品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向来以木讷著称,在本文分析的这首诗中,得知骑士的意中人的死讯后,叙述者只说了两句话:“不!/这是你所指的损失?天啊,这真是一件伤心事!”(1309-1310)表面上看起来,叙述者完全没有安慰这位伤心人,实际上,他在对古典故事、美丽春色的介绍中说出的那些内容,就已经比写一堆廉价而不切实际的宽慰言词有价值得多。
作为上帝在尘世世界的代理人,自然女神创造万物,给予万物美、善的本质和独立自存能力,通过建立自然法则来保障人类自由选择的权力,让人类充分发挥爱的天性而使人性变得高贵,获得美好的爱情,人生的价值得到提升,最后,自然的法则还劝诫人类在痛苦的打击下恢复平静,继续自己高贵的人生。在这里,神性的自然指引着人类向美、善的方向发展,受到神庇佑的人类则积极进取,在现实世界中展示了美、善的真谛。
因此,在这首悼亡诗中,叙述者、古典故事里的国王夫妇、骑士和他的意中人都忍受着忧伤或死亡的伤害,但诗人却一再地挖掘着人性的高贵和美好、对尘世世界的讴歌和眷恋。虽然他在其后创作的《声誉之宫》中对此进行质疑,但到了《百鸟议会》时再次坚持了这种理想主义精神,尽管其中的现实主义色彩加重了很多,而此后的《特洛勒斯与克丽西德》和压轴之作《坎特伯雷故事》仍旧扩展和加深了这曲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