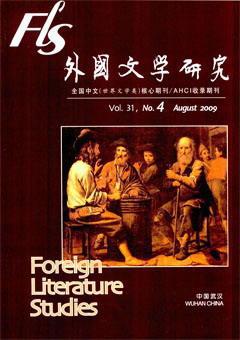阅读.误读.伦理阅读“俄狄浦斯情结”
王 卓
内容提要:美国黑人女性桂冠诗人丽塔·达夫的诗剧《农庄苍茫夜》是一个与西方经典《俄狄浦斯王》形成了清晰的互文性的后文本。然而,黑人和女性的双重边缘身份决定了达夫对西方经典的改写不会是一个简单的续写、引用或者模仿的过程,而是她基于“世界主义”和黑人女权主义诗学理念之上对“俄狄浦斯情结”的阅读、误读和伦理阅读的创造性阅读和“文本书写”的过程。此多重阅读和写作的文化容量是令人惊喜的:一方面,这个多维度阅读和写作过程是达夫对自己杂糅的文化身份和“世界主义”的诗学视角从焦虑到确立的心理暗战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达夫把诗剧《农庄苍茫夜》悄然地纳入了西方文学经典的框架之中的过程。
关键词:丽塔·达夫《农庄苍茫夜》“俄狄浦斯情结”阅读误读伦理阅读
丽塔·达夫(Rita Dove,1952-)是迄今为止美国唯一一位黑人女性桂冠诗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她的诗歌作品成为研究热点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了。然而,颇有些出乎意料的是,围绕着达夫还有一个比较集中的热点,那就是她的诗剧《农庄苍茫夜》(The Darker Faceof the Earth)。究其原因,恐怕以下几点是不容忽视的。其一,这个剧本是以韵文的形式出现的,是一部在当代美国文学中不多见的诗剧。因此,这部剧作也可以被认为是达夫诗歌创作的集大成之作,是她诗歌创作整体脉络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并非游离于她的诗歌创作之外;其二,这个剧本完成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却被达夫本人束之高阁长达20年之久,直到1994年才公开出版。这个思考、写作、改写、演出的过程为读者深入了解达夫创作思想的嬗变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素材;其三,这部诗剧触及了一个西方读者十分熟悉却又心存芥蒂的主题——乱伦。这部诗剧的整体框架挪用了古希腊经典悲剧《俄狄浦斯王》,弑父娶母的悲剧情节成为推动达夫诗剧的动力所在;其四,这部诗剧的时代和场景被达夫移植到了一个美国人十分敏感的历史空间和地理空间——南北战争前南卡罗莱纳州的种植园,而主人公也从体现着“人文主义精神”的古希腊神话英雄变成了美国南方种植园中还在为生存和自由而挣扎彷徨的黑人奴隶。
达夫的诗剧与《俄狄浦斯王》形成了一种“互文性”,前者是后者又一个产生“扩散性”影响的范例,是“俄狄浦斯情结”再生产的又一个范式。对于达夫来说,与西方正典之间的“互文性”情结要比人们想象中的黑人女作家的创作境况来得自然得多。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受过良好教育,并有多年欧洲生活和工作经历的达夫与西方经典的渊源由来已久。在1993年出版的《诗选》“序言”中,达夫讲述了她作为读者和作者的童年经历,其中特别提到了她从父亲的书架上找到莎士比亚戏剧和其他代表西方文学经典的作品的经历。达夫事实上却是在莎士比亚戏剧等西方经典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甚至可以说,长着白胡子的西方男作家是她事实上的“文学之父”。然而,种族和性别的特殊性决定了达夫作品与西方经典本质上的不同。作为非裔美国作家,她别无选择地身处“巨大的种族困境”(great racial dilem,ma)之间(Cruse 49)。达夫的诗歌作品含蓄地给出了答案,那就是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 Louis Gates)所说的“双色的遗产”(two-toned heritage):一方面,达夫“真实地”“在西方传统中改写文本”;另一方面,她又在“黑人方言的基础上”诉求着一种“黑人的不同”(Gates xxxi-xxiii)。达夫在这“双色遗产”之间小心翼翼地游走,并力求达到一种平衡。
以互文性为基础的文学文本之间,后文本是对前文本的一种阅读行为,离开了前文本,当今的文本可能就没有意义了。身处后现代创作语境中的达夫深谙此种文本之间的纠缠和交织的游戏。在《农庄苍茫夜》中,各色文本——从奴隶歌谣和劳动号子到众神膜拜的尤鲁巴符咒,从“救赎之书”到被岁月尘封的天文和占星术的厚重书卷——以及对它们的阅读和诠释都被达夫精心地编织进了她的诗剧之中,正如查理斯利(Theodora Carlisle)所认为的那样,“阅读的主题成为了[达夫]诗剧的中心主题”(Carlisle 138)。作为《俄狄浦斯王》的后文本,达夫在创作这部诗剧时充当了作者和读者、改写者和创作者的多重角色。因此,达夫的创作过程同时也是创造性阅读的过程和“文本写作”的过程。然而,黑人和女性的双重边缘身份决定了达夫对西方经典的改写不会是一个简单的续写、引用或者模仿的过程。那么,达夫在创造性阅读的过程中,在互文性文本的生产过程中,是如何以一个黑人女性的视角阅读并阐释古老的“俄狄浦斯情结”,并在《俄狄浦斯王》这个如羊皮纸文献一样的文本上完成了她的改写和拼贴的呢?笔者将从阅读行为的基点出发,检视达夫对《俄狄浦斯王》的阅读、误读和伦理阅读的多维度阅读行为和多层次阐释策略,从而对《农庄苍茫夜》独特的互文性生产过程和丰富的互文建构模式进行深入研究,并带动读者进行一次发挥自己的“能力模式”的阅读之旅。
一、阅读“俄狄浦斯情结”
尽管时间和地点置换到了南北战争前南卡罗莱纳州查理斯顿附近的种植园,在《农庄苍茫夜》中,《俄狄浦斯王》的基本情节脉络被达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与前文本中索福克勒斯将头绪繁杂的故事置于忒拜王宫前如出一辙,达夫也把主要的矛盾冲突放在了詹宁斯种植园中。俄狄浦斯身世之谜和他弑父娶母的情节成为推动《俄狄浦斯王》剧情发展的中心线索,而这一模式也是《农庄苍茫夜》情节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为了更加清晰地展示两部剧作在情节上的互文性特征,有必要把读者比较陌生的后文本的情节做一简要介绍。诗剧以主人公奥古斯塔斯(Augustus)的出生拉开序幕。詹宁斯种植园主路易斯的白人情妇阿麦丽亚生下了与黑人奴隶海克特的私生子一混血儿奥古斯塔斯。尽管路易斯本人以引诱黑人女奴为乐,但他却不能忍受自己的情人与黑人奴隶的私情,更无法接受他们的私生子。盛怒之下,路易斯对外人谎称孩子生下来就死去了,并试图杀死孩子,幸被医生制止。孩子被医生带出了詹宁斯种植园,后被纽卡斯特船长作为奴隶带在身边。20年后,奥古斯塔斯长大成人,他跟随自己的白人主人游走四方,见多识广,并接受了较好的教育。他被詹宁斯种植园购买,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阿麦丽亚,自己的亲生母亲产生了恋情。在奥古斯塔斯的生命中还有两位重要的女性,一位是黑人女奴菲比,她深深地爱着这个相貌英俊、识文断字的小伙子;另一位是黑人女奴丝赛拉,她如一位预言者一样,警告奥古斯塔斯灾难将至。当奥古斯塔斯参与到一场奴隶暴动时,为了防止泄密,他失手杀死了自己的亲生父亲海克特。最后,他误认为路易斯就是抛弃了自己的父亲,并杀死了他。至于奥古斯塔斯和阿麦丽亚的生死和结局,则取决于该剧不同的版本。
显然,达夫的诗剧从情节层面与《俄狄浦斯王》形成了“带有社会性容量”的互文性(BaIthes 39),忠实地实现了克里斯蒂娃的互文观。众所周知,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理论和“互文性”概念的提出运用了精神分析的方法和原理,可以说,由于弗洛伊德以及后来的拉
康的精神分析学,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才得以“超越结构主义的静态理论模式”,也才有了互文性的动态性概念提出的基础(王瑾41)。有趣的是,“俄狄浦斯情结”也是由弗洛伊德首先提出的,并使之成为文学的一个神秘的母题。而弗洛伊德似乎对《俄狄浦斯王》一剧更是情有独钟。具有高深文学造诣的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第五章《梦的材料和来源》中,不但对该剧剧情娓娓道来,更是对这一经典悲剧进行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全新解读。他认为,这部悲剧之所以具有经久的、令人震撼的悲剧性魅力的原因在于俄狄浦斯的命运完全有可能成为每一个观众和读者自己的命运。他还认为,在我们出生之前,弑父娶母的可怕神谕就已经降临在我们身上,换言之,我们所有的人,命中注定要把第一个性冲动指向母亲,而把第一个仇恨的目标指向父亲。《俄狄浦斯王》的震慑力就在于当我们揭示出俄狄浦斯的罪恶的同时,也看到了内在的自我,更为可怕的是,尽管加倍压抑,弑父娶母的欲望依然潜藏在我们的心灵深处。
与弗洛伊德把《俄狄浦斯王》解读成“本源之作”的理念和操作相仿,达夫的《农庄苍茫夜》也把《俄狄浦斯王》作为了一个互文性网络的心理生产的中心和原点(米勒,《解读叙事》2)。那么,达夫煞费苦心地与《俄狄浦斯王》构建起互文性关系的目的何在呢?
作为黑人女性桂冠诗人,达夫的诗歌创作生涯中最尴尬的问题就是她的“黑人性”一直受到评论家和读者的质疑。他们认为她“太白”了,没有遵循种族协议(racial protoc01)的模式,也很少在抗议主题和鲜明的非裔黑人事物的框架内创作。面对这样的指责,达夫不得不对自己以及作品的文化定位给予特别的关注,并力图形成比较系统的文化定位理念,因为这关乎到其作品在黑人社群中的接受问题,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达夫对“俄狄浦斯情结”的创造性阅读的首要目的是确立自己的文化定位。作为后黑人艺术运动的作家,达夫是典型的“文化混血儿”(cultural Mulatto)。正如特瑞·埃里斯所言,这些美国黑人作家“在多种族融合的文化中接受教育”(Ellis 234)。这些文化混血儿在美国的文化事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正是他们点燃了“新黑人美学”的火焰。他们不再需要“否认或是压抑”他们的“复杂”,有时甚至以“矛盾”的文化倾向来取悦白人或者黑人(Ellis 235)。特瑞·埃里斯对“文化混血儿”的界定仿佛是对达夫文学和文化定位的精确描述。达夫的经历为她提供了一个世界的视角,使她具有了成为“世界公民”的先天条件。这些是评论家派瑞拉(MalinPereira)得出达夫是“世界主义者”(cosmopolitan)的结论,并从她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视角研究其诗歌的基础。然而,有趣的是,“世界主义”是达夫诗歌创作的动力,也是她的焦虑所在。对达夫来说,在新黑人美学的前沿阵地创作的“世界主义”的非裔美国作家,文化融合成为一种必须被压制的原初(originary)分歧的时刻,因为在达夫开始文学创作的时代,公开承认自己的文化“杂糅”威胁了黑人民主主义的排他的“黑人性”心魔。
作为一个空泛的、形而上的概念,文化“杂糅”是不太容易找到一个具体的、对等的意象并在文学作品中得到适当的表现的。而达夫在她的诗剧中挑战的正是这个文化“杂糅”的概念,她把不可触摸的、无形的文化“杂糅”投射到具象的、生理上的不同种族之间的性行为。白人女性阿麦利亚与黑人奴隶海克特之间的私情以及他们的私生子、混血儿奥古斯塔斯成为达夫投射其文化身份的一个具象化的主体。在混血儿奥古斯塔斯的身上,时时闪过达夫本人的影子。达夫借阿麦丽亚之口,道出了奥古斯塔斯的文化身份和使命:“一位诗人/和一位反叛者”(65)。达夫在很多场合都暗示了她和主人公奥古斯塔斯之间身份的认同感:“在一个不同的世界中,阿麦丽亚(伊俄卡斯忒似的人物)本应该是独立生计的女人,而奥古斯塔斯(他对应着俄狄浦斯)是一名诗人”(qtd,in Pereira,“When the pear blossoms/cast their pale faces on/the darker face of the earth”198)。奥古斯塔斯是白人与黑人私情的产物,而他本人又与白人有了私情,这一切都从根本上决定了奥古斯塔斯文化身份具有典型的“杂糅性”。
奥古斯塔斯生理的“杂糅性”转化成为达夫对文化杂糅的艺术的焦虑。在该剧的第一版中,奥古斯塔斯的生理和文化杂糅性造成了他信仰和忠诚的矛盾,并直接导致了他命丧黄泉。他了解奴隶文化,也熟诸希腊和罗马的神祗;他亲身体尝了奴隶制的罪恶,也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启示;他热爱黑人文化传统,也欣赏弥尔顿等白人作家。在与白人主人纽卡斯特船长游历的岁运中,他经历并吸收了美国特有的多元文化因素。奥古斯塔斯曾经不无感慨地说,“没有你学不到的东西/如果你有那样的经历”(65)。除了奥古斯塔斯接受的双重教育,他与詹宁斯庄园的多重关系使得他的杂糅的文化处境变得更为复杂。他看重女奴菲比的情谊,却无心发展与她的恋情;他拒绝相信预言者丝赛拉对他发出的危险临近的警告;对他的生父海克特,他不但没有尽到保护和照顾的义务,反而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杀死了对方;他参与到谋划奴隶起义的事业当中,却由于他与阿麦丽亚的关系而半途而废。在该剧的第一版中,奥古斯塔斯与阿麦丽亚被当作叛徒处死。奥古斯塔斯作为黑白混血儿所产生的身份认同的矛盾和迷茫正是达夫作为文化“混血儿”与黑人族群的复杂关系以及矛盾的文学创作心理机制。在前面提到的例证中,奥古斯塔斯与黑人之间融合失败的终点恰恰是他与白人之间不断接近的起点。他拒绝与菲比发展恋情,因为他与阿麦丽亚早已暗渡陈仓;他不接受丝赛拉的巫毒教预言,因为在曾经的白人主人的熏陶下,他已经接受了西方经验主义的怀疑论;他没有将起义进行到底,因为他与阿麦丽亚的关系令他意马心猿。可以说,奥古斯塔斯的命运正是达夫对于定位于“世界性”的黑人作家命运之焦虑的外化。
二、误读“俄狄浦斯情结”
弗洛伊德认为,焦虑产生压抑,达夫的诗剧创作机缘巧合地印证了这一观点。女诗人对在后现代语境中,从“世界主义”的视角写作的文化定位的焦虑集中表现为对前文本《俄狄浦斯王》的反讽性的误读策略。“诗学误读理论”是布鲁姆提出的诗学影响理论,是通过对互文性理论的心理阐释而提出的诗学理论,从本质上讲,它是一种视角独特的互文性理论。有趣的是,与克里斯蒂娃如出一辙,布鲁姆的误读理论也是从弗洛伊德的“家庭罗曼史”模式出发来阐释诗歌的影响与焦虑感的内在联系的(徐文博4)。前文本与后文本之间互动性的关联网络事实上正是在“俄狄浦斯情结”的作用下构建的。布鲁姆认为,“诗的影响一当它涉及两位强者诗人、两位真正的诗人时一总是以对前一位诗人的误读而进行的。这种误读是一种创造性的校正,实际上必然是一种误译。一部成果斐然的‘诗的影响的历史一亦即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诗歌的主要传统一乃是一部焦虑和自我拯救的漫画的历史,是歪曲
和误解的历史,是反常和随心所欲的修正的历史,而没有所有这一切,现代诗歌本身是根本不可能生存的”(布鲁姆31)。布鲁姆把诗人之间的关系作为接近于弗洛伊德的“家族罗曼史”的档案加以审视,将诗人之间的关系看作“现代修正派历史中的一个个章节来加以检视”(8)。更为有趣的是,与弗洛伊德如出一辙,布鲁姆本人对《俄狄浦斯王》也情有独钟。在《影响的焦虑》一书的“绪论”中,布鲁姆阐释了俄狄浦斯对他写作的影响:
贯穿于本书的是这样一种隐含的痛苦情绪:光辉灿烂的浪漫主义也许正是一场波澜壮阔而虚无缥缈的悲剧。这场悲剧不是普罗米修斯式的悲剧,而是双目失明的俄狄浦斯的一场自我窒息的悲壮事业一俄狄浦斯不知道斯芬克司正是他的缪斯。
双目失明的俄狄浦斯在走向神谕指明的神性境界。强者诗人们跟随俄狄浦斯的方式则是把他们对前驱的盲目性转化成应用在他们自己作品中的“修正比”……(11)
可见,布鲁姆的诗学误读理论与“俄狄浦斯情结”也有着令人意想不到的联系。那么,作为在后现代语境中创作的非裔美国女诗人,达夫又是如何在焦虑的驱动下“修正”她的前驱诗人的呢?
达夫在“世界主义”文化定位下,诉求的是“双色遗产”,体现在文本创作之中,就是一个“错位的黑色的对等物”(black equivalent of metalepsis)(Gates 87),一个比喻性的言语替代另一个修辞性的话语过程,是一个通过对原文本的重新安排对一个“已经公认的比喻”的“修正”(Gates 145)。特殊的话语表述方式使得非裔美国作家成为说此而言彼的“喻指”高手,也是布鲁姆所言的有意“误读”的高手。达夫对《俄狄浦斯王》的阅读心理机制是复杂的,犹如一个斗争激烈的“心理战场”。作为黑人和女人,她对索福克勒斯这样的男性白人作家的心理反应要比布鲁姆所能想象的心理运作机制复杂得多。一方面,有布鲁姆所言的对前驱诗人的超越的焦虑,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是,对她本人作品的文化定位的焦虑。在这“双重焦虑”的作用下,达夫的“修正”策略也比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中所阐释的若干迟来的诗人所运用的策略要微妙,似乎更加处心积虑,也似乎更有颠覆性。
在古希腊悲剧中,悲剧事件的因果关系一直是戏剧研究者十分关注的问题。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对悲剧的界定以及对戏剧情节“突转”(peripeteia)和“发现”(anagnorisis)的论述都表明古希腊悲剧探究的根本问题是命运根源的问题。在古希腊悲剧中,通常都有一种强大的、不可思议的力量将人推向失败和毁灭。这种被称为“命运”的不可知力事实上有两种不尽相同的理解。第一种是来源于神的意旨,人的命运被神操纵着,而即使是奥林匹斯山上的神也不得不屈从于这种力量;第二种也是“命运”最原始的含义,指的是“落到每个人头上的运气和份额”(Liddell and Scott 1141)。第一种“命运”是大写的,神谕的;第二种是小写的,是人生的机缘巧合。俄狄浦斯的命运正是在这两种不同的“命运”的摆布中呈现出不可逆转的悲剧色彩的。特瑞西阿斯带来的是阿波罗的神谕,是“上天之事”;而俄狄浦斯在流浪的途中,巧遇并杀死素不相识的父亲拉伊俄斯,恰巧在斯芬克司的谜语使忒拜王国陷入瘟疫的危急时刻到达忒拜则是命运的机缘巧合。最终,俄狄浦斯发现,他的第二种命运是在第一种命运的掌控之下的。
与其它版本的俄狄浦斯的故事相比,“索福克勒斯进一步强化了神谕的作用”(耿幼壮83)。神谕是《俄狄浦斯王》的中心线索,更是俄狄浦斯悲剧命运的毒咒。作为悲剧英雄,俄狄浦斯个人的命运与公众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正如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的哲性思考:“在索福克勒斯看来,不幸的俄狄浦斯这个希腊舞台上最悲惨的人物是一位高尚的人。……任何法律,任何自然秩序,甚至整个道德世界,都会由于他的行为而毁灭,正是这个行为产生了一个更高的神秘影响区,这些影响力在被摧毁的旧世界的废墟上建立起一个新世界”(58)。俄狄浦斯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忒拜国解除了危机,救民众于水火之中;而他个人的罪行也同时为忒拜国的民众带来了灾难。
在达夫的《农庄苍茫夜》中,古希腊悲剧发生的因果关系以及个人与公众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究其原因,达夫对《俄狄浦斯王》中悲剧的因果关系以及个人和公众的关系进行了“偏移式”的阅读。达夫的这种误读正是布鲁姆所定义的“克里纳门”(Clinamen)。这一术语指的是原子的“偏移”,以便宇宙可能起一种变化。一个诗人“偏移”他的前驱,即通过偏移式阅读前驱的诗篇,以引起相对于这首诗的“克里纳门”。这种矫正似乎在说:前驱的诗方向端正不偏不倚地到达了某一点,但到了这一点之后本应“偏移”,且应沿着新诗运行的方向偏移(布鲁姆14)。达夫把俄狄浦斯的双重悲剧的动力移植到现代的、奴隶制背景下的特定框架之中,并在此基础上对前驱文本实行了“偏移式”的阅读。在诗剧的第一场中,菲比在嬉笑中对整个事件进行了暗示,并哼唱出主人公命运的一个版本:“踩在一枚大头钉上,钉子弯了,/那就是故事发展的方式”(13)。这里的“命运”显然是在第二个层面上,是一种机缘巧合。这个善良、乐观、不谙世事的小女奴对命运的岌岌可危并没有当回事。接着巫毒教女人丝塞拉预言了奥古斯塔斯的降生将带来一个可怕的诅咒:“我看到/厄运来临。厄运/骑着高头大马越过山岭来了,/马儿打着响鼻当他们奔腾/越过奴隶窝棚和有柱石的楼宇/马儿嘶鸣当他们奔跑。/一切都在他们的路上。/像一张薄薄的网/诅咒降临到大堤上”(36)。
与俄狄浦斯的降生一样,这个混血儿的出现也打破了曾经的和谐并破坏了旧有的秩序。与《俄狄浦斯王》惊人相似,这个命运的“薄薄的网”将把剧中的人物一网打尽。然而,从达夫诗剧的剧情发展来看,真正在这个悲剧中起作用的却是另外一种更为可怕的力量。对于在苦难中挣扎的奴隶来说,命运似乎打了一个死结:“没有出路,只能继续……/除了眼睁睁看着没有办法”(61)。奴隶们无路可逃的绝望感来自奴隶制而并非神谕。在两部剧作中,两种不同的命运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逆转。在《俄狄浦斯王》中,弑父娶母是俄狄浦斯神定的命运,并将带来他本人的悲剧和伊俄卡斯忒的毁灭;而在达夫的诗剧中,杀父和乱伦却只是“奴隶制的副产品”(carlisle 141)。奥古斯塔斯失去了认识到自己弑父娶母罪恶的能力,因为他被剥夺了认识自己父母和自己身世真相的权利。从这个角度来说,奴隶制才是降临到美国这块土地上的毒咒。
两种命运关系的变化带来了个人和公共关系的变化。在《俄狄浦斯王》中,个人的罪恶带来了公共的灾难;而在《农庄苍茫夜》中,这个因果关系被颠覆了:奴隶制的罪恶成为个人厄运的根源,而所有的命运的机缘巧合都是建立在这个巨大的公共的罪恶之上的。更为可怕的是,作为白人妇女和黑人男子。的私生子,奥古斯塔斯的身世触动的是美国南方奴隶制社会最敏感的神经。事实上,在奴隶制的社会机制下,白人奴隶主与黑人女奴生下孩子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也是社会一种心照不宣的秘密。通常的做法是,这些孩子将在种植园中沦
为奴隶或是被卖掉。在南北战争前的南方种植园中,这是社会禁忌的话题,却是社会可以接受的做法。与此相反,自人妇女和黑人男子之间的性关系,却是不能被社会接受的。“在南北战争之前的南方,如果哪个已婚女子生出了娃娃,而据判断娃娃的父亲是个黑人的话,这个女子十有八九是会受盘查询问的。即便白人女子只是被怀疑与黑人男子有奸情,并没有怀孕生子,也会成为当地的热门话题”(赖斯183)。正是在这一心理暗示的作用下,奥古斯塔斯才一直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的父亲是白人,而母亲是黑人;才会在一次又一次接近身世之谜的时刻,走向了真相的反面,错误地认为自己的父亲是种植园主路易斯。这是奥古斯塔斯对自己身世的误读,而这一误读使他离自己的身世真相越来越远,并最终走向毁灭。奥古斯塔斯对身世的误读从他对阿麦利亚杜撰的关于身世的故事就清晰可见:“在一个温柔的春夜/盛开的梨花/把白色的花影/投射到幽暗的地面,/马萨从摇椅里站起/自言自语,‘我还要/再弄一个眼睛闪亮的黑色小孩。/然后他伸伸懒腰,走向/我母亲的小屋”(92)。奥古斯塔斯用建立在社会主流思维基础上的想象为自己的混血儿身份构建了一个他本人和他人都能够接受的身世版本。这是剧中人物奥古斯塔斯对自己身世和经历的误读,也是作者达夫对前驱文本中的俄狄浦斯命运的“偏移式”阅读。在达夫的诗剧中,戏剧的焦点从“希腊舞台上最悲惨”的“高尚的人”俄狄浦斯发生了偏移。事实上,在所有的古希腊悲剧中,主人公都是出身高贵,具有个人英雄主义气质的人。但在达夫的诗剧中,这些气质已经从主人公奥古斯塔斯身上消失殆尽了。他在每一个方面几乎都是俄狄浦斯的反面:他出身卑贱;没有勇气追寻自己的身世的真相;为了与阿麦利亚的私情而对崇高的奴隶解放事业意马心猿等。可见:在达夫的诗剧中,主人公已经难以担负起解民救困的伟大事业。相反,达夫诗剧中发出崇高的声音的是奴隶群体。他们既作为种族和阶级的整体,也作为鲜活的、独立的个体而存在。这个群体的存在和群体的声音成为达夫戏剧的核心力量,表明了黑人群体的精神维度远远超越了悲剧英雄本身的个人力量,并将成为黑人种族获得解放的最终希望。
三、伦理阅读“俄狄浦斯情结”
达夫的阅读是创造的、生产性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女权主义和后现代书写的背景下对这部西方经典的重新阅读。同时,达夫在重读的基础上进行了“重新写作”,从而充当了《俄狄浦斯王》这个经典文本的“解释者”和“实践者”。达夫的重读和重写是在特定状态下的阅读行为,是一种批评性阅读;而《俄狄浦斯王》则在达夫的重读和重写中介人到了当下的“社会的、机制的、政治的领域中”(Miller,The Ethics of Reading 5)。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达夫和她的诗剧实践了米勒在言语行为理论文学观的基础上所阐释的“伦理”阅读的精神。有趣的是,与亚里士多德和弗洛伊德惊人地相似,米勒对《俄狄浦斯王》也投去了深情的一瞥,并把其专著《解读叙事》的第一章奉献给了这部经典。
言语行为理论文学观是米勒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并坚持的重要文学观念,与他五六十年代提出的现象学文学观、70年代提出的解构主义文学观共同构成了米勒文学观体系。米勒认为,“写作是用词语来做事情的,写作者必须或者也许得对该事情负责”(Miller,The Ethics of Reading 101)。换言之,文学作为一种话语形式,其功能不是被动地记叙事物的,而是用来主动建构事物的,因此是一种给事物命名的施为行为。具体到阅读行为,米勒认为,“人类的一切语言言语都既是在言说主体的意向意图的引导下进行的,又是在语言言语本身的运作规则的基础上完成的,既有受意识控制的理性的一面,又有不受意识控制的非理性的一面,是行和言、理性和非理性的集合体,所以一个真正的言语解释者既应关注言语的行的层面,更应关注语言的层面,既应重复它,准确地把握它的本义,更应重构它,开发它的非理性的新异的方面,应将再现和再造结合起来”(肖锦龙99)。可见,米勒的文学阐释是融重复和重构、记述和施为为一体的新型文学批评方法,米勒本人将其命名为“阅读的伦理学”(Miller,The Ethics of Reading 4)。米勒认为在阅读行为中,有伦理学趋向两个方向的时刻:其一是对某种东西的回应,“它承受它,回应它,尊重它”,换言之,“我必须履行责任”;其二是在阅读中指向了行为,具体到文本阅读,就是在某个评论家的评论中介入到当下的社会和生活(Miller,The Ethics of Reading 4-5)。作为新型的阅读的伦理学批评方法,伦理阅读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要求解释者完全投入到文学文本之中,“尊重”文本,忠实于文本。做文本要求做的事,而不是自己喜欢做的事,以重复文本为起点;二是要求解释者在重温文本本身的能指和所指内容的同时应致力于开发其中的新异(odd)的或者“非道德”的东西,发明新的事物,以重构和再造文本为目标(肖锦龙100)。
从阅读伦理学的视角考察达夫的写作,我们不难发现达夫的阅读的伦理时刻发生在两个不同的时间,针对的是两个不同的文本:第一个伦理阅读是对《俄狄浦斯王》的阅读;第二个伦理阅读是对她本人1994年版《农庄苍茫夜》的阅读。细读达夫的《农庄苍茫夜》,我们惊喜地发现,达夫的诗剧创作正是她对《俄狄浦斯王》的“行为阅读”的结果。一方面,达夫小心翼翼地追踪着索福克勒斯的文本创作意图,努力发掘“俄狄浦斯情结”的文本本义;另一方面又成功地走出了原文本,打造出了一个带有新境界的文本,从而把“记述性”和“施为性”融为一体。“记述性”使得达夫诗剧成功地保留了《俄狄浦斯王》的情节框架和“俄狄浦斯情结”的基本内涵,使得读者和观众轻而易举地从达夫的诗剧中嗅出前驱文本的味道;“施为性”使达夫的讲述带有一种明确的责任感,是作为黑人女作家对种族和性别身份的责任感。这正如米勒所言:“讲述故事本身就是一种讲述者必须为他所讲述的东西负责的伦理行为,就像读者、教师或批评家必须为他们借阅读、讲述和写作为故事所带来的生命负责一样。它们会引发政治的、历史的和社会的后果”(Miller,Versions of Pygmalion vii)。
作为女性作家,达夫对《俄狄浦斯王》的伦理阅读的重构主要体现在对其文本中消失的女性话语的巧妙恢复。《俄狄浦斯王》创作于希腊奴隶制社会的鼎盛时期,父权家长制社会形态已经形成。在这一时期,女性与奴隶一样,不能享受当时的奴隶制民主制度,也不被社会平等地接纳。在《俄狄浦斯王》中,神谕的命运来自阿波罗,是与“父权法则”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神的预言非常自然地推动着剧情的发展,而且还在文本中勾勒出一个意识形态范畴上的‘父亲形象”(顾明生105)。在“父权法则”的作用下,“在《俄狄浦斯王》中,体现着古希腊文学神话特点的‘神、‘人、‘妖三个女性形象最后都归于‘沉寂”(顾明生106-107)。在达夫的诗剧中,超自然的力量和预言的诠释者不再是代表着父权的阿波罗的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