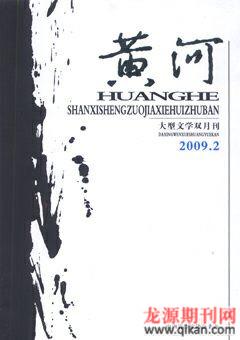歌行体、政治诗与底层关注
编者按:寓真的歌行体诗,成为新春文友聚会的一个议论话题。虽只是沙龙式对话,广涉泛议,即兴谈吐,亦不乏卓见。经本刊整理,择其要点刊发如下。
1、 旧体诗挑战新文学史的学科变革
张发(《黄河》杂志主编)寓真在高级法院工作多年,“左手拿刀杀人,右手拿笔写诗”。他与我们文学界的人打交道,是以一个诗人的面目出现的。他一面当法官,一面又在几十年中不断写诗,出了五六本诗集:《绝句二百首》、《律诗小集》、《寓真词选》、《寓真新诗》,现在我们又看到了这本《寓真歌行集》。还要值得一提的是,寓真对聂绀弩旧体诗的深刻的研究,他的这一新作,发表在最近一期的《中国作家》杂志,已经在学界引起关注,认为这是在牛年春节献给大家沉甸甸的、分量很重的一部作品。他的辛勤耕耘的成果,确实令人高兴,值得深入研究。
卢瑜(原山西省委宣传部部务委员)记得在2005年举行过一次寓真诗词研讨会,那一次的规模较大,来了不少全国和省内的名家,大家对寓真的诗歌作了充分的肯定。现在是2009年新春伊始,整个文化产业出现了好的发展势头,这将极大地有利于文学创作。文化产业的核心是创意,创意的真正源头是在文学艺术。创意就是灵感,比如说写一首诗也好,一篇散文也好,创作一部小说也好,都要有灵感,要有一种内心的激发。文化产业的创意,不仅是出一部好作品的问题,我们希望出现一个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整个文化的繁荣。寓真和我私下多次聊过,他对文化事业极有兴趣。我觉得寓真的诗,根子是文化底蕴。他的诗歌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仅是在山西,而且在全国都有影响,这是为树立我们山西的文化形象立了大功,同时对于诗歌创作的探索,对于旧体诗的繁荣也有着重要意义,值得引起关注。
谢泳(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我说两点意见:一,最近看寓真的东西较多,尤其是认真看了他写聂绀弩那本书稿(《聂绀弩刑事档案》)。因为我在厦门大学,教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料概述。这两门课的主要研究对象,包括聂绀弩的诗,也包括聂绀弩生平际遇的相关问题。看了寓真的书稿以后,感觉在我们目前研究聂绀弩的这个领域里面,这本书从史料的角度和评断的角度来讲,都代表了这个研究领域里的最高水平。这个专业的一种主要学术刊物叫《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它的栏目里面有一个书评专刊,曾经约我写一篇书评文章,我一直没有合适的评论对象,看了寓真这本书稿我就说一定写一篇专业性的书评,从文学史料如何判断、从史料的发现对我们中国现代文学有什么重要意义,从这个角度来写一篇专业的书评。
二,寓真谈到他的一篇论文的新观点,从我们教书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他的观点对我们这个学科的发展也非常具有启发意义。寓真的这个观点,针对我们现代文学史这个学科有一个严厉的批评。他认为从1917年以后讲现代文学史,忽略了在这个跨度里面一个必要的文学形式,就是旧体诗这个内容。这里有一个矛盾,就是我们知道中国新文学史的核心元素是用白话文写的,但这个时代里面,就是从1917年开始的这个文学实践当中,确实有大量的旧体诗歌,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和敏感程度,包括它的丰富性方面,在相当尖锐的程度上是超过了我们很多新文学的。所以以后我们这个学科里面是不是要把这个时代的旧体诗写到中国现代文学史里面,肯定是一个有学术吸引力的话题。比如对一个历史事件的反映,所有的当代文学作品里没有什么直接的、公开的表达,但是却有大量的反映现实比较有深度、而且很有艺术性的东西,正是出现在这个时代中国的旧体诗中。寓真的这本诗集,体现了他对社会的关怀,在学者中也好,诗人中也好,他是对当代中国的现实体现出非常关怀的一个写作者。有现实关怀的作家,必然有对政治的关心,关心政治甚至是所有作家或者是从事文学工作的第一个元素。如果说作家、学者或者诗人完全是为艺术而艺术,恐怕也不太现实。我也特别赞赏寓真讲自己的诗是政治诗,诗的情怀肯定是从当代的生活中产生出来的。中国文学史整个这门学科的建立,实际上是有比较强烈的意识形态的色彩。从王瑶和李何林他们开始的时候,现代文学史的学科基础实际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1949年到目前为止基本上是按王瑶的传统来写,基本上是一些议论性的评述,对一些作家、作品、文学社团、文学流派的作品大部分不从史料入手,而基本上是從一种观念入手。实际上中国新文学史的起源,本来是两个传统,除了王瑶这个传统以外,还有另外一个传统,即是史料的传统。在中国文学传统中由史料形成了掌故笔记之学,而1949年以后基本上没有了掌故和笔记的传统,却有了空发议论的传统。这个学科的地位到今天为止就越来越动摇,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我们也在商量,这门课在一两年之内肯定会酝酿一个比较大的变革,就是有可能使王瑶以来的传统发生一个重要的转折。寓真主张把旧体诗在这个时代里和文学的关系解释清楚,可能是我们这个学科变革的一个主要方向。
2、 传统诗歌的批判精神一以贯之
韩石山(原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家)我看了寓真的歌行体诗,原准备写点东西,后来一想,你这个人太认真,而且太“势利”,一看了点什么呢,总想化为自己的文字,而不愿意把自己的感觉直白地告诉大家,所以没写。但是我在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寓真这个人作为一个职务较高的官员,而能够一心地“好这手”,从我们行内的话来说就是“好这手”,这是很不容易的。寓真自己谈到他的诗究竟是政治诗还是什么诗,似有怀疑。我认为他实际上是不怀疑的,他很自信。如果不是自信他不会这样一本一本地出书,如果不是自信他不会说出那样谦和的话。一个人如果真的写得都是些“老干体”的话,他是绝对不会说我那个是不是诗,他一定要强调我这就是诗。寓真实际上是很自信的。
第一,他懂韵律,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这个人很狂傲,但是我绝不写诗,为什么呢?因为不懂韵律。不懂韵律写诗,就等于在那里丢丑、献丑。但是我可以评诗,我可以知道哪个是好诗,哪个是坏诗,凭我的感觉可以知道。懂得韵律的诗人,我们现在社会上不管年老的年小的都已经不多了,都是属于“稀奇的品种”。我认为只要写诗,不管写古体诗还是新体诗,最好还是应该懂得韵律。这个韵律是从大量的诗歌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有了韵律,自然就是音韵铿锵。当然,旧体诗更应该懂得韵律,如果不懂韵律的话,连“老干体”都不配写。这是他吃饭的行当,能够写诗首先就是因为他是懂得韵律的。
第二,似乎被忽略了的、作者也似回避了谈的一个问题,就是寓真的诗中有着深沉的感情。我是善于考证的人,我以前给寓真写过一篇诗评,那是评他的律诗,但不愿写成一个大而化之的、只说诗多么好的那么一种文章,所以我把他的律诗细细地看了不止一遍,就发现里边有一个女性的角色,几乎从上大学时到后来二、三十年里一直或隐或现地闪耀在他的诗歌里。于是我写的那篇文章,就叫《律诗中牵出的情感线索》,发在《文学自由谈》。我认为正是因为有这深沉的感情的线索,使他的诗的品质提高了一步。如果说你的诗总是写政治,不管是批判的还是歌颂的,即便全是为国为民的,总让人觉得单调,总让人觉着作为一个诗人少了一点什么。把个人的情感加进来,和对政治的关怀,对时事的关怀联系在一起,这就成了寓真的诗的最主要的优点。
第三,寓真对时代的深沉的关怀,体现在他的诗中,有一种沉郁、雄浑之气。寓真自己说他的诗是政治诗,有政治感情,就像张发说的他“一手拿的是刀,一手拿的是笔”,他的“刀”下去之时,他的笔也会写出他的感受。他的政治诗,正如他自己所言,不是主流派的。我认为他的诗不但不是主流派,更重要的是他的诗里确有一种针砭时弊的东西。他的针砭时弊,分作两个方面,一是写他切身感受的,我认为这是更为重要的一面,二是批判社会的那一面。最难得的是他那样一种身份,又能够把自己心中的苦闷、怨愤用诗的形式表达出来。如他有一首《琐记》:“旅梦孤帆又险涡,书生弱笔对干戈。亲丧十载谤无止,官擢千员怨愈多。工作再忙都扯淡,文章虽好不登科。幸亏天赐半聋耳,莫怪他人敲鼓锣。”三、四两句写出了内心的郁愤,五、六句俗语入诗,这就有点聂绀弩体了,后两句是很无奈的表达。这是一首出于亲身政治体验的诗。他的另一种政治诗,如《槐夏行》,是《山西文学》那年诗歌大赛时拿出来的,发表时改了诗名,我看了以后对诗人非常敬重。记得诗中有句“千秋长安夜,十万貔貅兵”,堪称名句。像寓真这样雅好此道,在领导干部层里是少有的,他是真的好这一手。因此,他的人生是有价值的。既做了行政工作,实现了一个男子的人生梦想,同时又顺便成为一个让人敬重的诗人。有的人一辈子做一件事都做不好,他可以做两件事,可以说是两世人生。
赵瑜(山西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早在几年前,我和寓真聊谈过现代写旧体诗的意义。特别是在某种特殊历史时段,如当年的天安门悼念周总理那次运动,就是旧体诗歌最为显赫的一次。那次运动对于文革的结束,对于新的历史一页的揭开,作用应该说是极其重大的,其中几乎全部是古典味的诗歌在发挥作用。我和寓真议及此事,都感到了古典诗词这个传统链条的承接问题,感到了要把被割断的东西再续接传延下去的重要意义。韩石山刚才谈到寓真在历经政治生涯的同时,“顺便”成为一个好的诗人,似乎也不妨这样说。但从我对寓真的了解,还真不是“顺便”为之,他在长治二中上学的时候,就是该校诗社的首创者。在他的中学时代,这个太行山的青年人就是激扬文字,充满理想的。只不过那时的理想也不免被我们的政治形势所捉弄,寓真在太行山的那个中学校里举办诗社、写诗,险些没有被打成小右派之类。后来他抱着忧国忧民之心上了中国政法大学,毕业时又遇上文化大革命,和当年所有的青年一样,一时间受了这种重造河山理想的激发,直白地说就是受了蒙骗,也曾随着那样一个洪流到全国串连、参加造反,其間在河北保定煽风点火,写了一篇文字叫《保定向何处去》,一夜之间贴满保定的大街小巷。但是,很快就被残酷的现实破灭了激情和理想。在战火连天的时候,寓真要回老家,一到太行山上,只见遍地血与火。从长治回他老家武乡,交通断绝,没有任何交通工具,不得不步行进山,一路上到处是哨卡、碉堡、公告,这个文化大革命究竟在干什么?他被分配到海南岛时,写有一篇散文,写了离开北京、一路南下的途中感怀,那还在文革的中期,他就怀疑我们这是干什么,文笔非常凄凉。可以说对当时的政治是非常失望的,甚至也是抱着绝望的心情去往海南岛的。我看过寓真这篇散文,联系他后来写的诗词,感到他成为一个诗人是有长久积淀的东西,真还不是“顺便”。他从学校以来形成的思想和情感基础,是他后来一直保持的那样一种东西。他从海南岛回到山西时,是先到的长治,和家乡、民间朋友、社会现实联系都很紧密,加上后来干了政法本行,始终与社会生活、与社会进步密切相关,使他无法忘怀忧患和国计民生。他的《国难备忘录》这首诗,写的是日本侵略时期的民族苦难,怀着沉痛写了大同的万人尸坑等等。我们这个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他的诗中一直写到汶川地震,从这个脉络来看,他写诗,写忧患的诗,不在意外,不是偶然。对于聂绀弩的作品,他很长时间就在琢磨,最终形成他发表在《中国作家》的这本书,在北京引起反响。中国诗人的一种传统的精神一以贯之,使寓真从青少年时代一直走到今天。所以说不是偶然现象,今后他还会有更好的发挥。
3、关乎政治是歌行体诗的重要传统
傅书华(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教授)今天既是随意叙谈,我想谈三个话题:一,谈谈官员诗歌。这在中国有很大的传统。我比较关注的问题是,现在的官员写的诗和古代官员写的诗区别在什么地方。中国古代的念书人最大的愿望就是“学而优则仕”,念书人和官员没有区别。从诗歌来说,中国的文学起源真正是从诗歌起源进入到小说、话本阶段,其实和文人就有点脱节了,所以诗歌、官员、念书人在古代是三位一体的。现代官员就有些差别了。尤其到了新时期,80年代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自觉意识比较强了,知识分子和官员是两个系统了,做官的知识分子和不做官的知识分子价值观不太一样。说到寓真,虽然是以前的大学毕业,但他在不断地看书,他的知识结构、价值结构其实是和现代教育的现代化程度是同步发展的。他不是传统的念书人,他是以现代知识分子的那样的价值结构和心态结构,进入到官员系统当中的,和古代的官员并不一样。这个不一致导致现代官员的诗歌和古代官员的诗歌是有差异性的。当然,现代官员的诗歌和纯粹诗人写的诗也不一样,由于官员所处的位置,他对社会、人生接触的广阔性和复杂性,有切身体会,这个体会是不当官的人所没有的。纯粹的诗人写诗可以不顾及这些。其实说到底,是人的生命情感的自由性、自由程度,和官员考虑到现实的操作性、约束性,二者之间一种张力关系。由于官员精神生态和对社会的辐射性,允许他在什么程度上可以自由地体现,都值得研究。
二,寓真说到政治诗,还有“诗到语言止”的问题。诗歌界是不是有些误区?就我对西方理论的理解,“诗到语言止”是20世纪50年代之后,西方整个哲学、文学全部出现一个语言学转向。西方原来讲的是主客两分的,语言有客观的、纯粹的一个客体,而我们的认识是对客体的一个准确揭示。到了20世纪50年代之后,语言学全部转向之后的哲学,认为没有客体本身,只是运用语言的人的描述,客体是不存在的。所以“诗到语言止”,语言本身就是存在的一切。其实,“诗到语言止”并不排斥我们对国计民生、对现实的揭示,只是我们所揭示的不是对象本身,而是揭示者的一种态度。语言是存在的家园,首先是存在。如果我们把存在都丢掉,语言就成了一个空的东西,但这不能得出我们不再关注社会现象的结论。
三,关于古典诗歌。古典诗歌在中国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像鲁迅、郁达夫这些作古典诗歌做得非常了不得,但是他们自己并不大看重自己的古典诗,他们看重的是自己新文学的部分。现在传统的古典诗词引起了大家的重新重视,觉得古典诗词有很重要的学术含量和精神含量。
高峰(诗人、文艺评论家)看到寓真的歌行体诗,首先感到惊讶。当代诗人的诗歌作品集很多,但还没有见到过这样的歌行体诗集。曾经看过一本《唐代歌行论》的书中说,中国是诗的国度,唐诗达到了顶峰,顶峰的标志之一是律诗,称为近体诗。其二就是由乐府诗脱胎出来的歌行体,到了唐代也达到了顶峰。从歌行体的特点来看,可以说大都是政治诗,甚至一些歌行体诗是非政治家写不行。寓真在写了那么多律诗的同时,为什么又一边写了这么多歌行体诗呢?我认为这是题材本身的要求,有许多用歌行体表达的内容,律诗是没法表达的。比如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清代吴梅村的《圆圆曲》,这些诗中所抒写的东西,用律诗绝对没法表达。歌行体以七言为主,长的一句可以到十一个字,可以转韵,还可由平韵转到仄韵,当律诗表达不了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的时候,用歌行体更能达到叙事流畅、抒情转折跌宕的表达效果。我的感觉是歌行体更难写,有了激情时写首律诗,格律和押韵可以反复推敲,反复打磨它,而写歌行体需要很足的底气。是不是中国的传统文化都有相似的地方,作诗也和写字一样?有些人好像很能写行书、草书,一写楷书反而不会了,而真正的书法家不是这样,如果没有楷书的基础,就没有办法写行草。寓真能写出一本歌行体诗,必是有深厚的传统文学的基础,有基本功的训练,有长期的积淀,否则是不行的。他的歌行体诗的韵律、节奏,读起来感觉非常好,传统的东西吸收很多。比如《锦梭歌》的“小引”:“天上银河浅浅情,河上织女灿灿明”,有古乐府的韵味。这篇长诗从风平浪静,一步步写到“祸起”、“玉碎”,到“尾声”很自然很熟练地用了歌行体结构的句式,诗人情感到了激越的时候,“人世从来多忧患/对案不食、拔剑击柱每长叹/淑女可怜、不禁长思念/西风残照、伤心山河暗”,这样的诗句喷发而来,非常熟练地写出这种歌行体句式。这种古风的韵味,既是有意为之,又是由于平常的积淀无意而发。再如《春晚琐记》,诗的情调和笔法非常独特:“春雪晶晶不久留,化作春水贵如油。田园滋润醉似酒,老农欢喜绽眉头/偏教都市犯忧愁,泥水污了锦衣裘。寒袭娇容脂粉损,首长夫人骂不休/我有一言对天告:雨雪只向农村浇。切莫淋湿官家道,高跟皮鞋易摔跤。”诗句叙述得似轻松、流畅,却把诗人对达官贵人的藐视、不屑和无奈的调侃,都写进去了,表现了诗人的平民情怀。这种形式既不是民歌,又没有陈腐气,不刻板,不多用典,文字简洁,没有学究气。可能是写旧体诗积淀到一定程度,自觉不自觉地要走到歌行体这条路上来。
还有一个问题,现在人写律诗往往太空洞,因为现代人的生活情境不同于古人,比如过去的“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这些诗现在写不出来了,通讯便捷了,怀人这种诗不可能写出唐代那种感觉来。但旧体诗这个传统是割不断的,它可以找到新的表达内容,每到一个历史的关键时刻,不在乎有人提倡不提倡它,诗词的代表作品就出来了,诗词家就出来了。像寓真这样的诗人,不管是歌行体,还是律诗,都写得这样好,艺术上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我尤其觉得他的歌行体,在内容上比他的律诗更为充实。我认为歌行体诗本来就是政治诗。如寓真自己所说,即使是陶渊明的诗也脱离不了政治,官员写诗怎么脱也脱不了政治。有平民思想的官员,能写出很好的同情平民的诗来。不管叫不叫政治诗,只要有真情,又有非常适合表达自己思想的艺术形式,就是好诗。
4、歌行体是中国古典诗歌中的自由诗
李骏虎(山西省作家协会理论研究室主任、作家)寓真的作品其实我是比较熟悉的,曾为他的散文集写过一篇名为《观瀑者的身姿》的评论。他的诗集《四季人生-寓真抒情诗选》首发和研讨时,评论通稿也是我写的。看过他好多东西,印象比较深。我在山西日报《黄河》副刊做了六年的文学编辑,最头疼的是编旧体诗,写旧体诗的老干部多、在职的官员多,叫“老干体”,有的很流俗,有的很拗口,不知该怎么下手编辑。后来读了寓真的诗集,当时很惊奇,还真正有懂格律的,真正有把旧体诗写得这么好的,我就非常感兴趣。看他的散文集时,有很多共鸣,他的诗和散文都有传统风韵,很能见一个人的境界,所以就写了一篇评论。当时我对旧体诗的感觉,已经以为它是一种边缘的文体了,似和古玩、字画一样,成了一种互相赠送的礼品,一种高级玩味的东西。我在下面挂职时,分管文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导组的组长,曾想过旧体诗应该列入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里去。因为写旧体诗的人虽然很多,但像寓真这样真正懂、写得好的人并不多。看到寓真所写《聂绀弩刑事档案》,我又找到了当年读他的散文那种感觉,有文采,有感染力,能给人以美感。
潞潞(山西作协文学院副院长、专业作家)我是寓真的忠实读者,这是因为他的诗歌的魅力和带给人的阅读的愉悦。尽管寓真是写古典诗词,我是写新诗的,但是实际上我们面对同一个问题,就是每一个诗人在写作时遇到的用什么文体的问题。寓真的幾本诗集,除去一本新诗,其它都是中国传统诗歌的形式,歌行体诗使我尤为感兴趣。一个诗人决定用什么文体来写作,决定于他的文化储备、价值观和审美趣味。寓真的诗,从律诗、绝句一直到歌行,都是中国古典形式,可以看到他的诗歌的血脉,是中国传统文化,是传统诗歌一脉相承的那种血脉。中国的诗歌史,就是文体集大成的延续史,从最初的四言诗,《诗经》体,到后来的五言、七言格律等等。我的理解,歌行体就是古典诗词的自由体。歌行体从形式到它的内容,都非常有意思、有特色。歌行体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汉乐府,乐府作为当时一个音乐机构,主要是采集民间的音乐、诗歌、歌谣,一方面是有文化的功能,另一方面也具有皇帝和最高决策层体察民情的功能,这也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形式和内容的传统形成的重要因素。像寓真诗中,那种关注民生的表达,现实感很强,就是与传统诗歌一脉相承的。甚至就他的歌行体诗歌的这种形式而言,在阅读的时候,让人有一种自动回放的功能,能感觉到仿佛白居易的歌行、新乐府,如《长恨歌》、《卖炭翁》等。读寓真的诗感受之深,一是悯农,二是悯女,诗中表现的对女子的那种特别怜悯,这也一直就是中国古代诗人的悲悯情怀。可见寓真的诗的文体,完全是中国传统文化这条脉络相沿而来的。
寓真说他面对新的诗歌观念,是一个落伍者。我是这样认为的,就诗歌而言没有落伍者。因为各种文体各种文学形式尽管千变万化,但诗歌是最少变化的文学品种,基本因素就是音乐性节奏,从古到今一直如此。诗歌就像是惰性气体,是很少变化的。不管时局、时代怎样不一,诗的基本要素是永不会变的。如果诗歌没有音乐性,没有节奏,诗歌就消亡了。但是诗歌有一个极端的例子,“梨花体”,完全没有音乐性,没有节奏,随意分行,大白话。追溯到五四伴随新文化运动而来的白话诗歌,完全背叛传统,诗体拿来主义,完全西化,这种诗体现在看来是失败的。但我自己为什么走了写新诗的路子?我特别同意说是“身体写作”,诗歌是最直接的身体写作,你的气质、禀赋、语言、发声器官等等,你是深沉的,高昂的,气壮的,婉约的,都和你的身体有关系。现代诗有一种先锋性的关怀,对所有的年轻人都有着一种魅惑力,有年轻人永远要站在时代潮头的感觉。还有一个是价值体系、立场的问题,愿意做一个自由的诗人,追求完全民主自由。借助这种文化,就与旧体诗不同了,这是两个不同的系统,但文学是没有落后和先进之分的。我倒是想做一个落伍者,不想那么先锋。这几年我的功课是回过头来大量读古典诗词,主要是古典诗词的精神内涵太宝贵了。我更多的是吸收中国古典诗词精神含量的东西。在诗体上,我可能关心更多的是决定我的审美趣味的东西,我对符号学感兴趣。我们面对两种诗体,选择哪种是由自己的很多东西决定的。我前段时间写了一些诗,因为看到了中国古典诗歌对现实、人生、民生的关怀,越来越回到写实的路上了。这里有两种努力方向,比如要写中国古典式的格律诗,努力的方向是关注民生,最重要的是要具有作为一个诗人的那种情怀和境界;而要写从西方舶来的新诗体,当你不断地写下去的时候,你面对的可能是一个终极真理的问题,可能是一个绝对文体的问题,可能是一个纯粹的诗歌问题。我说我要做一个退步者,我想退回到中国古典传统上来。寓真的歌行体给我一种启发。其实歌行体并不神秘,也不仅仅是中国传统诗歌里有,西方也有过行吟诗。选用什么诗体有着巨大的文化背景。能不能在新诗里借鉴歌行体,寓真探索的歌行体是否也可能是诗歌复兴的一个路径,这也许是一个启示。
5、底层关注和忧患感
构成了传统诗歌的基调
王春林(山西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文学评论家)我一般搞的是小说评论,对诗歌充满了敬畏。这次我很认真地写了一篇短文——《读〈寓真歌行集〉有感》:
一,寓真的这部诗集所收作品,写作时间最早的是1963年,最晚的是2008年,前后的时间跨度达到了45年,可以说,这些作品的写作贯穿了他的青年、中年,一直到晚年的整个人生岁月。而且,这部歌行集带有明显的现实主义色彩。我首先的一个突出感受就是,寓真以这样一种歌行体的特别形式,从他自己真切的人生感受出发,为我们提供了一部长达45年之久的中国社会的诗史。历史学家们在以历史教科书,以学术著作的方式,书写着历史,而诗人则是在以歌行体的形式书写着历史。我觉得,甚至于在整个中国,寓真的这种书写方式都是独一无二的。能够从1963年的生存困境写起,写到十年浩劫的文革,写到武斗,写到改革开放,一直写到当下时代的市场经济,我个人认为,诗史式的写作可谓是功莫大焉!
二,在这部歌行集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诗人一种格外强烈的忧国忧民情怀的存在。比如第一首《回乡吟》即是如此。诗中有这样一种对比性的描写:一方面是“初离家时每回头,京中耽乐忽忘忧”,“书中枉然读先哲,脑中几将忘黎民”;另一方面却是:“一朝重见乡亲面,何至肌瘦颜黑黄。吞噬生民猛如虎,天灾人祸俱嚣张。”两相对比之后,诗人当然也就产生了一种特别强烈的愧疚心理:“令人反躬心怅惘,更觉无地置颜羞。岂能京华自安舒,忘却父老与耕锄。”要知道,诗人写作这首诗的时间是1963年,在当时能够有如此思想,如此胆识,的确是相当难能可贵的,应该得到我们的高度评价。在其中,既表现了诗人一种特别可贵的现实批判意识,也同时表现出了一种深刻的自我批判意识。双重批判意识的存在,当然也就使得这首诗歌具有了相当的思想艺术价值。
三,在这部歌行集中,我们还感受到了诗人一种朴素异常的真情实感的表达。这一方面最值得注意的作品,就是写于1993年的那首《送母还乡》。在这首诗中,诗人一方面以极其简洁凝练的笔触概括表达了母亲那其实充满了艰难坎坷的一生,另一方面,却也真切地传达出了诗人内心深处对于母亲的深厚情感。其中诸如“饥寒每暗泣,战乱更愁眉”,“满面皱如刻,一头白雪飞”,“怅然此分手,车远还欲追”,“涧水汩汩去,山烟阵阵垂”之类的诗句,可以说能够给读者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张贵宝(太原市城市监察四大队队长、诗人)有幸拜读《寓真歌行集》,感慨万分,厚重的生活积淀,孜孜不倦的追求,使寓真的创作硕果累累。他的作品贴近生活,针砭时弊,为“小人物”鼓与呼,为时代著华章,于平实中透着淡淡的馨香。“炎夏一炉烧,会厅千扇摇”,“台上轮番讲,台下人难熬”,“生命诚可贵,何苦会中凋”,某些会场百态跃然纸上。“官家圈地商家占,禾黍罢种高楼建”,“失此生计,忍教妻儿无路投/辛劳所得,纵然大半缴车主/小有赚取,一家衣食暂无忧”,作品反映了失去土地转而包车跑出租为生的农民的无奈与艰辛,它使我不禁联想到了白居易的《卖炭翁》。“歌”源于上古,“行”创自汉代,至唐通称歌行。作为古代诗歌的一体,今人用之渐稀,但其自由的形式,不求对仗,音节韵律也无固定的格式等特点,成为其生存的土壤。
刘淳(《黄河》杂志副主编)寓真是一个有良知和正义感的诗人。他有着法官和诗人的双重身份,在现行体制里面,法律的良知和正义感体现的如何是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谈起来极其复杂,但我肯定他是一个有良知和正义感的诗人。在寓真的这部歌行集诗里,我感受到诗人充满了一种对中国现实社会底层的关注。这部诗集所收集的作品从时间的跨越上看整整45年,最早的创作于1963,诗集中开篇作品充满诗人对中国底层人物的同情与怜悯。应该说,用诗歌的形式关注中国底层社会在今天并不多见,甚至极其少有。寓真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能坚持这样做,所以我说他是一位有良知和正义感的诗人。去年秋天以来,我一直在酝酿写一篇文章,叫《中国当代艺术的底层关注》,就是当代艺术家以怎样的角度和什么样的视野关注中国底层的社会现实。但这里边就有个问题,什么是底层?我们从传统意义上理解底层就是农民、进城务工者和城市失业者,这三者在中国现实社会一直存在着,而且从过去到现在成为政治和文化领域研究社会底层的主要对象。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考察的话,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比方说,妓女是不是社会底层?同性恋是不是社会底层?他们的收入很高,他们生活得非常奢侈,但他(她)们却是被中国传统道德所鄙视的人。政治上被压迫的是不是社会底层?所谓是底层还有哪些领域,换句话说,还有哪些被我们长期忽略或遗忘?我们为什么要关注底层,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大问题。至于用诗歌或绘画,只是一个不同的形式而已。所以我现在觉得底层的概念越往深追究越模糊,很难去定义它。从学术的角度上说,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过去我们长期停留在一个比较简单的表层上,今天我们正在走向深入。寓真的这部歌行集,可以帮助我们感知或了解中国底层社会,了解中国社会从60年代到现在的某种历史变迁。这部歌行集,体现了寓真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关注,体现了诗人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深度思考,在那一行行的诗里,我们感受到作者的愤怒,也看到诗人对中国底层人物的关注和同情。
所以我想说,寓真的诗尽管是歌行体,还属于古体诗,但诗人没有将它仅仅作为一种形式去呵护,而是用它来反映中国的当代问题,这一点非常难得,非常可贵。值得我们学习与思考。
6、传承中国优秀文化
是诗歌与诗人的担当
李杜(山西日报文化部主任、诗人)我的两点感受,一个是诗体问题,一是中国文化传承问题。唐代的诗歌有两个巨大成功,一个是律诗的恢弘,一个是歌行体的伟大。歌行体里有李白的诗,当然很好,但最终两个成就都达到高度的是杜甫。杜甫把律诗提升到一个至高无上的境界,律诗的本身创造是中国传统的创造,是中庸哲学的艺术表现,它不像外国的东西可以不对称,中国的中庸就是非对称不可,整个是儒教的传统。世界一百位文化名人排座次,没有李白,唐代只有两个,一个是杜甫,排在第十七位,另一个可以候补的是韩愈。为什么不是李白而是杜甫?因为在唐代传承儒家文明的只有杜甫。除了杜甫,当然还有韩愈,此外你在哲学界、文化界找不到一个更有代表性的人物能够代表儒家文化在唐代的传承。李白说到底是道教诗人,所以他诗中才有一种灵动仙气,他才有诗仙之称,但他不是儒家文化的传承者。两千年的儒家文明在唐代得以传承是通过诗歌,通过杜甫,通过他的两个创造。一个是文体的创造,律诗,又叫近体诗,他把一个诗体推崇到一种无可更改的地步,后人只能照他的去写。律诗是作为一种中庸的温柔敦厚的文化传统产生的诗体。杜甫的另一个创造,就是他又以他的歌行体诗记载了当时的历史,如《三吏三别》,唐代的重大历史事件在他的诗中反映出来。
寓真的诗几乎涉及了中国诗歌的各种诗体,歌行体,律诗,绝句,还有新诗也写得不错。寓真其实走的是一条非常不得了的路子。文以载道,我们写诗要有道在里面,道很大,“道之道,非常道”。在中国文化的传承上,寓真以后的开拓空间是非常大的。像他处在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个情景下,这样的个人经历,以他的心胸境界和学识素养,都能使他有所建树。从寓真的写作中得到的关于诗体和中国文化传承问题的启示,是我们写新诗的需要学习和融合的,旧体诗就我的愿望来说,会有它的一个复兴的到来。
金汝平(山西财经大学教授)我是写新诗的。我写诗这么多年,觉得不论是写新诗还是古诗,都有许多问题。中国的古代诗歌虽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我觉得以三千年文化的辉煌而论,这个成就取得还不够。仔细看一下中国古体诗的发展,其实是非常缓慢的,和封建专制社会的缓慢是成正比的。到了明清以下,基本上是步唐诗的后尘,谈不上任何创造性,所有有才华的诗人都在唐诗宋词的巨大才华下失去了自己创造力。中国传统出现了危机,同时遇上了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导致了中国文化也对冲击做出了判断,就是新诗的产生。新诗的产生有没有合理性,肯定有,就是建立在古体诗在当时来说比较衰败的基础上,这就是古体诗面对的一个危机。新诗到今天,真正发展也就是三五十年。到了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文化政策的原因,一方面打破了过去的贵族体系,同时也扼杀了诗人的创造性。在漫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的诗歌基本上是在政治宣传附庸的位置上出现的。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文化大革命结束,出现了朦胧诗,实际上没有多少年。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古代的歌行体其实应该是我们诗歌发展的真正方向。现在的新诗面临的困境比较多。自从网络出现以后,百家争鸣,大多数人的印象,从社会的角度来说不太接受新诗。新诗没有传承古典诗歌的精髓,这种精髓我觉得不仅仅是格律。今天的倾向是把格律松开,更显示一种相对的散文化,又更具有诗意的内涵的东西。南方一个诗人说:“现在写新诗写得比较不错的诗人,回归到语言,但是没有回归到汉语言。”如果建立在對西方诗歌西方文化充分的了解上,又汲取了汉语内在规律性的东西,可能写得更好。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摸索。聂绀弩的最大特点是能够把今天生活的东西容纳进来,有很多口语化的东西。古体诗需要吸纳今天鲜活的汉语言。现代诗也需要把古代的内在的一种音韵、格律吸纳进来,互相搭配,互相弥补,也许是另一种风景。
寓真(原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诗人)文学观念在不断更新。诗人日益走向个人化,追求独立性。一些诗人认为:诗就是诗本身,语言就是诗的本体,似乎并不关注诗的内容和功能,它的社会意义、现实意义等等。如果是这样的,我的观念就难以跟进,我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觉得是一个落伍者。我的观念,无非还是为许多人所不齿的“诗言志”之類,在这本歌行体诗集中,尤为显著。其实我又何尝不想超脱于红尘之外。从政了许多年,厌烦之极。既做诗人,就应该饮美酒、吟风月,像陶渊明那样的闲适隐逸。我一直非常羡慕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何等自在。但认真读过鲁迅《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这才完全明白了不能做陶篱的梦想。鲁文从“三曹”和“建安七子”,说到了陶渊明。据鲁迅说,陶渊明虽然博得了田园诗人的名称,却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还在留心朝政,“与时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例如《陶集》里有《述酒》一篇,写的就是当时的政治。所以鲁迅说:“据我的意思,即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世间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世事未能忘情。”又据美学家朱光潜的研究,渊明的大半生中,兵戈扰攘,几无宁日。“渊明一个穷病书生,进不足以谋国,退不足以谋生,也很叫他忧愤。”“渊明诗篇篇有酒,这是尽人皆知的,像许多有酒癖者一样,他要借酒压住心头极端的苦闷,忘记世间种种不称心的事。”朱光潜赞扬说,渊明在中国诗人中的地位是很崇高的,可以和他比拟的,前只有屈原,后只有杜甫。而屈原和杜甫,却是比渊明更加沉郁的。原来如此。田园诗人,风流名士,原来也都是耿耿于政治的。古人尚如此,何况今人,何况我辈。如我一直在政界充任微职,地地道道的俗吏凡夫,怎么着也清高不起来。所写的诗,大概是总也脱离不了政治的。我于是便有了自知之明:自己的诗绝对达不到超现实、唯美性、独立性和现代意识,只能算某种政治诗而已。政治诗可能是个不够美感的名称,但当代新诗早已形成了政治抒情的传统,而且一直处在主流地位,名家屡出。只是我这种政治诗,又属另类,背时的一类,绝对进入不到当代诗歌的主潮当中。旧体诗词被逼于边缘状态,加之我写的内容又属背时的政治诗,因此,一直不愿意拿出来。而今已到迟暮之年,且已退出公职,不大顾忌了,才拿出这本歌行集来,听听诗友们的批评意见。听听意见,亦无他意,只是为了在写作上总结经验教训,达到自我提高,有些旧作还能再作一些修改。既然远离主流,更与名利无涉,正好能让自己达于心境的自由、醇化和安之若素。
衷心感谢以上参与对话、讲了许多重要意见的各位专家和诗友,感谢从外地发来函电关注诗歌讨论的罗盘、关明两位先生和积极参与组织这次活动的胡树嵬先生。各位专家诗友的远见卓识,使我深受启迪,不仅拓开了我的眼界,同时鼓动了我的信心。韩石山先生认为我很自信,那就可以说听了诸位的批评,更加自信了。其一,诸位对于歌行体这种相对活泼、并有可能与新诗达成某种融通的形式,及其富于现实批判精神的政治诗的传统品质,予以了认可;其二,诗歌不是诗人自酌的小酒,不能忘却它的历史担当,李杜先生讲到的中国文化传承的意义,令人震悟。正是如上两点,使我对于诗的写作得到了新的鼓舞。虽已迟暮,仍愿同大家互与勉励,在中国诗歌的复兴中,“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周潞 寓真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