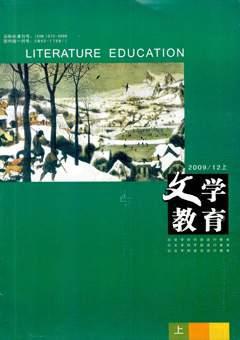读阿斐和郑小琼的诗
阿斐,原名李辉斐,1980年生,江西都昌人。编有诗集《以垃圾的名义》,担任《2004-2005年中国新诗年鉴》执行主编。
阿斐曾被称为“80后第一人”,第一人不是指写得最好,而是指出道最早,提供了某种标示性的东西。杨克说阿斐最早摒弃了那种在纸面上强说愁的写作,把都市漂泊的无根感受,以快意张扬的自嘲口吻尽情宣泄出来,非常具体传达了存在缝隙里小人物的生命疼痛。
《众口铄金》虽没有显示太多技巧,只是朴素说出一代人的命运人生,恰恰是一种最典型的“说出”,故得到同代人一致认同:
我的孩子都快出世了
而我昨天还是个小孩
两个“孩子”,包含了丰富含义,前一个,是真正意义上的“新新人类”,而昨天的“这一个”则充满辛酸的内涵,它是父母辈的缩影,代表人母的,是机械的、睡着的、“毫无灵感的蚌”;代表人父的,是猪一样的生态与猪圈一样的命运。两个孩子的抽象与反差,涂上时代的鲜明烙印。
而更为深刻的,是后来引申的“说出”了一个时代,一切弱势群体的心声:
战战兢兢地伸出孱弱的手
迎合命运的安排
像甘霖之下无辜的万物
无力改变弱势的处境,在命定相似的圆中兜圈子。挣扎、无奈,是“一代人的精神特征和特殊命运”。类似这样的主题与写照,一直贯穿着阿斐的写作,像下面的诗作:
“我哑口无言地走进这个世界/在这个巨大铁笼的一角圆睁恐惧的双眼/我分明看到一些人像野兽却披上人皮/我分明看到大多数人像野兽一样暴尸荒野/角色替换如车轮疯转/我在成为我之前就已失去了自我”
再次地印证底层的诗写经验。这一首同前一首黄土的“错乱”不大一样,它不是具体针对种种形而下事物,而是凿开一点深入其中的核心。
所谓“底层经验”诗写,既是指对人类生存理由的追问,更是侧重对人类生存境遇的直接呈示。凸现底层生活的矛盾、问题,以普通人的身份进行叩问,充满群体的和个人的生命吁求和命运感怀。
像阿斐这样的底层诗写,完全与雕刻、漂亮无缘。多数是从现场观察出发、从感同身受出发(大量打工诗是有力证明),只有少数停留于底层经验的想象力上,这就使得它摆脱“廉价的良心”、简单的倾诉或抱怨,真正出自自我的真实,写出内心的惊恐和战栗。
诗歌在与现实的关系上,勇于走向民生承担,是新世纪诗歌的一次“回心转意”。倘若在直接呈现的规约下,再加强点“技巧”含金量,一定会更上一层楼。
附:众口铄金/阿 斐
朋友告诉我
我变了
是变了
面目全非
群众的眼神已经异样
我的孩子都快出世了
而我昨天还是个小孩
孩子的母亲躺在床上
像一只毫无灵感的蚌
机械地睡着
像所有初为人母者那样
没有目的
没有记忆
梦中她的丈夫披红挂彩
乡间最耀眼的新郎
如果我是一头猪
命运会赏赐给我一个猪圈吗
如果我是一个人
孩子她妈,是否会赏给我一个安稳的未来
所以我变了
变成了朋友预想的模样
一个坐着八抬大轿的草民
战战兢兢地伸出孱弱的手
迎合命运的安排
像甘霖之下无辜的万物
郑小琼,女,1980年生于四川省南充。2001年南下广东打工。曾获得首届《独立》民间诗歌新人奖等。出版有《郑小琼诗选》。
9次出现“经血”,6次出现“蝙蝠”,显然经血与蝙蝠反复交缠,构成该诗主导内核。
“沿着黑夜蜗行,战争的阴影 覆盖住宗教的器具 虚构的城堡在海洋另一端沉没。”开篇的“黑夜蜗行”、“战争阴影”、“宗教器具”、“城堡”,没有明确的特定指示,所以可以看作是泛指,但泛指到底还是给出了线索:古往今来所进行着的男人与女人战争,或性别或为女人的战争,总是以男人的胜利告终。战争少不了神话的虚构成分,但真实的存在是,女人,像蝙蝠一样出没的女人,她们忍受“千年无法意料的事”:“尖叫”、“潜逃”、“穿越”、“挣扎”、“洗涤”。五个强烈性的动词,描写了她们的性别特性、习性、隐密行为和苦难。太阳不容许她们白天出没,但穿越太阳,如灯蛾那样扑火;被放逐于白天,只能吸收黑夜,那么黑夜就成为她们骨骼的一部分。始终要“在泉水边洗涤千年尸衣”,就是注定要洗涤历史遗留给她们的宿命,千年不变。第一节写出性别包裹下女同胞的不幸命运。
“她们的哭泣进入战争的列车。轰隆变形的私语”。女人只好继续扮演失败的悲剧,沦为哭哭啼啼絮絮叨叨的弱者。但弱者也不能甘于沉沦。纠结起体内的经血,长出蝙蝠一样的刺,长出尖细的头颅,发出有形的慌叫。经血涂抹——喂养饥饿的蝙蝠,经血喷涌——鼓翼穿越太阳的蝙蝠。“经血、蝙蝠、女人”,一旦在诗人主观意识驱使下遭遇,便三位一体,合三而一了。长期蜷伏,被囚禁被打压的深层女性意识、浮游在显意识或潜意识里的“性别”冲动,终于不甘落败,顽强突破层层硬茧,发动起来、飞扬起来了。
这还不够,“她渴望经血在蝙蝠身体长出阳具,她需要自我繁殖/受精、生育。然后把这种变异唤作女权主义”。如果说,此前作者关于蝙蝠的隐喻和换喻之行,虽浓烈但还保持适当的“遮羞”状,至此则抑不住掀起头盖布,愤然跳将出来呛声:觉醒后的“女性意识”,还要不断扩大、生长、繁殖,变异为“女权主义”。“她渴望经血在蝙蝠身体里长出阳具”,公开的宣称叫板,赫然凸显出强烈的女权犄角,铮铮作响。在这里,“阳具”是最具代表性的男性象征物,它几乎涵盖男性世界的一切,但最重要的是影射男权最高权势。隐藏在诗人内心对性别权力的向往,昭然若揭。这一奋不顾身的“冲刺”,当然主要源于诗人与她的姐妹们多年的经验:即“下水道”的生存和“霓虹灯”的生活。前者在底层,污水般流淌着城市最低贱的“垃圾”。后者在“天堂”,纸醉金迷地沉浮,她们的挣扎或“撕咬”,抗争或交易,都成为作者书写的资源和动力。
作为女性诗歌的蝙蝠,应该穿过更为艰难的纵深地带,在思想的悬崖,向下俯冲,向下俯冲……“俯冲”意味着勇猛、义无返顾,意味着不计后果。“俯冲”再次强调女性的决绝,不甘罢休,甚至希望通过暴力决一雌雄。然而,“江水流过烧焦的荒野/冷,悄无声息的抵达拱形的城堡”。一番拼杀,一片狼藉之后,不是还要回到走出不去的“城堡”吗?而一阵反省,沮丧和无奈之后,作者最终希望:“让我返回那座女性黑暗的光亮部分”。“黑暗的光亮部分”——意指还有信心在黑暗中坚守,“在石头中点灯”。
因为还有那么多的“黑夜”在吞没我和姐妹们,还有那么多女人成为货架商品的一部分。作者深深意识到,“我的经血之间无法勃起权欲的阳具”。女权意识或女权主义无论多强大,最终还是无法取得完全平等的两性世界,这仍旧是难逃宿命。但“多血质、敏感和天性”的本能,依然一直强化女人固有的特质,一直还会受到黑暗的伤害,同时也“划破”黑暗。毕竟,世界在进步,“呈现乳房样的星光”。微弱的希望,微弱的诗歌蝙蝠,在星光下继续不停地扑打着翅翼。
附:蝙蝠/郑小琼
沿着黑夜蜗行,战争的阴影覆盖住宗教的器具
虚构的城堡在海洋另一端沉没。苍凉的尖叫
悬崖的风潜逃,千年无法意料的事,蝙蝠穿越
太阳的羽翼,白天在它的肉体里挣扎,黑夜已成为
它骨骼的一部分。女人在泉水边洗涤千年的尸衣
她们的哭泣进入战争的列车。轰隆变形的私语
蝙蝠在她肉体蜷伏,在她血液里飞翔
她变形的手长出了蝙蝠一样的刺,它尖细的头颅
她有形的慌叫。她的经血涂抹一只饥饿的蝙蝠
她的经血喷涌的姿势象一只穿越太阳的蝙蝠
她渴望经血在蝙蝠身体长出阳具,她需要自我繁殖
受精、生育。然后把这种变异唤作女权主义
她的经血在南方的下水道里流淌。更多的蝙蝠在撕咬
男人们。在霓虹里飞翔,更多的黑暗在灯里升起
夜晚正在低头忏悔。她把自己安放在酒液浸泡的诗歌中
诗歌的蝙蝠穿过女性的纬线。经线的思想在山崖上
一直向下俯冲,向下……江水流过烧焦的荒野
透过红色的霜。冷,悄无声息的抵达拱形的城堡
让我返回那座女性黑暗的光亮部分。看不见的事物在流逝
黑夜正逐步吞没我和姐妹,他们一天天将我们出卖
最后成为货架商品的部分。我的经血之间无法
勃起权欲的阳具。我们多血质和敏感的天性部分
在黄昏中变浓。在深红的岩石与经血的反光
一只女性的蝙蝠无法逃避它的宿命。它无法自我繁殖的
必将社会的暗影刺伤。世界呈现乳房样的星光
陈仲义,著名诗评家,现居福建厦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