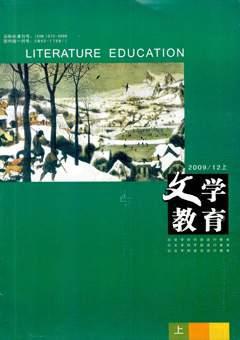《为奴隶的母亲》的悲剧之美
“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正是《为奴隶的母亲》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的写照。不论是春宝娘、皮贩,还是秀才、大娘,尽管他们有着对立的阶级背景:一边是农民,一边是地主;一边食不果腹,一边家财富足,但是都摆脱不了社会历史背景和封建文化凌驾在他们身上的巨石,他们都有着各自的不幸。那么这样的悲剧又何美之有?鲁迅先生说过,悲剧就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小说中那些被传统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人的尊严、女性神圣的生育能力通通都被物化了。这里的人是没有尊严的,甚至于连做人的权利都无情地被剥夺,春宝娘只是奴隶,甚至“恐怕竟和母狗一样……还要到处奔求着食物”。女性如此神圣的生育能力,也不过只能等同于一百元钱而被当作一种生育工具。
皮贩曾因为被追债而走投无路,差一点就跳进潭里,但就是因为对活着的渴望而“总没力气跳”。在无奈和绝望之际,不得不从他的妻身上打起了主意,因为儿子是只有一个的,自然舍不得,一百元把妻典给李秀才家三五年生养子嗣,延续香火。皮贩是可悲的,为了活着,苟且的活着,不惜将自己的结发妻子出典,“可是穷了,我们又不肯死,有什么办法呢?”但是在女人“面前旋了三个圈子”,羞愧悔恨却对她说不出口,可见其实他的内心也是无比痛苦的,但又不得不向现实低头。
秀才家是“有吃有剩的人家,两百多亩田,经济很宽裕”。即使有着如此殷实的家底,他仍具悲剧性。秀才曾养过一个孩子,但后来得病死了。五十多岁,对于受着封建宗嗣制度熏陶的秀才来说,他深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若自己不能为家族传宗接代,他不仅使自己更会使自己的家族颜面无存,这是封建家族决不能容忍的,所以他不得不为生养子嗣想尽办法。秀才是有经济能力纳妾的,他也有纳妾的理由:男子年过四十而无子嗣是可以纳妾或是典妻的,但他还是选择了典一个妻子来替他生儿子。大概他是有点怕妻的,大娘无缘无故的叫嚣、唠叨,他从没说过一句重话;也大概他是很爱妻子的,所以他不再纳妾。当秀才得知女人怀了他的孩子时,欢喜地吟诵起《关雎》,更是称有了孩子是比“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更快乐的事。这其实就显示出秀才在封建传统文化下的渺小。他是可悲的,但他决不能抗争,他也没有能力抗争,在他的家庭,在他所习得的文化之下,唯有遵从。他的快乐只不过是终于完成了替家族完成传宗接代的“光荣使命”,不过是用秋宝来证明了他不会成为封建家族的罪人,仅此而已。
秀才的妻,在封建传统文化的重压下,其悲剧性更加突出。大娘并不是一个逆来顺受,任由丈夫来摆弄的怨妇。她可以动辄就训斥秀才“老东西”,可以向他抱怨不满,她能阻止秀才纳妾,但是却又不得不帮着秀才找媒婆物色相当的女人典进家来生孩子。当她看到自己的丈夫与别的女人同房时,她无比痛苦,却殊不知这都是封建礼教文化所导致的,她只能通过辱骂来宣泄自己的情绪。她也是很精明的,深知母凭子贵的道理,所以她坚决反对秀才续典或是永远买下她来,甚至以死相逼:“你要买她,那先给我药死吧”。大娘,这样一个封建家庭里的女人,责任是无比重大的,她不光对她的丈夫负责,她更要对他的家族负责,她有着替家族传宗接代的使命,大娘自己完不成这个任务,她就必须找了人来替她完成,就算有再多的不满和怨气,自己也不得不忍气吞声。
春宝娘在残酷封建文化的压榨下悲剧至极。她,甚至连一个正式的名字都不曾有过,给她的代号不过就是两个字——女人。她从来就不曾有过做人的尊严,只是一个无名无姓的“奴隶”。她是皮贩的奴隶,皮贩迫于生计就将她出了典;她是秀才的奴隶,秀才典她不过是为了延续香火,对她好是因为她有了自己的子嗣,送她的青玉戒指,也不过因为是要传给秋宝的,她仅仅只是生育工具;她是大娘的奴隶,大娘任意羞辱她、嘲讽她,她甚至连做母亲的权利都被剥夺了,秋宝只能唤她作“婶婶”,却唤大娘作亲娘。春宝娘也总是幻想春宝和秋宝都在她的身边,不过只化为泡影。在她三年后回家之时,她是永远的见不了秋宝了,而此时的春宝也已经不认识她,“简直吓的躲进屋里他父亲那里去了”,晚上只是“陌生似地睡在她的身边”。
悲剧也是一种艺术,只是它给予人们的美,却要壮烈得多,不是让人由衷感叹,而是令人反思震撼。
谢嘉沂,重庆师范大学文新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