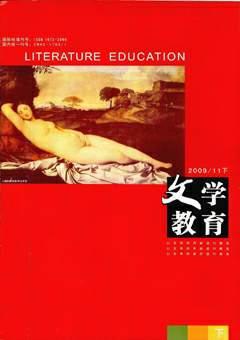《红字》中海丝特.白兰的伦理蕴涵
陈 了
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 1804-1864)作为美国19世纪影响最大的浪漫主义小说家,他的代表作《红字》以主题思想深遂、想象丰富、写作手法独特而标志着美国长篇小说创作上的一个重大突破,被奉为美国文学经典。就主题而言,《红字》既是一部爱情悲剧,更是一部道德悲剧,作品中浪漫主义色彩浓厚的主人公海丝特身上蕴含着明显的清教伦理倾向的道德评判。下面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对主人公海丝特·白兰的人物形象进行分析,从而对《红字》的伦理内涵进行深入挖掘。
一.尊严的维护
海丝特的形象深入人心,作为一个坚强的女性,她具有一个抗争的人生经历。海丝特珍视个人幸福,坚信自己的追求,为此,她抗争,不惜单独同那个社会的宗教与道德习俗作战。虽然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斗争,但她无所畏惧,决不退缩。在她的内心深处,对狭隘的宗教及道德习俗的偏见是蔑视的。
“红字”本是耻辱的标志,但她却精心地把它绣得金光灿烂,如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这个字以细红布作底,四面围以精美的刺绣和奇特的金线花边,是煞费苦心、用无比丰富瑰丽的想象制作出来的……堪称华美绝伦。”[1]小珠儿是她“罪恶”的结晶,她却把女儿打扮得像个小天使似的,让她在无忧无虑、无拘无束中自由地成长。在示众台上接受审判时,面对法官和民众,她表情坦然;面对众人要她供出自己孩子的父亲的逼问,她斩钉截铁地回绝:“决不说!”在判决后的岁月里,无论走在大街上,还是到别人家里去做女红,她的衣服上总别着那个鲜红的“A”字,坦坦然然,从不畏缩,从不以别人的躲避和沉默相向为意。蔑视教规的海斯特·白兰表现出顽强的反叛精神,大胆的面对来自于社会、教会的羞辱和迫害。当她从狱中迈步到观众面前时,人们惊奇的发现她不但没有在“灾难的云雾中黯然失色”,反而闪现出非常美丽的光。她的脸上现出高傲的微笑,她的目光是从容不迫的,她身上的服装是十分华美的,就连那象征耻辱的红字,都绣得异常的精美。在她心中,她的道德善恶观与传统教会灌输的是迥然相异的,与其说她坚强乐观地生活,倒不如说她自从在耻辱柱戴上A字的惩处之后,便不再把教会和世俗价值观放在心上。她在厄运面前表现出来的尊严,在教权压抑下展示出来的人性力量使她的人格不断上升,她改变了那红A字在人们心中的耻辱含义,那红A字发出了超凡脱俗的光芒,成了她行善积德美好人格品德的标志。她成了富有创造力的“能干的”人,成了善良的神的“天使”,成了“令人尊敬的”先知者。她还汲取了“比红字烙印所代表的罪恶还要致命”的精神,把矛头指向了“与古代准则密切相关的古代偏见的完整体系——这是那些王室贵胄真正的藏身之地”,称得起是一位向愚昧的传统宣战的斗士了。
霍桑用浓郁的笔墨将海斯特的反抗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从出场到结局,她的反抗精神一直如生命之泉贯穿着整部作品。她形式上虽然接受佩带红色A字的惩罚,但在思想上却没有接受惩罚她的那些社会道德规范。
二.爱情的执着
海丝特的爱情核心精神就是勇敢追求,永不屈服,决不向世俗妥协。尽管这种爱不受法律和宗教的保护,被人们视为罪恶,但她却在她自己爱的世界里独自做着爱情的享受,执着地爱着。
爱情本是人类的天性,但按照基督教义,亚当和夏娃偷吃了伊甸园的智慧之果,懂得了男欢女爱,不再靠上帝创造而由自己繁衍人类,这本身正是“原罪”,至于私情,更触犯了基督教的第七戒。霍桑虽深受教会影响,但自从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爱情早已成了文艺作品永恒的主题,时时受到歌颂,他即使再保守,也会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海丝特是勇敢追求个性解放、爱情自由的先锋,海丝特对齐灵渥斯坦言,“我没有感受到爱情,我也不想装假”。黑格尔讲过:“爱情在女子身上显得最美,因为女子把全部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都集中在爱情里,她只有在爱情里才找到生命的支持力;如果她在爱情方面遭遇不幸,她就会像一道火焰被第一阵风吹熄掉。”[2]在婚姻中从没有尝试过爱情的海丝特·白兰内心有着大胆狂放的渴望,她敢于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爱的权利和力量,认为她与齐灵渥斯的婚姻是“一种错误而不自然的关系”,是一种爱情的献祭。她的“含苞的青春”几乎被埋葬在这不合理的婚姻中。为了尽可能避免这种生命的难堪,获得新的生命意义,海丝特挣脱了清教教义的一切束缚,听从人类生命本性的呼唤,她勇敢地不顾一切地爱上了温文尔雅、一表人才的青年教士丁梅斯代尔,并与之有了爱情的结晶——珠儿,为此她犯了“原罪”,触犯了清教条里“十禁”之一的“通奸”。事情败露后,她被迫终身佩戴红字,为了爱人的名声,她独自承担了全部罪责与耻辱。即使是在七年后,当她看到情人丁梅斯代尔被内外的力量折磨得几近崩溃时,在牧师外出布道返回的路上,在人迹罕至的密林深处,她仍然敢于与牧师幽会,把自己丈夫的诡计告诉他,并劝说牧师带着自己和女儿离开这个充满谬误与偏见的地方,去创造新的生活。也正是出于对他的眷恋之情,她不但在他生前不肯远离他所在的教区,就是在他死后,仍然放弃了与女儿共享天伦之乐的优越生活,重返埋有他尸骨的故地,重新戴上红字,直到死后葬在他身边,以便永远守护、偎依着他。在她身上充分的体现出了“爱情”力量之大,死亡也无法战胜。
三.“罪”的救赎
在霍桑看来,通奸罪行本身是一方面,重要的是行为发生后个人对待罪恶的不同态度以及在他们心灵上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在《红字》中,体现在对人性罪恶的深入挖掘上,也体现在内心的忏悔与行为的过失获得救赎的信仰原则上。
基督教教义中强调信救赎,认为人类因有原罪和本罪而无法自救,要靠上帝派遣其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做牺牲,作了人类偿还上帝的债项,从而拯救了全人类。海丝特的救赎,或者说她相对于其他两个男主角更早获得的内心安宁和自由,是来自她对罪的公开与结果的直面和承担。狱中的经历,刑台的示众,社会的抛弃,胸前的“A”字,以及珠儿作为“A”字的活的见证,如此“众目昭彰”的刑罚倒成为她的某种“庇护”,因为她已无所隐匿,也就无所丧失。直至后来,彰显羞辱的红字甚至“含有修女胸前十字架的意义,给予佩戴的人一种神圣性,使她得以安度一切危难”,并赋予她一种遗世独立的自由,一种洞察人性的能力,一种体恤众生的胸怀。她依从内心真实的情感和本能,追求脱离习俗羁绊的个体自由,并在离群索居中坚忍不拔。她坚信自己与丁梅斯代尔的结合是出于内心真挚的激情;此后在独自担当羞辱、绝不供出情人,并含辛茹苦养育女儿珠儿的漫长岁月中,更印证了其爱情的坚贞不渝和对生命强烈的责任心。这一切使她有充分理由相信她所做的“有它自身的神圣性”。人人都是有罪的,通过救赎来达到一种精神的超脱。
海丝特·白兰努力用自己的善行弥补自己的过失,以至于许多妇女向她倾诉自己内心的秘密,寻求安慰和忠告。清教主义者认为,人拥有一种趋向于德性的自然倾向,不过,只有通过了某种‘训练,人们才可能达到德性的完美。海斯特·白兰正是通过这种“训练”努力用自己的善行弥补所犯下的罪,“最终净化了她的灵魂”。红字也不再是受辱和犯罪的耻辱火印,而是激励精神复活的标志和象征。
从一开始的“她焕发的美丽,竟把笼尽着她的不幸和耻辱凝成一轮光环”,令人联想起“圣母的形象”。到后来“并造就出一个比她失去的更纯洁,更神圣的灵魂”海丝特身上还体现了另外一种完全不同于罪人原型的人物原型形象—圣母原型。早在海丝特站在刑台上为通奸罪而接受惩罚时,霍桑就写道:“在这群清教徒中假如有一个罗马天主教徒,他看到了这个美丽的妇人,她那美丽如画的服饰和神采,以及她怀中的婴孩,自然地会想起圣母的形象,即那个令无数杰出的画家竞相表现的形象;确实,这个形象只有通过对比才能使人想起的,想起那个怀抱为世人赎罪婴孩的圣洁清白的母亲。”不仅如此,她的经历也颇似《圣经》中的圣徒:带着上帝的使命,受尽人间磨难,正如圣徒保罗说:“在我看来,上帝把最坏的位置留给了我们这些使徒……我们遭辱骂时祈祷;受迫害时忍受;受侮辱时以好言回报。”自从戴上红字,海丝特·白兰的生活便如同信基督的信徒一般,忍辱负重行善积德,最终用善行和仁爱感化了众人。海丝特·白兰因背负上红字这个沉重的“十字架”而得到拯救,并在一定意义上拯救了众人。在这里,当一切罪洗尽,海丝特·白兰也就成了因世人的罪过而受难的圣母玛丽亚式的女人。
陈了,女,湖北咸宁学院人文学院讲师,武汉大学2009年文学专业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