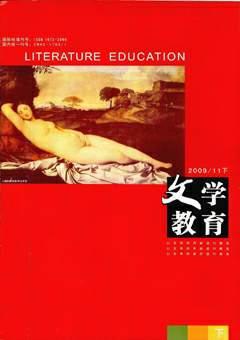莫里森对人类生存发展的思索
托妮·莫里森是当今美国乃至整个世界最受关注的黑人女作家之一。在她的作品中种族意识与女性主义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但身处多元文化共存的美国现代社会,她作品的主题并不为其黑人和女性的双重身份所限制,其作品在关注黑人民族和黑人女性命运的同时,还面向世界,深切关注人类的共同命运,密切关注人在这个多元化现代世界里的生存和发展。的确,正如某些评论家所赞扬的:她不仅仅是一位具有非裔美国人身份的作家,不仅仅是一位女作家,也不仅仅是一位黑人女作家。而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LouisGates,Jr.)的评价就更直接了,他认为:“莫里森的小说总是象征着人类的共同命运,既描述又超越了性别、种族和阶级的界限。”因此
莫里森既是“美国黑人作家的代表性艺术家、代言人”,又是全人类的“共同之声”,其作品具有普遍意义。
一.寻求归属
在当今这个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人们常常会有种失落感,而这种失落源于他们心灵的无所依托。归属感是人类的原始需求之一。尽管物质文明日益发达,世界趋向全球化,但人对自己本根理解和文化认同的意识以及回归大自然的意识却在增强。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现代社会,伴随着人们的物质欲日益膨胀,精神生活却极端贫乏乃至堕落,有些人甚至变得邪恶,背离了人类天性中原始天然的质朴美。因而,回归纯真的传统文化,回归朴素的自然生活成为很多人返璞归真思想追求。
人类的归属感首先体现在种族归属感和对祖先传统文化的认同上,这一切集中表现在《所罗门之歌》里。《所罗门之歌》里的麦肯·戴德就是一个物质的俘虏,为了占有财富,他脱离了朴实的黑人传统文化,曾经质朴的天性被扭曲,变得自私冷漠。在派拉特的回忆中,生活在农庄时,生活在黑人传统文化氛围中时,“麦肯是个好孩子”,他关心爱护妹妹,帮助扶持父亲,是个好哥哥、好儿子。但后来物质欲膨胀时,他却背弃了亲情,脱离了黑人社区,变得贪婪冷酷,远离了祖先传统文化。他压榨贫苦的黑人,蔑视住在贫民窟的妹妹,厌恶自己的妻儿。他的世界中只有占有财产一件事是他所热衷的。然而,他虽住着舒适的大房子,开着豪华的大轿车,却感到无比的孤独空虚。
在父亲物质追求的影响下,奶娃也曾一度空虚失落,直到他踏上文化回归的旅途,获得种族身份认同,被自己民族所接受,知道了自己祖上的真实姓名和他们的业绩,找到了自己被割断了的“根脉”,找到了种族归属,他才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精神自由和独立,产生了健康向上的自我意识,开始活得有意义。这正体现了莫里森所追求的一种人类最初的古朴和纯真的原始主义的回归。奶娃最后的起飞,也正是人类灵魂的一次原始飞跃。一个人只有回归到自己的传统文化中,找寻到自己的根才能坚定而自信,生活才能充实而幸福。
人类的归属感还体现在自然回归上。这一点在《所罗门之歌》里也有所表现。派拉特一家虽然一直住在一座狭窄的平房里,家里没有电,没有煤气,没有任何现代化设备,她们“用蜡烛和煤油灯来照亮房间,她们用劈柴和煤来取暖做饭”,她们吃简单自然的食物,却过得快乐而充实。自然原始的生活状态使派拉特拥有了一种独特的人格魅力。“虽然她就同大家所说的那么穷,眼神中却不见一点能够证明她贫困的东西。”“她算不上漂亮,可他心里明白他可以盯着她看上一整天。”在这里,莫里森旨在召唤人类回归生命的源头,在社会化过程中尽量保持人的良好的自然本性,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而找寻现代文明中失落的人性的光辉。
同时回归自然,人类可以获得精神上的洗礼。在物欲横流的今天,人们需要精神上的净化滋养,获得真正的心灵上的平静。奶娃就是一个人在月光下躺在原始森林的土地上,在蓝岭山脉之中,在一棵散发出香甜气味的桉树下顿悟的。清香的桉树、草丛和空气净化和滋养了他的灵魂。而且自然可以使人感悟生命。跟随着当地黑人完成了冒险、有趣的狩猎活动后,奶娃“他自己也笑着,笑得有力,笑得响亮,笑得长久。那是开怀大笑。他发现自己仅仅由于走在大地之上便振奋不已。走在大地上就像是他属于大地;就像他的两腿是庄稼的茎,是树木的干;他的部分躯体就这样往下延伸,延伸,直扎进石头和土壤之中,感到在那里十分畅快———在大地上,在他踏脚的地方。他也不跛了”。与大自然紧紧拥抱在一起,奶娃感到了生命的欢欣与活力,找到了自己的根本。
此外,自然还可以抚慰、拯救人的灵魂。《宠儿》中孤独的丹芙每每感到孤独失落时,就会来到房后的树林里一个圆而空的房间里,“在生机勃勃的绿墙的遮蔽和保护下,她感到成熟,清醒,而拯救就如同愿望一样唾手可得”。塞丝也不例外。每当感到困顿无助时,她就会寻求自然的庇护。她就会去一片林间空地———当年她的婆婆贝比曾在其间布道的绿色圣地,在那里她可以思考,可以领悟。那片处在树林深处的林间空地所具有的梦幻般的魔力和无限生机拯救了塞丝,使她在精神上获得再生。自然可以洗涤人心灵上蒙受的喧嚣和尘埃,恢复人心灵的清脱和空明,从而拓展人心灵的新空间,积储生命的能量,在深蓄厚养中实现灵魂的升华并赋予人无限的动力。人决不能脱离自然环境,人要与自然的发展保持和谐的状态。只有这样,人才能获得心灵的安宁,活得充实。
二.寻找自我
商品经济的冲击下的现代社会,增强了人们对物质追求的欲望。某些现代人在物欲的诱惑下人性被压抑、扭曲,在拜金、拜物、追名逐利过程中迷失了自我。他们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又被其异化,成为物质的奴隶。随着人们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越演越激烈的相互竞争,人际关系也愈发紧张,以致亲情淡化,人心浮躁,精神迷惘。物质富有与精神空虚的巨大反差,说明精神的匮乏对人的生存的威胁。特别是青年人,在这个充满活力与欲望、喧嚣与骚动的时代,对未来把握不住的恐惧与对人生意义的迷惘交织在一起,使他们失落、无助、抑郁甚至绝望。在沉湎于远较父辈更多的社会权力与物质享受时,他们更可能迷失。他们没有完善的价值观体系支撑,陷入一种精神危机。他们无法深刻体察祖辈的奋斗历程,同时也难以维系本民族深厚的传统文化,感到精神上无所皈依。对自我存在的价值和反思使他们陷入迷惘、困顿和虚无之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精神的流浪者。
他们不断追问自己:“我”是谁?世界与“我”究竟是什么?而“我”的位置又在哪里?迷离的年轻人身上出现难以排遣的焦灼感和浮躁气。因此,现代社会中的人们面对着自我创造的那些令人眩目的物质财富时,很难有由衷的喜悦,反而产生一种失乐园的忧郁,猛然发现自我已经迷失。于是“寻找自我”、“认识自我”、“人的全面发展”等命题,又以新的意义召唤着现代人。寻找自我、认识自我、发展自我的呼声汇成一股新的人本主义浪潮。
寻找自我也贯穿于莫里森的整个文学创作中。特别是在《秀拉》和《所罗门之歌》里,她连续探讨了这个主题。这两部小说从主人公与社会、与他人的关系的层面上,表现了秀拉和奶娃寻找自我的成败的原因和意义。《秀拉》中的黑人女主人公不断地与命运抗争,努力地寻找自我、发掘自我,竭力要实现自我的价值。她不愿意像其他黑人女性那样屈服于命运的安排,她从不逆来顺受,委曲求全,而是桀骜不驯、我行我素。她全然摒弃传统的道德观念。她不结婚,通过随意地与男人发生性关系来寻找自我、发掘自我。为自我发展而进行的斗争使秀拉变得孤立起来,远离保护、养育和引导她的人群。因为她盲目的抗争,她不被黑人群体所理解,受到众人的唾弃。同时由于她对黑人社会、黑人文化传统以及社会责任的排斥,秀拉的探索彻底地失败了。与秀拉相比,尽管历经坎坷,奶娃对自我的探索最终获得成功,原因在于他们所选择的探索道路大相径庭。奶娃有精神上的母亲派拉特的指引,又有南行时接受本民族古老文明的再洗礼的历程,真正懂得了只有接受了自己的过去和自己家庭的过去,他才能真正长大成人,才能真正地寻找到自我。回到南方,回到爷爷奶奶曾生活过的地方,寻到祖先的姓氏后,从未想过要为别人干点什么的奶娃想到要为别人干点什么了。
当南方的温柔妓女“甜美”给他搓背洗澡时,他首次主动要求给她也洗个澡,他还帮她洗刷盘碟、擦亮澡盆。不仅如此,他还开始想念派拉特的魅力,理解母亲的牺牲,意识到“他母亲和派拉特从一开始就为挽救他的生命奋争,而他从来连一杯茶都没给她们俩泡过。”同时他开始体谅父亲的做法并懊悔对哈格尔的冷酷。奶娃在不断的领悟中成长,懂得了爱,懂得了责任。他最终成为了一个富有责任感和道德感,懂得尊重别人、帮助别人,懂得爱、懂得善待他人的人,成功地找到了他真正的自我。秀拉和奶娃对自我的探索不仅仅是黑人的探索,它其实是现代人,特别是迷茫的现代年轻人对自我的探索。这也是奶娃寻找自我成功的意义之所在。
三.包容兼爱
物质文明日益发达,世界趋向全球化。现代人在关注归属感,寻找自我的同时愈发关注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在这个现代多元化世界里的存在和发展。莫里森在作品中不断深入探索,执着地为美国黑人乃至全人类寻找着出路。在莫里森看来,固然像《最蓝的眼睛》中的波莉、佩科拉和《所罗门之歌》中的麦肯·戴德那样完全认同、接受白人的价值观,甘于接受白人的精神奴役,逐渐抛弃黑人的传统文化本色是不可取的,但是像《秀拉》中的秀拉那样既不受白人文化意识形态影响,也不固守黑人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做法也是没有出路的。而像《所罗门之歌》中的吉他那样坚决地抵制白人主流文化、不相信黑人与白人有调和的可能,坚决与之针锋相对,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偏激和自以为是更是不可取的。吉他出身贫寒,因而对种族歧视有着切肤之痛。他不愿被奴役,特别仇恨白人。于是,他加入了以暴抗暴的团体“七日”,代号为“星期天”。该团体由七人组成,按一周的星期顺序给每个成员编上号,白人对黑人的种族暴力事件发生在星期几,代号为该日的成员就有责任以同样的手段进行报复。这个团体的成员都是极端激进的黑人。正因为吉他的这种偏激和自以为是,后来他与奶娃成了死敌,并误杀了派拉特。吉他的反抗很不理性。他并不知道祖先优秀的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他也不明白白人精神奴役的危害,他关注的只是黑人当下的生存状态。他曾对奶娃说:“奴隶姓氏对我没什么,只是奴隶处境让我讨厌。”但是非洲裔美国人必须拥有自己真正的名字,他们才能认识自身的价值,获得人的尊严和自由。因此吉他选择的路只能是一条死胡同,无益于保护和弘扬黑人文化。吉他激进的种族主义是狭隘的、荒谬的。最好的办法是,在保持黑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与其他外来文化兼容并蓄,扬长避短,走一条共同发展的道路,并用爱心去包容一切。费尔巴哈认为,爱是人的本质的表现,是人与人之间联系的基本手段。包容兼爱,世界才能和谐。
莫里森笔下的派拉特正是这一思想的代表,她守护着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但却不是一个极端的守护者,她以博大的胸怀去包容世间的一切人和事,以纯真的善心去关爱身边所有的人。她不仅关心黑人,也关心白人。她肯背负起被哥哥杀死的白人的尸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只有多一些派拉特这样肯包容兼爱的人,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传统才可能得到传承与弘扬。
人类社会是多样化的存在。任何一统天下的妄想都是违背人类社会发展的。因此文化霸权主义是行不通的。与之相反,文化多元化将成为推动世界文化进步的巨大动力。人类生活的这个世界,“各种文化形态都有自己存在的理由和活动的空间,他们彼此间的关系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同时共存和互补”。我们应赞同不同于主流文化基调的“他者”文化存在,弘扬一种包容的精神和开放的气魄,要知道不同文化的融合互补,是交流和对话而非冲突和对抗。因此,莫里森在她的作品中一直反对白人强势文化对黑人的精神奴役,同时她也不赞同黑人固守传统,因循守旧,极端排斥白人文化的做法。她始终热衷于不同文化之间既相互对立排斥又融合互补的错综复杂关系,她渴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对话。这一点在她的作品《柏油孩子》(又名《柏油娃》)中尤为突出。在《柏油孩子》中,小说的主角不再仅仅局限于黑人,小说对白人、黑人、浅肤色黑人都有生动的刻画,小说的背景也不仅仅是黑人居住地,而是拓展到了美国内外。小说中的骑士岛其实是美国的微缩景观,骑士岛的种种问题其实是美国现实社会中种族问题的写照。《柏油孩子》以同名非洲民间故事为框架构思,将男女主角儿子(Son)和吉丁(Jade)与兔子和柏油娃相对应。他们是一对相爱却又挣扎着脱离对方“柏油”般黏附力的黑人青年男女。男主人公儿子是黑人民族的儿子,他是非洲传统的极端守望者。他“虽然生活在20世纪,但他拥有的只是杜波依斯所说的一个传统黑人自我。他的思维定势朝向过去,对现代西方文明持一概拒绝态度。”他固守传统,因循守旧,敌视现代工业社会的文明进步,不想借鉴学习白人的任何社会组织的经验,拒绝任何变通。因而在白人世界、在现代社会,他有一种疏离感。
吉丁则是由白人雕琢出的一块“美玉”,在行为上、思想上代表者哺育了她的白人文化。作为在白人世界长大的浅肤色黑人,吉丁完全脱离了黑人文化的根,浸润了西方文化。作为一个缺乏文化根基的黑人女性,接受了西方现代教育的吉丁自信干练的同时难免会感到孤独困惑。因此吉丁在纽约如鱼得水,与埃罗却格格不入,而儿子正好相反,荆棘丛生的埃罗让他有归宿感,现代化的纽约却让他手足无措。处于这样两极的他们相恋相爱了,却难相知相守。是黑白两种文化之间既相互对立又相互吸引的关系造就了儿子与吉丁之间这种矛盾的爱情。儿子与吉丁对教育、对工作、对埃罗和纽约的看法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反映的其实是非洲文化与西方文化这两种文化视角的差异。莫里森关于两种文化共存的前景在迈克尔·斯特利特,那个瓦利连和玛格丽特没露面的儿子所代表的倾向中体现出来。作为白人,迈克尔从来没有歧视过黑人文化,反而劝吉丁不要抛弃本民族的文化。他还深入到印第安人保留地去体验生活。在他看来,由单一的一种文化取代所有其他文化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各种文化都应有其存在的理由和空间。
吴金莲,内蒙古民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