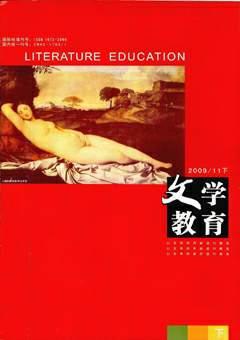《猎人笔记》在中国的研究现状与展望
叶 芳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这位人称“小说家中的小说家”的伟大现实主义作家,生活在上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他英勇地用笔刻下了那个时代的烙印,成为俄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是什么动力使这位浪漫的诗人转向尖锐而现实的小说创作呢,是时代的召唤和历史的变革。屠格涅夫的小说创作始于1847年,他在进步刊物《现代人》上发表了一篇特写《霍尔与卡里内奇》,这便是《猎人笔记》的开端,至此,他又连续在《现代人》上发表了二十篇短篇。1852年,他又增补了一篇,共二十二篇,出版了取名为《猎人笔记》的单行本。1880年,作者又增加了《且尔托泼哈诺夫的末路》、《车轮子响》和《活尸首》,共二十五篇,出版了最后定本的《猎人笔记》。这本随笔式的短篇集,使我们不仅领略了美丽清新的自然风景:“渐渐地小树林变昏暗了;本来昏昏欲睡的树梢上缓缓移来了晚霞的红光,红光如流水般滑过树根、树干、树枝最后到了树梢头……过了不多大一会儿,树梢上的红光也移走了,暗了下来;天空也慢慢地由红而蓝。林子里开始充斥着一种暖和怡人的润湿的空气,气息也不再清新如旧,而逐渐浓烈起来;风儿一吹到您近旁就会停住了。鸟儿们也开始分类分期地睡去,先是燕雀,再接着是知更鸟,然后是白鸟。林子里更黑了。”(《叶尔莫莱和磨坊老板娘》)更看到了19世纪四十年代沙皇尼古拉一世统治下的俄国,“希皮洛夫卡村的农民都是交代役租。宪法这样规定了——能有什么办法?不过他们交租金给我时却是一清二楚。老实说,我早有叫他们改交劳役租的想法,可只有这么点地!虽然这样我还是觉得奇怪,他们是如何度日的呀?话说回来了,这是他们的事。”(《管家》)无一例外,《猎人笔记》中的地主们总是一副闲适优雅的姿态,留着金色的大胡子,带着有教养的慈善家面具,压榨底层农奴,农奴们的脸上则布满忧愁和不满的神情,劳作,隐忍,屈身,他们住在荒芜的沼泽地里,黑暗的仆人房中,他们仿佛被这片黑色的土地吸去了灵魂和生命,根扎在泥土里,任劳任怨。据统计,仅从一八四五年至一八四九年短短的五年间,俄国各地先后就发生了一百七十二次起义和暴动。这是农民在觉醒、农奴制度处于崩溃的前夜。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写成了,通过对农奴社会的描写,以达到启发和惊醒世人的目的,是对俄国走向民主的召唤和引导。
20世纪初的中国处在内忧外患的动荡局面,抱着救国理想的一批有志青年开始将目光放在了海外,于是包括俄国文学在内的海外名篇开始被译介到中国来。起初,俄国文学的译介是从一批留日学者开始的,当时国内精通俄文的人才极少,许多作品诸如《上尉的女儿》(戢翼翚译)等都是日译中的形式被翻译到中国,鲁迅先生最早在阅读屠格涅夫《猎人笔记》的时候看的也是日文版。人们隐隐地从这位陌生的俄国作家身上看到了变革的曙光,和民主思想的闪光。1917年,由周瘦鹃编译,中华书局出版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中收入了屠格涅夫《猎人笔记》的一部分。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无疑使更多的中国人开始关注俄国文学,开始关注屠格涅夫,这为《猎人笔记》在中国的研究提供了背景前提,屠格涅夫成为了五四时期“俄国文学热潮”中译介最多的俄国作家。
1920年,沈雁冰,从“艺术方面”用“严格的眼光”挑选出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推荐翻译,1921年3月—1924年11月,耿济之在《小说月报》中翻译并连载了《猎人笔记》,并以此为基础在1936年3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最终审编后的《猎人笔记》,这是建国以前唯一的译本。值得一提的是,1922年,耿济之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猎人笔记研究》的论文。这是当时评论界研究屠格涅夫作品的第一篇论文,同时也是最有分量、多所创见的一篇论文。在这篇文章中,耿济之对《猎人笔记》中反农奴制的主题思想和文中运用的人物刻画法作了分析。
此外,在同一时期的鲁迅、沈端先也对《猎人笔记》所反映出来的民主斗争精神和“为人生”的思想境界做了简要评析,田汉、郁达夫、巴金、王统照等人则着意于《猎人笔记》文本本身的艺术特点和结构。胡先啸更是从“A human relic”(《猎人笔记》中的《活尸首》)看到了深刻的宗教色彩。
民国期间,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影响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如鲁迅、郁达夫笔下的“多余人”,他们大多善良脆弱,也曾对生活抱有希冀和热情,却在残酷的岁月中不断遭遇苦难,在失落中沉沦,这与《猎人笔记》中《西格雷县和哈姆莱特》里描写的“哈姆莱特”有着共通性。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也从《猎人笔记》中得到启示,在他笔下的大自然和人的灵魂和谐地陶冶在一起,人文、自然、生命浑然天成,既有历史的纵深感,又有现实的真切感,这与《猎人笔记》中自然描写所显示出来的历史感与现实感的统一是一致的。更重要的是《猎人笔记》中反映的民主思想更是带动了一批有志革命的中国人,成为当时中国资产阶级新文化的一部分。
建国以后,《猎人笔记》被完整翻译到中国的最早单本当属1953年文化出版社发行的,丰子恺译著的版本。1953年,丰子恺之女丰一吟翻译了诺维科夫的专著《猎人笔记鉴赏》(又名《论猎人笔记》)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后,丰子恺父女为《猎人笔记》在中国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与前提。至今,市面上流行的中译版《猎人笔记》已有不下30个版本,从这些数据中,我们看到《猎人笔记》在中国译介与研究在不断地扩展中。
前期编译和引进国外研究的还有,1986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高文风编译《屠格涅夫论》,1989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李兆林编《屠格涅夫研究》。经历一个世纪的沉淀,现今,国内对《猎人笔记》的研究也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主要研究学者有陈建华、李金、孙乃修、朱宪生等人,所涉及的领域也由原来传统的对主旨思想和艺术特点的分析,扩展到比较文学、政治历史学、生态学、语言学、叙事学、美学、修辞学等多领域、多角度、多方位的论述,主要论著有2007年重庆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陈建华),1988年学林出版社出版的《屠格涅夫与中国》(孙乃修),朱宪生《在诗与散文之间——论屠格涅夫的创作与文体》等。在中国期刊网上输入关键字:猎人笔记,可以搜索出相关论文98篇,这个数据一方面说明,国内对《猎人笔记》的专门研究已经引起重视,另一方面说明,《猎人笔记》的研究还有很大的剩余空间,等待我们去挖掘和开拓。
新世纪之初,学者杜昌宗意识到:“当代西方的文学批评已不再仅仅是单一的文本分析,它广泛吸收了政治学、语言学、历史学、精神分析、社会学、哲学、人类学、历史学、艺术史等学科的理论成果,变成了一种文化创造与再创造的活动,这种泛文化的文学研究立场是对所有被认为是自然的东西进行批判,因为一切自然的东西都可以视为历史和文化的营造。”(《跨学科文化批评视野下的文学理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可以说,一种文学的传统是受该文学赖以产生和发展的文化语境中的诸种因素制约的,因此它往往映照出这个民族的民族文化、民族心理和民族素养。《猎人笔记》中描述了许多具有俄罗斯文化特色的环境和场景,比如庄园文化、狩猎文化等等,都可以作为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由于俄罗斯独特的地域特征,东西方文化在这片土地上相互角力,文学的一个主要源头,就是从拜占庭传入的基督教文化,因此俄罗斯文学中具有明显的宗教色彩,相信命运,救赎,报应,这点在《猎人笔记》也不例外,如《死》中对死亡思考就带有深刻的宗教意味。可以从宗教学的角度解读《猎人笔记》。
在写《猎人笔记》之前屠格涅夫更大程度上应该是一名诗人,这使得《猎人笔记》有着一种独特的诗化的语言,它讲究韵律和节奏,这使得很多评论家都将《猎人笔记》比作音乐。在这方面的研究有1991年2月王加兴发表在《中国俄语教学》中的一篇名为《<猎人笔记>的语言风格》的论文,从语言学上研究《猎人笔记》无疑也是一个可靠的领域。
在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史上就有“心理流派”的说法,而对人物的内心世界作有力的刻划也就成为俄国文学的一个传统手法。屠格涅夫的心理描写,不仅在他的创作手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还具有独特的韵律。屠格涅夫认为:“诗人应当是一个心理学家,然而是隐蔽的心理学家;他应当知道并感觉到现象的根源,但表现的只是兴盛与衰败中的现象的本身。”(《古典文艺理论译丛》1962年第三期第185页)《猎人笔记》中屠格涅夫除了对“我”的心理刻画外,几乎避开了对他人的直接心理描写,但我们却能在文本中感受到不同人物的心理特征,屠格涅夫在这里十分高妙地借用人的行为和表情刻画心理。无论从心理学还是行为学的角度,《猎人笔记》都将成为很好的研究素材。
《猎人笔记》中不乏美丽、勇敢、善良的女性形象,如《叶尔莫莱和磨坊主妇》中勤快可人的阿丽娜,《活尸首》中美丽坚强的露克丽亚,她们是生活在那个黑暗时期的女性,脆弱却勇敢,我们看到阿丽娜争取婚姻权力的斗争,看到露克丽亚面对苦难的坚韧和善良,她们都是农奴制的祭祀品,结局是悲壮的,但她们勇于斗争的心已深入人心,《猎人笔记》中的女性形象也代表着女性意识的觉醒,从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分析《猎人笔记》不失为一个好途径。
屠格涅夫是一个自然描写大师,他笔下的一草一木都仿佛有着一颗灵动的魂魄,真实而美丽,《猎人笔记》不惜大量地着墨于对自然的描写,这激起读者对自然的崇敬和热爱之情,屠格涅夫的创作既是对自然的摹写,也注入了蕴含哲思的感悟,他眼中的自然万物都是人化了的自然,别林斯基评价说:“屠格涅夫笔下的大自然,是他所理解的大自然”。《猎人笔记》中的景都给人以真实的难受,作者屠格涅夫几乎能叫出所有树的名字,鸟的名字,即便是野草也不是无名的,这样的细致描写,提供了从自然生态角度研究《猎人笔记》的多种可能。
以上为《猎人笔记》在中国的研究做了简单的概括,并对其在新世纪的进一步研究做了六个领域的展望,针对新世纪文学批评的特点,研究《猎人笔记》可发散思维,多元化,多领域发掘,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猎人笔记》在中国的研究会取得新的突破。
参考文献:
[1]《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谢天振,查明建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版
[2]《三四十年代苏俄汉译文学论》,李今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版
[3]《屠格涅夫研究》,李兆林、叶乃方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版
[4]《屠格涅夫与中国》,孙乃修著,上海学林出版社1988版
[5]《鲁迅全集》,鲁迅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版
[6]《郁达夫文集》,郁达夫著,广州花城出版社1983版
[7]《巴金全集》,巴金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版
[8]《西洋文学通论》,茅盾著,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版
[9]《中国现代文学翻译版本闻见录》,张泽贤著,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版
[10]《在诗与散文之间——屠格涅夫的创作和文体》,朱宪生著,1999版
[11]《屠格涅夫评传》,普斯托沃依特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版
[12]《三四十年代苏俄汉译文学论》,李金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版
[13]《中国翻译文学史稿》,陈玉刚主编,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版
[14]《古典文艺理论译丛》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15]《<猎人笔记>的语言风格》王加兴《中国俄语教学》1991
[16]《<猎人笔记>艺术微探》冯羽《南京师大学报》1984第三期
[17]《猎人笔记》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6
[18]《跨学科文化批评视野下的文学理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叶芳,女,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