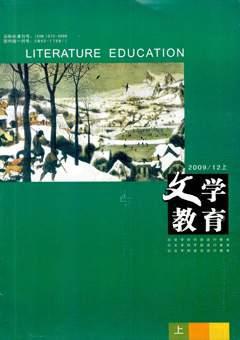性别话语视野下的《红楼梦》
陶芸辉 桑大鹏
在历史上,女性主义是从特定的各种历史条件下演化出来的,它作为一种抗议运动,起源于英国、法国和美国的西方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发起者是那些商人和下层贵族受过教育的妇女。两个世纪以来,世界经历了两次女性主义运动的高潮,关于女性主义的研究分析也通过这两次女性主义运动而日渐完善。伴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和女性主义理论的建立,在以福柯、德里达等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之下,形成了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者主张在妇女运动的内部实现一个“模式转换”,即:从只关注事物,到只关注话语。如果话语即权力,那么,对原话语的解构即是对原有权力的颠覆。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1],在拥有五千年历史的古代中国,统治阶级是君主帝王,而统治阶级的思想毫无疑问则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在儒家思想中,对于性别的规范性话语无疑来自于两方面:一是《周礼》、《礼仪》、《礼记》的“三礼”所确立的性别规范,即“男女有别”,这种性别规范以其权威性和经典性集体无意识地影响着古代中国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二是宋明程朱理学的性别理念,即“制欲”。从后现代角度来进行思考,我们不妨设儒家思想中这两种对于性别的规范性话语已经形成了“权力”,那么这个权力的组成模式是怎样的呢?
在西方,关于女性主义的研究思潮主要是从生物性别和社会性别两方面来进行讨论的。而在古代中国,男女除了按照生物性别和社会性别来划分之外,还按照阴阳来进行分类,大致的划分为:阴阳→男女有别(生物性别)→社会性别。
在这样的前提假设之下,《周易》里清楚地说明了男为阳女为阴,阳气主宰万物,阴气则顺从阳气,以调和万物,这个时候,阴阳只有功能上的差异,并无明确的位序上的尊卑。而当《周易》的阴阳论逐步过渡到儒家的“三礼”时,对立统一的“阴阳”演变成了“男女有别”。礼从西周开始典章制度化,周礼的核心是“亲亲”和“尊尊”,这种制度启动了男女、嫡庶之别,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以男系为本位的伦理系统,这种伦理系统是排斥和贬抑女性的。相对于之前的阴阳论,“三礼”所确定的性别规范有个最大的不同,即:男女有别。《礼记》记载:“男女有别,然后父子亲;父子亲,然后义生;义生,然后礼作;礼作,然后万物安。无别无义,禽兽之道也。”[2]到了明代,理学被定为官学,而理学中关于性别的主要观点即男尊女卑,“从一而终”是女性顺从的基本要求,并且衍生出许多其他要求,对女性应该拥有的女性气质进行推崇。相对于西方女性主义者所确定的女性气质:相互依靠、群体、联系、分享、感情、身体、信任、没有等级制、自然、内向、上进、欢欣、和平和生命等,古代中国父权制统治者所确定的女性气质还兼备中国五千年封建制的专制特点:顺从、守节、对男性无条件的服从等等,在福柯看来,我们虽然不是单纯由本能规划和驱动的,我们的想法和行为却在某种程度上收到这些不同的话语的影响、规范和制约,因此,古代中国的女性处于长期“失语”状态。那么造成这种“失语”的原因是什么呢?下面,我们以《红楼梦》为文本来进行分析。
一.《红楼梦》中的性别话语
《红楼梦》作为一本为女子立传、“闺阁昭传”的小说,其颠覆了之前才子佳人小说模式,并且,作为在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所创作的小说,曹雪芹处于一个古代中国女性地位完全确定的时期。这个时期,中国封建社会正走向衰落,手工业、小商业正处于发展阶段,女性地位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所以,我们不妨将《红楼梦》中的女性角色视为曹雪芹对之前数千年古代中国女性形象的总结,并且对未来女性气质可能出现的所有可能性所进行的一种探讨。
1.阴阳论在《红楼梦》中的体现
在《易经》中,乾道为男,坤道为女,乾元统天,坤元承天。这种传统观点也在《红楼梦》中体现了出来,第三十一回《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双星》中,史湘云就与丫头讲解过阴阳:“天地间都赋阴阳二气所生”、“阴阳顺逆”、“走兽飞禽,雄为阳,雌为阴;牝为阴,牡为阳”。红学家根据标题“因麒麟伏白首双星”猜测史湘云和贾宝玉在四大家族没落后结为夫妻,其真实性有几分我们暂且不作讨论,但是从现行版本中我们可以见到史湘云的结局:新婚不久,夫婿痨病,基本是在捱日子,如果夫婿不死,相当于在守活寡,如果夫婿死了,那就守寡了,“终久是云散高唐,水涸湘江”。对于一个接受古代传统教育、恪守礼教的大家闺秀来说,史湘云熟知阴阳论实属情理之中,她的命运也定位于“承天”,即顺从夫婿,守寡抑或守活寡是史湘云在封建礼制下大家闺秀正常的生活轨迹。
2.生物性别在《红楼梦》中的体现
以《周礼》、《礼仪》、《礼记》的“三礼”所确立的性别规范“男女有别”,我们可以视为古代中国对生物性别的认知并加以限制的制度:“非祭非丧,不相授器。其相授,则女受以筐,其无筐,则皆坐。莫之而后取之。内不共井,不共浴,不通寝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装,内言不出,外言不入”,[3]这种男女有别、授受不清的观点可谓根深蒂固地影响着古代中国女性,我们来看看《红楼梦》中所体现的这种观点。
在第三回《贾雨村夤缘复旧职 林黛玉抛父进京都》中,林黛玉曾这样对王夫人说:“我来了,自然只和姊妹同处,兄弟们自是别院另室的,岂得去沾惹之理?”
在第二十五回《魇魔法姊弟逢五鬼 红楼梦通灵遇双真》中,当贾府男男女女所有人涌进大观园看发疯的贾宝玉时,薛蟠的表现很能反映古代女性的生存状况:“别人慌张自不必讲,独有薛蟠更比诸人忙到十分去:又恐薛姨妈被人挤倒,又恐薛宝钗被人瞧见,又恐香菱被人臊皮”。因为男女有别,大家闺秀足不出户,所以,薛蟠保护薛宝钗不被其他男性,甚至是自己亲族内的男性看见实属情理之中的行为。
在第三十四回《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错里错以错劝哥哥》中,贾宝玉因“在外流荡优伶,表赠私物,在家荒疏学业,淫辱母婢”之罪被贾政笞挞之后,袭人与王夫人讲解大道理时提到了“如今二爷也大了,里头姑娘们也大了,况且林姑娘宝姑娘又是两姨姑表姊妹,虽说是姊妹们,到底是男女之分,日夜一处起坐不方便,由不得叫人悬心,便是外人看着也不象”,这番话让王夫人“如雷轰电掣的一般”,甚合心意,袭人从此也深得王夫人喜爱,暗地将其定为了宝玉的屋里人。
3.社会性别在《红楼梦》中的体现
激进女性主义者始终强调:性/社会性别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本原因。她们中的很多人认为,性/社会性别差异与其说是出自生物原因,不如说是出自“社会化”过程,或者说是“出自作为女人在父权制社会存在的整个历史”。但是,至今女性主义者并未对如何铲除性别歧视达成一致的共识。
在《红楼梦》第四十二回《蘅芜君兰言解疑癖 潇湘子雅谑补余香》中,薛宝钗对林黛玉说:“所以咱们女孩儿家不认得字的倒好。男人们读书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读书的好,何况你我。就连作诗写字等事,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内之事。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只是如今并不听见有这样的人,读了书倒更坏了。这是书误了他,可惜他也把书糟踏了,所以竟不如耕种买卖,倒没有什么大害处。你我只该做些针黹纺织的事才是,偏又认得了字,既认得了字。不过拣那正经的看也罢了,最怕见了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一席话,说的黛玉垂头吃茶,心下暗伏,只有答应“是”的一字。在第四十五回《金兰契互剖金兰语 风雨夕闷制风雨词》中,林黛玉对薛宝钗教育她的大道理做了这样的回应:“从前日你说看杂书不好,又劝我那些好话,竟大感激你。往日竟是我错了,实在误到如今”。对于从不勉强贾宝玉理仕途经济,并且尖酸刻薄的林黛玉,在面对薛宝钗教育她要“只该做些针黹纺织的事才是”时心里“暗伏”,并且大感激她,古代中国对女性角色和女性气质的定位一目了然,对贵族的大家闺秀依然要求“不识字”、“针黹纺织”,而对男性又不一样了,“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礼记》记载:“男不言内,女不言外”,[4]因此,从符合封建礼教道德规范的大家闺秀薛宝钗口中说出的这番关于男女该如何定位的话,又得到了封建道德规范的叛逆者林黛玉的认同,我们可以知道,这种观念已经根深蒂固,而且是符合封建正统的“大道理”。
二.关于《红楼梦》中性别话语的讨论
在铲除性别歧视方面,各派女性主义者持不同的意见:
弗里丹则认为只有社会像重视“男性气质一样”重视“女性气质”,妇女才能和男人平等。
米利特盼望的是一个雌雄同体的未来,她渴望一种文化的整合,能够把分离的男性气质的亚文化和女性气质的亚文化结合为一体。但同时她坚持认为,这种整合必须谨慎进行,要对所有的男性气质特征和女性气质特征做出彻底评估。关于雌雄同体,米利特推论说,只有在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分别都是有价值的情况下,把这些气质特征结合到雌雄同体的个人素质里,这才是有价值的理想模式。
费尔斯通认为,仅仅在性/社会性别制度方面做保守的改良是不够的,应该进行更有力的变革,这才能使妇女和男人的性摆脱生物学的生殖动机,使妇女和男人的人格从社会建构的、强求一致的所谓“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的监狱里解放出来。
戴利则坚持,摆脱男人建造的女性气质,妇女将会显示出她们原初的女性力量和美。她还明确地否定了雌雄同体的人这一理想,她作为理想提出来的是“狂野的女性”,这样的女性超越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而存在。要成为完整的人,女人必须摆脱虚假的身份——父权制为她建构的女性气质。那时,也只有在那时,她才能把自己作为自我来体验,那是犹如她生活在母权社会而不是父权社会将会具有的自我。
通过各女性主义者的观点,我们总结下来,对于如何消除性别歧视,实现男女平等,主要有以下三个途径:①男女气质整合的雌雄同体;②以男性气质为参照标准的女性气质;③高于男性气质的女性气质。但是,究竟哪个途径是可行的,现在还没有一致的看法,那么,我们就以《红楼梦》中的人物对这三种途径在古代中国的可行性做一个探讨。
1.男女气质整合的雌雄同体
在男女气质整合的过程中,需要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但是,这种动态平衡的临界点在哪里,我们暂时给不出一个定论,那么如果我们给这种动态平衡给不出一个临界点的话,在整合的过程中就有可能出现两种情况:
(1)具有男性气质的女性
在《红楼梦》中,具有男性气质的典型女性是王熙凤,在第二回《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中,冷子兴曾这样评价过王熙凤:“说模样又极标致,言谈又爽利,心机又极深细,竟是个男人万不及一的。”王熙凤就是这样的一个综合体,一方面,她“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起笑先闻”美丽的容貌满足了男性的审美和欲望。另一方面,“聪明过了”的王熙凤却让男性感到畏惧。作为当家人,王熙凤精明干练,具有自主性,并且具有一定的管理能力,而这些特点一般是与男性相连的,因此,男性对王熙凤的评价我们可以从贾琏的小厮兴儿口中窥知一二:“奶奶的心腹我们不敢惹,爷的心腹奶奶的就敢惹。提起我们奶奶来,心里歹毒,口里尖快。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一脸笑,脚下使绊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都占全了。”具有男性气质的王熙凤让男性惧女性怕,并且,这种男性气质并不容于当时的主流社会,所以,无论王熙凤最终的结局是被休回家还是早逝,都是情理之中的,因为,在古代中国,在男性话语里,三从四德是女性最基本的美德,王熙凤的悲剧性结局证明了具有男性气质的女性是不能被男性和主流社会所接受的,顺者昌逆者亡,王熙凤不能顺从,就只能死亡。
(2)具有女性气质的男性
毋庸置疑,《红楼梦》里具有典型女性气质的男性是贾宝玉,贾宝玉的外形是“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面如桃瓣,目若秋波。虽怒时而若笑,即视而有情”,而这种外形,一般是用来形容女性的,在第三回林黛玉第一次见贾宝玉中作者给出了贾宝玉这样的外表,就垫定了贾宝玉外形上女性气质的一面。
“且说宝玉自进花园以来,心满意足,再无别项可生贪求之心。每日只和姊妹丫头们一处,或读书,或写字,或弹琴下棋,作画吟诗,以至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无所不至,倒也十分快乐。”从贾宝玉进入大观园的所作所为,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与女性无异的男性,对于这种多愁善感的气质、厌恶功名利禄、喜爱女性物品、没有等级观念等等在父权制话语下妇女应该具有的品质。贾宝玉显然是个异类,被大家视为“混世魔王”。显然,他并不能被主流话语所接受,安排出家应该是贾宝玉最顺理成章的结局,原因有二:其一,贾宝玉具有了女性气质,那么他肯定要被排斥于主流社会之外,悲剧性的结局不可避免;其二,不管怎样,古代中国男性地位始终高于女性,因此,贾宝玉不可能像具有男性气质的王熙凤那样以死亡来祭奠封建礼制,出家成为了他最好的结局,给他留下了一条生路,即使这样,我们也可以看到,社会对男性的宽容是高于女性的。
2.以男性气质为参照标准的女性气质
在我们对这个途径的探讨中,我们选择《红楼梦》中的探春,在第五十五回《辱亲女愚妾争闲气 欺幼主刁奴蓄险心》中,探春对赵姨娘说:“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业,那时自有我一番道理”。探春是有理想、有抱负的,作为庶出的女儿,是“老鸹窝里出凤凰”,探春是美丽的,“削肩细腰,长挑身材,鸭蛋脸面,俊眼修眉,顾盼神飞,文彩精华,见之忘俗”。她的美丽让男性心动,贾琏的小厮兴儿说出了男性的看法,“三姑娘的浑名是‘玫瑰花,玫瑰花又红又香,无人不爱的”。探春是聪明的,连王熙凤也称赞“她虽是姑娘家,心里却事事明白,不过是言语谨慎;她又比我知书识字,更利害一层了”,她在大观园里面兴利除宿弊,却连尖酸刻薄的林黛玉都对她赞赏有佳:“三丫头倒是个乖人。虽然叫他管些事,倒也一步儿不肯多走。差不多的人就早作起威福来了”。探春是个典型的大家闺秀,知书识礼,言语和顺温柔,但是,“才自精明志自高”并不符合男性话语维度下的女性标准,虽然她美丽,无人不爱,但是“只是刺戳手”,无人敢摘。探春渴望自己是个男人,这样就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众人看到她的能力而忽视她庶出的身份,但探春毕竟不是男人,对于她这种不安于女性的行为,是不能被当时的主流社会所接受和认同的,“远嫁”的结局正说明了探春的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是遥远的,而以男性气质为参照标准的女性气质在古代中国可以说是海市蜃楼,可望而不可及。
3.高于男性气质的女性气质
在《红楼梦》中,基本符合这一标准的女性是尤三姐。和贾琏贾珍吃饭,尤三姐能够“自己高谈阔论,任意挥霍撒落一阵,拿他弟兄二人嘲笑取乐,竟真是他嫖了男人,并非男人淫了他。一时他的酒足兴尽,也不容他弟兄多坐,撵了出去,自己关门睡去了”。她是狂野的女性,她敢对贾琏贾珍直接说不:“这会子花了几个臭钱,你们哥儿俩拿着我们姐儿两个权当粉头来取乐儿,你们就打错了算盘了”。就连贾珍贾琏弟兄两个本是风月场中耍惯的,不想今日反被这闺女一席话说住。尤三姐美丽但是风流,不为礼教所缚“尤三姐天生脾气不堪,仗着自己风流标致,偏要打扮的出色,另式作出许多万人不及的淫情浪态来,哄的男子们垂涎落魄,欲近不能,欲远不舍,迷离颠倒,他以为乐”,尤三姐的形象完全悖逆了传统女性形象,那些文化上与妇女相联系的价值和美德几乎没在她的身上有任何体现,这种压制于男性的气质在古代肯定会被视为洪水猛兽,除之而后快,因此,尤三姐最终自刎,我们将其视为父权制下,尤三姐以死来祭奠主流社会话语的象征。
在性别话语的角度下,我们将重新获得对人的研究、对历史的研究和对文本的重新阐释。《红楼梦》大致写作时间为康熙48年至乾隆9年,即1744年至1754年之间,这个时期,正是西方女性主义开始萌芽、女性意识开始苏醒的时期,而清朝也是中国封建社会走到顶峰并走向末路的时期,这个时期,束缚中国女性的封建礼数基本已至顶峰,三从四德、三纲五常、一夫多妻、守节、童养媳、缠足等等条例和习俗已在社会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影响,《红楼梦》中各种女性形象应该是为之前的妇女形象做一个总结。但是,性别话语研究迄今为止各方观点各有不同,相信随着理论更深入的发展,研究更加的细致,我们会对《红楼梦》中的女性形象再有更深的认识。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
[2][4]梁鸿.《礼记》编选.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
[3]J·丹纳赫.《理解福柯》.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陶芸辉,三峡大学文学院文艺学08级硕士研究生;桑大鹏,三峡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