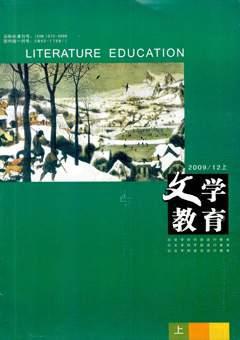论张爱玲小说的道具设置
郭 云
1966年,张爱玲在美国改写旧作《十八春》并异名为《半生缘》。由于《半生缘》中道具设置密度大、数量多,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具有代表性,本文以《半生缘》中的道具设置为例,分析张爱玲小说的道具设置的艺术作用,并进而探讨张爱玲道具意识的形成原因及其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
道具首先是戏剧术语,指出现在舞台上的物件。运用于小说艺术中,主要指作者刻意设计的具有特定艺术作用的物件。在这里,有必要明确一下道具与意象的区别。意象主要指凝聚了作者思想感情的“象”,是小说重要的内容构成,意象中的意和象不能剥离,张爱玲小说中的典型意象,如月亮、镜子、太阳、老宅、竹帘等的研究已相当成熟;而道具只要能实现在小说中的功能,是可以被替代的,如《金锁记》中的核桃、《小艾》中的字模、《色戒》中的钻戒等。当然,意象与道具有时也会重合,比如《封锁》中的电车,既是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意象,又是一个使人物暂时脱离其日常生活环境的道具。本文把作者对物的功能性使用称为道具设置。道具在小说中存在的意义除与人物、意象、物象等一起构成“现实”幻觉外,更主要地体现在小说的形式构成方面。
在《半生缘》的创作中,张爱玲使用了大量的道具,而这些道具对《半生缘》的人物塑造和故事叙述有很大的影响。在《半生缘》中,红手套、筷子、灰绒线背心、热水瓶、红宝石戒指、紫色旗袍、酒、狗、火腿、信件等道具出现在不同的人物关系之间,发挥了特定的艺术作用。
红手套、筷子、灰绒线背心、热水瓶、红宝石戒指构成了一组具有共同艺术功能的道具,就这些物在小说中的使用目的来看,它们都与曼桢与世钧的爱情相关。红手套第一次出现是在书中的第一章,世钧初见曼桢,“手上戴着红绒线手套……”书中第一号的女主人公是和红手套一起出场的。曼桢将叔惠的筷子放在茶杯里涮了涮,替他架在茶杯上,顺手把世钧的也拿过来洗好,世钧接过来,却依旧搁在油腻的桌面上。作者通过一双筷子写出了世钧眼中的曼桢的殷勤体贴,与世钧的“见到女人总有点拘束”。红手套的一只在三人外出照相时遗失了。世钧在放工后的黄昏,“也不知道是怎样的一种朦胧心情”使他打着手电筒,冒雨在当初拍照的两棵大柳树下,找到了那只红手套。红手套在这里是个标志,标志着“只笼统地觉着她(曼桢)很好”的世钧对曼桢的微妙、朦胧的情感,也暗示两人的关系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半生缘》中的人物关系彼此是不透明的,人物在感情上都非常的含蓄、内敛。如果说红手套是世钧自己都莫名的心意表达,而灰绒线背心则是曼桢对世钧情意的委婉暗示。第三章,曼桢想给世钧织一件背心,却先为叔惠织了一件,看在叔惠母亲的眼里,是“灰绒线上满缀着雪珠似的白点子”。曼桢示爱的矜持,要依赖读者在阅读时进行创造性的填充和发现。在世钧与翠芝结婚之前,看到叔惠穿着和他一模一样的那件灰绒线背心,“世钧的那一件他久已不穿了,却不能禁止别人穿”。作者借助一件毛衣,使人物心理的呈现含蓄蕴藉。世钧第一次回南京的前夕,曼桢帮世钧理箱子。当爱情来临时,世钧恍惚的心情通过一个热水瓶得到了深层的刻画。“这只热水瓶,先是忘了盖;盖上后,又忘了把里面的软木塞上。”红宝石戒指是两人爱情关系确定时期的信物。第十章,世钧送给曼桢一枚红宝石戒指。第十一章,世钧因为家人隐约知道曼桢其姐为舞女的家世,要求曼桢搬家。曼桢将戒指还给世钧,世钧赌气把它扔进纸篓。第十二章,曼桢被祝家幽禁,将戒指押给佣人阿宝,求她送信给世钧,阿宝把戒指交给曼璐。曼璐则将计就计,谎称曼桢已嫁给豫瑾,把戒指退给世钧。世钧对曼桢彻底死心,回南京后不久与对叔惠失望的翠芝因同病相怜而仓促结婚。作为一个贯穿性的道具,红宝石既是爱情信物,又推动了故事情节继续发展。红手套、筷子、灰绒线背心、热水瓶、红宝石戒指构成了一组道具,见证了曼桢与世钧的爱情的萌芽、发展、确定与结局。这些与人物息息相关的物,既标志了人物之间的关系,揭示了人物的深层心理,又见证了人物的命运,推动了故事情节继续向前发展。
因父亲去世,曼璐为了家庭做了舞女。曼璐主动与未婚夫豫瑾解除了婚约,豫瑾七年都没有结婚。第八章,豫瑾到上海见到曼桢,豫瑾不觉将感情移到曼桢身上。曼璐穿着紫绒旗袍去看豫瑾。紫色衣服在这里有特殊的含义。“从前,她有件深紫色的绸旗袍,他很喜欢她那件衣裳”……“豫瑾有一个时期写信给她,就称她为紫衣的姊姊”。紫色衣服联系着两人相恋的美好时光,曼璐喜欢紫色。买衣料时,赌气买紫红色的而非伙计推荐的深蓝色布料,潜意识里大概还是因为豫瑾很喜欢紫色衣服。而看到“一个穿着紫色丝绒旗袍的瘦削的妇人”的豫瑾,“一颗心直往下沉”,“想想从前的事,非常幼稚可笑。”因曼璐的巨大变化而受到强烈刺激的豫瑾以自卫的姿态否定了对曼璐来说是最美丽的回忆。曼璐“身上穿的那件紫色衣服,顿时觉得芒刺在背,浑身都象火烧似的。”作者借紫色衣服这一往昔爱情的记号,准确地描写了当爱已成往事时,昔日恋人之间错位的尴尬情感,深入准确地进行了人物心理刻画,同时极大地节约了叙述的篇幅。作者在《红楼梦魇》的自序中写道:“我大概是中了古文的毒,培根的散文最记得这句,‘简短是隽语的灵魂,不过认为不限隽语,所以一个字看得有斗大,能省一个也是好的。”[1]一件紫色衣服帮助作者达到了“经济和准确是艺术最高的道德”[2]的境界。作者并没有到此为止。第十一章在曼璐设计诳曼桢探病留宿祝家时,顾母惦记着曼桢明日要参加豫瑾的婚礼,“你问姊姊借件衣服穿,上次我看见她穿的那件紫丝绒旗袍就挺合适。”完全无心的一语却具有直刺曼璐之心的效果,也坚定了曼璐设计陷害曼桢的决心。而小说与台灯是曼桢借给豫瑾的。曼璐看到豫瑾房中的小说与台灯,误会曼桢对豫瑾买弄风情。“曼璐真恨她,恨入骨髓”,从而推动了情节的进一步发展,曼璐设计,将那“借腹生子的”阴暗的想法变成了现实,从而彻底毁了曼桢与世钧的爱情。
叔惠和翠芝的恋情对小说中其他人来说是个秘密,只有两人心知肚明。叔惠和翠芝各自的婚姻不幸,可以部分地归因于两人之间没有实现的爱情。较之其他人,叔惠在作品中的形象不够立体,他与翠芝的恋情也主要是从侧面进行描写的。作者写两人的隐秘感情,仅仅写了叔惠和翠芝的三次单独相处。对读者而言,叔惠对翠芝的感情由隐至显,则是通过叔惠的三次饮酒得以揭示。第六章,叔惠听说翠芝和一鹏订婚。“叔惠心里那块东西,要想用烧酒把它泡化了,烫化了,只是不能够。”第十三章,在翠芝与世钧的婚礼上,叔惠那桌“也许因为有他,特别热闹……叔惠豁拳的技术实在不高,结果他喝得最多。”有些借酒麻醉自己的意思。第十六章,叔惠回国,翠芝与世钧请他吃饭。“叔惠是在别处吃的半醉了的,也许是出于自卫,怕跟他们夫妇吃这顿饭”。叔惠心中爱着翠芝,却不肯正视自己的情感,始终采取逃避的态度,通过他的三次饮酒,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
作者也用了几个出色的道具含蓄地揭示了世钧与翠芝婚姻的真实状态。第四章,翠芝家的那只狗新近生了一窝小狗,要送一只给世钧的侄子小健。而翠芝知道“如果世钧常住在家里,我就不便送狗给你们了,世钧看见狗顶讨厌了”。在两人结婚后,翠芝仍养了一只狗。狗咬了小健,是小健不好。而叔惠归国后要来世钧家,那狗则被拴在亭子间了。世钧在曼桢家吃饭的次数多了,顾太太是知道他的口味的。“楼梯还象前天一样,搁着个煤球炉子,上面一只砂锅咕嘟咕嘟,空气里火腿的气味非常浓厚”。世钧是爱吃火腿的。在婚后十几年后,翠芝用不相信的口吻说:“你爱吃火腿,怎么从没听你说过?”世钧厌恶的,世钧喜欢的,作为妻子的翠芝都没有放在心上。而当年世钧从南京回到上海,看到曼桢正在写信给他。那半封信不知为什么没有被销毁。14年后,成为触动世钧回忆曼桢的契机。翠芝无意中发现了这半封信,用当时流行的话剧腔念给世钧听,“世钧差点没打她”。世钧心中关于曼桢的角落是不容侵犯的。翠芝从来都没有走进世钧的心中,反之亦然。世钧与翠芝的无爱的婚姻真相,在几个哑巴物件的见证下,昭然若揭。
除以上一定人物关系之间的道具的设置外,张爱玲尤其擅长写女人的服饰。曼璐那件印上“一只淡黑色手印”的苹果绿软缎长袍”画龙点睛般地刻画出了一位已经过气的风月中人。曼璐结婚后,不再用蓝布罩袍自卫的曼桢的那件“粉红底上印着绿豆大的深蓝色圆点子”的短袖夹绸旗袍,让世钧眼前一亮,感觉她像“陡然脱了孝一样”。翠芝第一次出场时,知道世钧的母亲有撮合她和世钧之意,身上的蓝色罩袍的“袍叉里微微露出里面的杏黄银花旗袍”,写出时尚小姐的矜持自重。衣服在《半生缘》里充当了揭示人物身份、心理与情绪的重要道具。
综上所述,道具在《半生缘》的艺术作用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首先是以物写人,通过道具的设置,呈现人物之间的微妙关系,揭示人物的深层的隐秘心理。其次是以物写事,道具推动了故事情节继续向前发展,巧妙地参与了故事的叙事,如红宝石、紫色衣服等。最后是构成了小说含蓄蕴藉的美学风格,物件虽无言,在作者一支妙笔的驱使下却可以充分表情达意。由于借物抒情,红宝石、灰绒背心、信件等既表现人物的感情,又有前后对应、使人物睹物生情,人物情感因此而意味绵长、深厚。这些小说人物的生活中的物件也因此具有了美学功能和审美价值。道具,这些哑巴物件,在小说中被赋予了生命,好像可以开口说话。如果没有这些道具的设置,《半生缘》在故事构成和人物描写方面都会受到颠覆性的影响。道具设置构成张爱玲小说技巧的一部分,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作品总是技巧介入的产物,而技巧必须有一个主体在操作与使用。“一种小说技巧总与小说家的哲学观点相关联。批评家的任务是在评价小说技巧之前首先找出他的哲学观点。”[3]张爱玲对道具的使用,表现出重呈现而非讲述的叙事特征,也体现出对生活持旁观的独特的“张看”姿态。
《半生缘》中明确的道具意识,不能排除《红楼梦》等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中国古典小说善于对物进行功能性的使用。《红楼梦》中巨细蘼遗的对服饰、物件的描写与运用,例如周瑞家送的宫花,浪荡子贾琏的九龙佩,宝黛之间的旧帕子等,应该对熟读《红楼梦》的张爱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另外,在《半生缘》写作之前,张爱玲创作了《未了情》、《太太万岁》两部电影剧本。电影剧本要求视觉化的思维方式,而可见的物是电影叙事、写人的重要手段。而由四十年代末的《十八春》改写的《半生缘》,明显具有电影思维的痕迹。根据李泽厚的概括,现代文学以启蒙、救亡为主流,而历史的机遇使救亡压倒了启蒙。谢有顺在谈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局限性”时,认为“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基本上都徘徊于种族、国家、乡土及家族的命题之中”[4],小说家忙于对世界发言,说什么比怎么说更重要,因此其文学文本感情与思想的浅露、内容大于形式、技巧粗糙等症状也就不可避免。而张爱玲在《半生缘》的写作中,上承中国古典小说对道具的使用,不着痕迹、独具匠心地使用了各种道具,通过道具揭示人物关系,推动故事情节的进展,人物之间的感情呈现因此含蓄厚重,那不动声色、冷眼旁观的叙事声调,给人以独特的宿命般的现实感。从而既保持了与中国古典小说的连续性,也参与造就了张爱玲在现代小说史上的独一无二。早在1944年,傅雷先生就发现了张爱玲的“天分和功力”。同时他也认为“技巧对张女士是最危险的诱惑”。[5]不过,张爱玲在《半生缘》中的那些有表现力的道具设置是恰如其分的。我们看不到作者滥弄技巧的痕迹,而不得不对张爱玲的“天分和功力”再次惊叹。
参考文献:
[1]张爱玲.红楼梦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2]李健吾.咀华集·咀华二集[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3]萨特.萨特文集·文论卷[C].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谢有顺.重塑灵魂关怀的维度——构建一种新的文学伦理[N].文汇报.2005-7-31
[5]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A].中华文学评论百年精华[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郭云,女,淮海工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