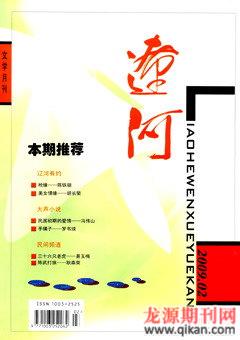陈武打狼
耿森荣
整个涧横村就像一只灰不愣登的大麻雀,落在太阳沟的沟沿边上,挤挤挨挨地住着那么五六十户人家,却是北山里头数一数二的大村子。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涧横村因狼多而闻名太阳沟里里外外,而陈武,又因擅长打狼让涧横更加闻名。
陈武,就是陈耀先他爹,靠打狼的技艺给儿子挣下了近一辈子的村长。那时候,狼比土匪可怕,土匪二秃子不过要钱要粮要女人,狼直接就要人命,都不带商量的。天刚一擦黑,家家户户便院门紧闭,熄灯安歇,相互之间再不敢瞎串,冷寂寂的,全村像死绝了一般,顶玄的是,老七家养活了一群羊,用胳膊粗的木桩子结结实实地圈了羊圈。弟兄几个轮流下夜看守,应该是万无一失了吧?可某夜,月黑风高,竞叫狼不知采用怎样的手段,神不知鬼不觉地开了圈门,拿尾巴当鞭子,一个不剩地赶上了山。天明村人结伴去寻,在后沟的土窝子里,终于发现了残留的羊头羊腿,白骨随处散落,一片狼藉。至于谁家的孩子或者老娘一不留神葬身狼口,只余一只小鞋半拉头巾留个念想的故事,屡见不鲜。
陈武,精壮汉子,粗短身材,一身筋肉疙疙瘩瘩,出手更是干净利落。村里的后生想摁倒他,没有三个五个那是门儿也没有。陈武打狼不用猎枪,也不拿棍棒,赤手空拳,稍有武松风范。
別人砍柴锄地,相互拨工,成群结伙,以防万一。陈武不,从来独来独往,如旧贪黑起早,艺高人胆大。往往用不了半月,准能拖一条狼回来,洒一路狼血。狼肉没人吃,怕长狼心狗肺,据说味道也不好,陈武就剥了狼皮,做褥子,做帽子,做皮袄,用不了就送给亲朋族人。那几年,涧横村谁家没有几件狼皮制品,其实都是陈武送的。
涧横村出了个陈武,哪一年打狼也够三二十条,可狼似乎不见少,看来死的还是没有生的快。狼多,也许正应了乱世之兆。
老村长死了以后,大伙纷纷推举陈武,陈武就应了。其中有好事者说,陈武,你会打狼,可我们谁也没有亲眼见过,这样,你当众打一回,村长的位置叫你家世代承袭。好多人跟着起哄,话赶话,陈武也就应了。
一日午后,村人都藏身在太阳沟中间的观音洞,远远地看着,陈武一个人就下到了沟底。沟底平,展生生一块,也是狼经常出没的地方。
陈武仰面朝天躺了,像睡着了一样稀松平常,后秋的阳光送来一些难得的暖意。往日是怕狼来。今天却盼着狼来,村人心里都痒酥酥的,像孩子盼过年一样。可一连两天,大伙连一根狼毛也没有看着,到傍晚,都只好悻悻地回了家。
第三天,陈武刚躺下工夫不大,远远地,便有一狼踽踽独行而至,耷拉着一条长尾巴,蔫里巴叽的,和一条大狗差不多,毛色微微发些红,却不光亮,疙里疙瘩的,有经验的人说,老狼。老狼老远就看见了死尸一样的陈武,照直跑过来,村人都为他捏着一把汗,这样不做准备的逆来顺受,哪如拉开架势的对打,不管死活总还显得轰轰烈烈一些。
在寓陈武一丈远的地方,老狼反而站住了,先提着鼻子闻,一副犹疑不定的样子,并没有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猛地扑上去。看陈武没有动静,老狼开始绕着陈武转圈,和推磨似的,转了一圈又一圈,好像在寻找下口的地方,陈武却和睡在自家炕头上一样自在,看也不看一眼。突然,狼伸出后腿,屁股朝里,往陈武身上刨土,细细的土面子顺风扬出去,打远处看,一片狼烟。
可陈武还是不动,任凭尘土把自己埋个灰头土脸。不见陈武反应,老狼发了一会儿呆,然后好像想起了什么似的,就在陈武腰间跳来跳去,来来往往再三。这下,村里人可真长了见识,狼吃个人还有这么多仪式啊。忽地,只见陈武猛一起身,不知什么时候两只手已抓牢了狼的两条后腿,一拧一撇一摔。背口袋一般,狼竟死挺挺地不动了,好多村人还没有看明白,战斗已告结束。等大伙跑下来,嘿嘿地笑着。看见陈武正抓起狼皮擦胸口上的污物,原来,老狼一着急,拉了陈武一脯子稀汤屎,逗得大伙又是一阵大笑。
村人簇拥着陈武回到村里,对陈武的绝技佩服得五体投地,作为村长,是没有一个不服的。
可是没几天。陈武的胸口开始发痒,起红斑,挠破了红斑,皮肤就一层层的溃烂,遍寻当地医者,却无人能识此病,更不用说医治。卧床百余日,竟一命归天,由陈耀先扛着白幡发了丧。村里人无不叹息。
大伙倒也讲信用,让陈耀先一个小屁孩当村长,一直当到土地改革。可对陈武的死因,人们莫衷一是,说法颇多。倒是后来有一白须长者途经涧横,说得让大家比较信服,老狼的一泡稀屎,那是老狼的绝命一击,最毒不过,是修行多年的得道狼特有的损招,陈武因此而命丧。
可是说来也奇,自从陈武死后,大阳沟一带再不见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