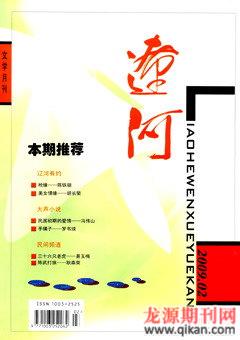枪缘
陈铁骊
一
从小听俺爹说,俺家老辈儿就喜欢枪,尤其俺爷爷,把枪玩到了极致。夸张一点说,那时要有“枪艺”吉尼斯,准没別人的。老人们都说,如果俺爷爷活着,保不准俺们家也是将星闪烁咧。
自莫言的《红高粱》问世以来,很流行写爷爷奶奶。俺也想写写俺爷爷,倒不是赶这个时髦,也缺乏写小说的天赋,俺只想随心所欲地写写俺们家与枪的缘分。
俺爹说,写恁爷爷,就要先写俺爷爷,因为没有俺爷爷就没有恁爷爷。想想也是这么个理儿,那就先说说俺们家老太爷吧。老太爷姓鲍,原籍山东,上世纪初。孤身一人来关东闯荡,走过私、淘过金、盗过墓、贩卖过大烟膏子,后来实在没啥整了,干脆上山当了胡子,据说干过“炮头”(匪语:带兵打仗的头目),手使双枪,一手好枪法。
从俺们家后来的发展看,老太爷的“原始积累”是否血腥,已无从可考。但自金盆洗手后,他就把全家接到了东北,将全部精力倾注于维系家庭的发展和对财富的聚敛上。都说老太爷办事果断。雷厉风行,也就十几年的工夫,俺们家所拥有的积蓄和田产竟有了空前的发展。
俺爷爷就是在这样一个殷实家境中长大的独苗苗。那时候,孩子刚懂事时都兴“抓周”,就是在炕上摆些物件,孩子抓到什么就预示着将来在这方面准有出息。俺爷爷每次都喜欢抓老太爷那杆枪。老太爷高兴地说,小兔崽子,行!像老子的种。不过。咱不干“一人一马一杆枪,好吃懒做人大帮”的马贼,要当带兵打仗、精忠报国的将军。
为了实现这个宏伟蓝图,俺爷爷四岁时就请了私塾先生,整天教那些《三字经》,大点儿开始背诵《论语》、《道德经》什么的,再大点儿,老先生突然卷铺盖,拜拜了。说这小子心忒野,虎巴叽的就知道舞枪弄棒。
的确,俺爷爷打小喜欢枪,10岁开始摸枪。老太爷不许任何人碰他的双枪,但俺爷爷是他的掌上明珠,整天跟着他在子弹堆里滚,还学会了骑射,十七八岁时,真就练成了飞马百步穿杨的硬功夫。文革时《智取威虎山》风靡全国,坐山雕一枪打灭一盏灯,杨子荣一枪灭俩,俺爹说,不是吹,要是恁爷爷,起码一枪灭仨。老人们说,俺爷爷能“枪打双飞”、“十步装枪”,还能“两腿装弹”。
一年秋天,有家大户要卖地,开价3500块大洋。经过讨价还价,3000块成交,但条件是要现钱。老太爷很大度,说人到了卖地的地步,一定有急用,咱就成全人家吧。于是,写完文书契约,老太爷拽出一张3000块大洋的银票,甩手给了卖地人。
那年月,拿出3000块大洋眼都不眨,和现在写张支票就能兑出300万差不多。那是真气派!就这气派,老爷子有钱的名声,是一传十、十传百,而且越穿越神,最后竟成了开钱庄的。
一天傍晚,来了一伙胡子,进了村就直奔俺家。老太爷接到信儿,马上喊大家撤离。自己提着双枪向村口跑去。说实在的,他并没把几个毛贼放在心上。刚到村口,一群土匪嗷嗷叫着扑上来,老太爷子弹打光了,竟被一阵乱枪打死。
紧接着,灾难降临了。土匪包围了俺家,硬说俺家是大户,起码要捐一个“老串”。土匪管明抢叫“捐大界”,一个老串10万元,拿不够就要杀人。
接下来的情景可想而知,因为俺家根本拿不出这笔钱。
俺爷爷那天正好去老姑家串门,听到信儿赶回家时,满院子都是横七竖八的尸体。俺爷爷从地上捡起块手帕,上面绣着一只“花蝴蝶”,这是土匪的报号。凡土匪都信奉“没有外号不发家”的道理,颇有“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气概。如今连恐怖大亨本,拉登都知道了,9·11后忙不迭地出来“报号”。
俺家就这样败了,败得如此简单、彻底。
那时要想报仇,最好的出路就是当马賊。俺爷爷把手帕揣进怀里,立马上了山。
二
俺爷爷晕头转向地进山到处踅摸,正巧遇上两个外出“踩盘子”(事先探风)的匪徒,立马被蒙上眼牵进了匪窝。
俺爷爷从小练枪,也练就了一身胆气,当蒙眼布解开时,看见十几个蓬头垢面,杀气腾腾的大汉,居然面不改色心不跳。
一个五大三粗,满脸胡子的大汉用枪顶着俺爷爷骂道,妈了个巴子,老子的山门你也敢闯?俺爷爷抬手将枪轻轻拨开,反问道,你们要是不带路,俺能进来吗?那大汉愣了一下,朝俺爷爷上下好一阵打量,问,蘑菇溜哪路,什么价(什么人,到哪儿去)?俺爷爷多少知道点儿土匪的规矩,于是抱抱拳说,俺是前来“挂注”(入伙)的,请大当家的收留。那大汉围着俺爷爷转了一圈,然后将枪插进腰间,说,兴许俺看走眼了,瞅您像个书生,为嘛出来干马贼?
俺爷爷说:俺要报仇!花蝴蝶杀了俺全家。
大汉说:咱这旮儿不是大车店,说来就来。你凭啥本事入伙?
俺爷爷说:俺会打枪。
大汉一听,笑得前仰后合,说,看你瘦得跟个瘘筋狗似的,只要不挫个屁股墩,俺就收留你。大汉转身说,二傻、老根,给他把枪,咱出去遛遛!俺爷爷说,俺要双枪,还有俩盘子。大汉说,嘿,小子,牛皮吹得还不小。
匪窝附近有一个湖,方圆大约两三里地,满是蒿草。众人来到湖边,大汉抬手对天放了一枪,枪声惊起几只水鸟,大汉又是一枪,一只水鸟扑楞楞落在湖里。
俺爷爷说:好枪法。
那个叫二傻的冲俺爷爷扔过两支上了膛的匣子枪,俺爷爷掂着枪,将俩盘子“嗖”地向空中一抛,甩手两枪,枪声中传来清脆的碰瓷儿声。瓷片落在湖面,荡起阵阵漪涟,俺爷爷对准一个漩涡,枪声响过,一条打着挺儿的鲤鱼翻了上来。
大汉、二傻、老根都看呆了:我操,枪打双飞!
俺爷爷说:俺要入伙!
大汉说:上酒上肉给这位爷接风!
接下来就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汉说,这里有酒喝,有肉吃,不过凡事都有规矩。俺看你文武双全,只要能捐半个‘老串,俺拜你为军师,坐第二把交椅。俺爷爷说,行,不过得借俺两把枪。大汉说,俺还送你一人情,花蝴蝶那娘们前些日子被她的炮头插了(杀了),但她丫头藏在孩子的老姨家,是个大户,俺本来想去绑红票(绑架大姑娘),送你了。
三
第二天,俺爷爷就揣着匣子枪又下了山。
下面说说俺奶奶,不过还得先从俺爷爷说起。
且说俺爷爷黑灯瞎火地摸进那家大户,将主人用枪捅醒。主人嘟囔着说,你咋深更半夜回来了?俺爷爷听出是个女人,愣了一下,说,“上亮子”(点灯),別吱声。
煤油灯点着了,炕上坐着一个女人,怀里抱着一浑身发抖的丫头。俺爷爷问,当家的不在?女人哆哆嗦嗦地说,跑生意去了。俺爷爷看见那丫头浓密的乌发上,别着一朵镶玉的蝴蝶,便厉声说,俺要半个老串,外加这丫头。说着,俺爷爷用枪挑起丫头的下巴想看看丫头的模样,这一看不打紧,两眼被勾了魂儿似的凝住了:这丫头太俊了,笔挺的鼻梁,小巧而红润的嘴唇,湿润着,充满了少女的魅力,尤其那双丹凤眼,即使在一丝恐惧中也显得那么机灵和聪慧。
女人说,求求这位爷,您可不能“绑红票”啊!俺爷爷说,妈的,冤家路窄……对不起了,这丫头俺
带走了。不管女人怎么嚎,俺爷爷还是把丫头带走了。
俗话说,无巧不成书。俺爷爷一生的“巧”足够写本书。
俺爷爷押着那丫头走了一天一夜,来到埋着全家人的坟前。俺爷爷手握匕首,要把那丫头的心挖出来祭奠爹娘。但俺爷爷不敢正眼看那丫头,他怕自己看一眼就再也下不去手了,因为那丫头太美丽,好比刚摘的红樱桃,鲜红得让人垂涎。
丫头说:哥哥,你会不会真的杀俺?声音是那样的撩人。
俺爷爷说:“俺要报仇,你娘杀了俺全家!”
丫头说:俺看你没那个胆儿,你的手在发抖呢!你敢看俺的眼睛吗?
俺爷爷说:妈的,闭嘴,老子今天就杀给你看!说着朝坟茔三叩头,说,爹,娘,儿子今天给你们报仇来了。说完一手将那丫头拽了过来,一手举起了匕首……丫头急忙说,哥哥甭急,反正俺的命攥在你手里,啥时拿去你说了算。俺爷爷说,別套近乎,俺不随便杀人,俺是以命抵命。
丫头突然解开了衣服扣袢,盯住俺爷爷说,哥哥,你吃过女人的妈妈儿么?
俺爷爷一精壮的毛头小伙儿哪受得了这个?他的手软了下来,脑子一阵发热,气喘吁吁地说,操,不吃白不吃……
俺奶奶脱去绣着一只漂亮花蝴蝶的兜肚。傻了眼的俺爷爷把刀掉在地上……
丫头告诉俺爷爷,她叫月儿。月儿就是俺奶奶,那年十七岁。
四
俺爷爷没捐上半个“老串”,然“失主东隅,收之桑榆”。当天,他把俺奶奶送了回去。
俺爷爷说:月儿,俺舍不得你,俺不走理了。
俺奶奶说:骑白马挎双枪才是男人,俺等着哥哥混出个样儿来明媒正娶。
俺爷爷想起那第二把交椅,二话没说,提着双枪直奔匪窝。刚到山口,几只长短枪对准了他。一个声音说,缴枪不杀,要不崩了你!另一个说,快点!操你妈的,找抽啊?俺爷爷掏了半天,从兜里摸出俩窝头,向空中一抛,甩手两枪,面渣子溅了一脸。俺爷爷说,二傻,老根,不认识二当家了?
二傻说,呦,二爷。接着转身骂道,你他妈眼睛是撒尿的,这是“枪打双飞”的神枪二爷啊。俺爷爷说,带老子上山。二傻说,二爷,你这二当家是做不成了。前些天花蝴蝶的炮头花子刘杀了花蝴蝶,当了汉奸,引着小鬼子摸上来,把咱连锅端了。老根接着说,要不是俺们在外捐大界,也玩完了。
俺爷爷说:天降大任于斯人!愿意跟我干吗?
二傻说:操,俺几个正合计着没人挑头呢?
老根和大伙儿说:俺们佩服您文武双全,俺们跟您了!
就这样,俺爷爷领着大伙儿重整旗鼓。俺爷爷说,既然重新”起局”,就得立个规矩。于是,几个人割破手指。滴血入酒碗中,然后点上香,俺爷爷说,拜过老辈四方,哥几个今后就起局了。俺自个定的规矩要遵守,否则被枪打死,遭炮轰死,喝水呛死,吃饭噎死!二傻他们几个也跟着这样说。
俺爷爷说,今后,咱要打小鬼子,杀汉奸,不祸害老百姓,你们要是听俺的,咱就一起干!
一次,曰伪军偷袭靠山屯,要把那里的人全部杀光。俺爷爷提前得到了消息,说,杀小鬼子,敢去不?
二傻说:敢!
老根和大家伙说:敢!
俺爷爷说:好,够爷们儿。
于是俺爷爷率众化装混在村民中。当小鬼子架好机枪准备扫射时,俺爷爷一抬手,就把射手的脑门打开了花,随后大家弹无虚发,将五六个小鬼子和10多个伪军全部消灭。
这是俺爷爷起局后的第一场大胜利。那次胜利,俺爷爷缴获了两把蓝汪汪的德国造镜面匣子枪。当晚,他就乘着夜色,潜回了俺奶奶家。他有一年多没回家了,他太想俺奶奶了。
俺爷爷的出现,喜得俺奶奶小麻雀似的,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哥哥、哥哥,你这血渍呼啦的,打哪儿钻出来的?俺爷爷说,小鬼子的血,都是欠咱的。看看老子的枪,正宗的德国二十响。
俺奶奶间:哪儿来的?
俺爷爷说:小鬼子送的,老子杀了好几个鬼子呢。
俺奶奶说:就你?拿刀子对着俺都哆嗦,吹吧你!
俺爷爷说:老子现在兵强马壮,等小鬼子一玩完,老子被招了安,二十拾大轿明媒正娶。来,让俺抱抱!
俺奶奶说:埋了巴汰的,先别猴急,看看你留的种吧!
炕旮旯的襁褓里睡着个胖小子。这不是俺爹,而是俺大伯。俺大伯没能活到今天,1947年死在了还乡团花子队的魔掌里。俺爷爷的眼睛笑成了一条缝,说,哈哈,打胜仗,得儿子,老子双喜临门。他瞅着襁褓里的儿子,仿佛浑身上下有使不完的劲,一下子把俺奶奶抱到了炕上……这一晚,俺爷爷搂着儿子,使劲偎在俺奶奶的怀里撒着欢。不久,当地好几绺胡子推举俺爷爷为首领。俺爷爷率领众人驰骋白山黑水,骑一匹白色“鞑子马”(蒙古马),手使两把匣子枪,很少枪响人不倒,杀掉多少鬼子、汉奸和富豪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了。
五
1945年8月15日被称为“光复”日。
俺爷爷说:小鬼子完了,咱也得商量商量干啥。
二傻说:满洲国没了,蒋委员长回来了,咱去投国军。
老根说:别,咱去投八路,听说八路,对咱穷人好。
二傻说:我操,那八路穷得卡八裆里摇铃铛,衣服都没得穿。国军有吃有穿,还发饷。
有人说:都是扛枪打仗,投谁都一样,咱先下山,碰上谁投谁。
俺爷爷说:国军有吃有穿,但祸害老百姓。倒是八路和咱的规矩挺相似,不如投八路吧。
于是,俺爷爷对俺奶奶说,老子要当兵,混他个连长营长的干干。
山里人不知道什么是时事政治,民国对俺奶奶来说就是“袁大头”,因为那玩意儿好使;俺奶奶也不知道张作霖,但知道什么是土匪,知道当土匪不好。于是,俺奶奶说,去吧!俺等着哥哥的二十抬大轿!
那时候,国共逐鹿东北,共产党到处招兵买马,急需俺爷爷这样既有正义感,又有战斗力的队伍。
一天,山上来了一位身穿灰布军装的女兵,腰间别着一支锃亮的德国造勃朗宁手枪。女兵朝俺爷爷抱抱拳,说,鲍先生文武双全,饱读诗书,特来拜会。俺爷爷一摆手,说,那都是以讹传讹,敝人只读了点《四书》《五经》,还没全背过呢。女兵笑着说,读过诗经就能识大礼。直说吧,我们是东北民主联军,非常欢迎先生这样的人为国家、为民族尽点儿力。俺爷爷说,您太客气了。老话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俺正准备接受招安呢。
寒暄过后,女兵自报家门,说,我姓宁,名茹凇。代表东北民主联军G纵队新编独立团与先生谈判。俺爷爷说,这没问题,可就您跟俺谈?俺爷爷平日被人们簇拥着,个个说着奉承话,眼下八路派了这么个年轻姑娘前来招安,他觉得有点怠慢他。宁茹凇说,看来您……的手下不太服气?咱们可以比试比试。她很客气地将“您”改成了“您的手下。”
二傻说:口气不小,比识文断字还是比枪?
宁茹凇说:枪!
二傻说:识文断字有俺大当家的,比枪有俺。
宁茹凇说:你不够格!
俺爷爷说:真他妈痛快!俺要是输了,立马把队伍交给你,俺回家抱老婆种地去。你说怎么比?
宁茹凇说:一局决胜负。
“一局决胜负”拿如今的话说就是PK。但俺爷爷PK宁茹凇就好比刘欢PK超女,那是输不得的。
俺爷爷又在湖边表演了“枪打双飞”的看家绝技。宁茹凇甩手两枪,打断了两根在风中摇曳的柳树条子。俺爷爷说,好枪法,好枪法!说着甩手击飞了二傻头上的一盏油灯。宁茹凇没有打老根头上的那盏灯,她说,咱八路不拿人的尊严赌博,我弃权。
俺爷爷、二傻、老根和大家伙:……
宁茹凇说,咱比比基本功。说着把匣子枪拆得七零八落,兜在衣兜里,向前走了十步,回头搂火开打,又打断了在风中摇曳的两根柳树条子。
这就是有名的“十步装枪”。
俺爷爷也拆了匣子枪兜在衣兜里,丢三落四地走了十步……俺爷爷输得心服口服,对二傻和老根说,我操,这八路连一姑娘都这么厉害,将来一定坐天下。二傻和老根说,您说句话,咱就跟着八路干!
宁茹凇留在了山上,俺爷爷经常向她请教问题,偶尔也请她指点指点队伍训练。宁茹凇经常和俺爷爷聊聊古今中外的大事,从林则徐焚烧鸦片讲到中日甲午战争,从国共合作抗日讲到德意日法西斯的覆没,最后讲到国民党搞独裁统治,背信弃义撕毁停战协定,妄图消灭八路军、新四军,旁征博引,有根有据,直把俺爷爷说得灵魂出窍,五体投地。
俺爷爷把胸脯子拍得啪啪响,说,今天不论年龄,俺叫您大姐,接受八路的改编。但是俺也有一个条件,您得为弟兄们出谋划策,老话叫军师,队伍上叫参谋长。
于是,俺爷爷骑着白马、挎着双枪,带着他的百十号人参加了革命。
六
俺奶奶始终在家等着那二十抬大轿。终于,一天傍晚,俺爷爷回来了。
那天,俺奶奶正伏在炕沿上拍着俺大伯打盹,忽听外面喜鹊嘎嘎叫个不停,俺奶奶一睁眼,俺爷爷手提马刀,腰插双枪,威风凛凛地进了院——这时的他,已经是东北民主联军G纵队新编独立团的骑兵连长。
俺奶奶喜滋滋地叫道,哥哥,啥风儿把你刮回来了?俺爷爷说,俺在附近清剿花子队呢,想月儿了,就悄没灯跑回来了。
那时候,国民党军在东北收编了日伪警察,反动的民团武装和多如牛毛的土匪。这些政治土匪无恶不作,而且衣着不整,言行污秽,冬季多戴长耳帽遮寒,所以老百姓管他们叫花子队。
俺奶奶戳着俺爷爷的脑门说,匪心难改。多加小心,这一带可是土匪窝呢。俺爷爷说,老子现在是八路军的骑兵连长,谁敢惹我,把他尿泡打成筛子。
回到家,俺爷爷那个美就不用说了,钻进俺奶奶的被窝,用胡子拉碴的嘴使劲亲俺大伯,又用他的马鞭子在俺奶奶的身子上蹭来蹭去。
天亮了,折腾了一宿的俺爷爷终于睡着了。俺奶奶又听见喜鹊在房前屋后不停地嘎嘎叫着,叫得焦急,叫得刺耳,叫得阴森森的。她预感到什么似的,抬眼向远处看去,不好,山上报警的消息树倒了。
原来,俺爷爷回家,被国民党收编的汉奸土匪花子刘的探子发现了,他带着队伍来抓俺爷爷。俺爷爷跨上他的鞑子马向村外冲去,回头撂下一句话,月儿,你等着,老子马上带队伍杀回来。
俺爷爷跑出家门后,俺奶奶抱着孩子还没出屋,就被包围了。十几个匪徒闯进院子,把住院门,用抢逼住俺奶奶。凶神恶煞地喝令交出俺爷爷,俺奶奶怒目而视。一个匪徒号叫着,一脚把俺奶奶踢倒。俺奶奶爬起来还是不回答……匪徒们冲进屋内,翻箱倒柜,抢劫东西,把锅碗瓢盆扔得满当院。
一个匪徒上来抢俺大伯,俺大伯大哭起来。俺奶奶使劲搂着俺大伯,大骂,牲口,你们都是牲口。
匪徒们大喊大叫,恶狠狠地用枪托撞俺奶奶的胸,又抓住俺奶奶的发鬏往墙上撞,把俺奶奶的头撞得鲜血直流。俺大伯终于被抢走了。一个匪徒狂笑着把俺大伯掼到墙上,俺大伯哼都没哼一声,当时脑浆进裂气绝身亡。
空气凝固了,声音凝固了……此刻,俺流泪了,因为俺感受到了俺奶奶心如刀割的绞痛。
一个匪徒声嘶力竭地叫嚣,上刺刀,挑死这个八路婆。几个匪徒咔咔上了刺刀,向俺奶奶逼来,但突然吓得驻足不前:俺奶奶木然地站着,纹丝不动地站着……她的头发都竖起来了,目眦欲裂,表情骇人。
“咣当”,一个匪徒把上了刺刀的大枪掉在地上,又战战兢兢弯腰去取。
这时,奇迹出现了:只见俺奶奶狂奔几步,一脚踏在弯腰捡枪的土匪脊背上,纵身拔地一跃,登住墙半腰的石缝,双手扒墙,嗖的一下窜上一人多高的墙头,在匪徒还没清醒过来的愣神中,飞身跃到院外消失了。
天际里传来俺奶奶的声音:狗日的,月儿发誓带俺的男人回来报仇……
多少年后,关于俺奶奶这次“飞檐走壁”,被无限夸张放大。在乡亲们的传说中,俺奶奶是一个头扎丝巾,身披斗篷,短衣紧裤,飞檐走壁的女侠。俺相信这个传说,因为“人类极限学”已经证明:人的生理极限可以定性,但无法定量,精神力量和求生的意志能使人在危险事件中表现出巨大的能量和超乎想象的行为。
七
俺爷爷得到信儿,嚎啕大哭了一场,咬着牙说,有仇不报,那是孬种!老子今儿就去报仇。
二傻、老根和大家伙说:俺跟你去!
俺爷爷擦干眼泪,说:好兄弟!咱现在不是土匪,有纪律。二傻和老根去一个。二傻说,那就听天由命!说着他把一块大洋举起来,说,袁大头。被抛起的银元划着弧线落下来,袁大头朝上。
俺爷爷和二傻换上黑衣黑裤,马嚼子一勒就上路了。凭着对情况和地形的熟悉,他们在靠山屯附近撵上了流窜的匪徒。俩人拴了马,向屯子里摸去。
两个巡逻的匪徒边走边唠。一个说,我说吴老疙瘩,这几天生意可忒好了,算起来七八辆大胶车。吴老疙瘩说,是呀,二狗子,刚才二当家的说回去就“挑片”(分红),加上以前攒的,俺就能把翠花给娶了,啊,那屁股,那奶子……俺心都酥了。二狗子骂道,就你那孬样还想娶翠花?也不撒泡尿好好瞅瞅,要身材没身材,要气势没气势,那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哼,告诉你,翠花老早就答应俺了。吴老疙瘩不高兴了,说,你那话啥意思?啊。你想抢老子的翠花……
呸!操你妈的,来了几天?枪还没捂热乎呢,就跟老子耍横是吧……二狗子骂得不过瘾,上去又是一大耳刮子。吴老疙瘩被激怒了,大骂,妈了个巴子,俺老娘都没动过俺一指头,老子做了你。说着掏出刀子扑上来。
真正的土匪,不像电视剧里那样个个八面威风、颐指气使,甭说首领整日提心吊胆,防止有入不服而随时可能篡权,就是一般的崽子被惹急了,也会不顾后果的立马反目。
二狗子端起枪就要搂火,只听“扑哧”一声,一把飞镖插进他的后心,二狗子“啊”了一声俯在地上。
俺爷爷将枪顶在吴老疙瘩腰上说,缴枪不杀。吴老疙瘩紧张地说,谢救命之恩!看您也是把好手,请问哪路的?俺爷爷说,老子以前也“吃打饭”
(干土匪),现在是八路。
那年月,八路是最好的招牌,好比今天的“知名品牌”。
吴老疙瘩扑通跪下,八爷手下留情,俺前些日子刚‘碰窖,(火拼)过来的,有啥事尽管吩咐。俺爷爷说,好,给老子带路,俺要会会花子刘。吴老疙瘩说,花子刘回山了,屯子里是他弟弟刘二愣,正在东头老曹家‘压花窑(强奸妇女)呢。
俺爷爷对二傻说,你在这里接应,天黑前老子没回来,就是撞墙睡着了(行动失败,死了),你赶紧回部队。二傻说,俺接着去,替你报仇。俺爷爷说,别扯犊子了,老子睡着了,你赶快带队伍来收拾他们。
俺爷爷跟着吴老疙瘩摸到了东头老曹家,拎着双枪冲屋里大喊,操你妈刘二愣,俺为儿子报仇来了!
屋里,刘二楞拿枪逼着曹家的闺女欲行非礼,那闺女誓死不从,俩人撕扯着。外面的声音吓了他一跳,骂道,哪个杂种不想活了?俺爷爷喊道,狗日的刘二愣,老子是你八爷,八路军骑兵连长鲍文龙!
刘二愣从窗户垛口里露出了半个脑袋,把黑洞洞的枪口伸了出来……双方的枪同时响了。刘二愣眉心中弹,倒在炕旮旯。
俺爷爷说,我操,这小子还凑合,算个“好吧嗒”(老手)。话音未落,一股鲜血从俺爷爷右耳朵根子一直流到脖子里,俺爷爷的右耳朵从此少了半边。
八
因为那次擅自行动,俺爷爷被关了一天禁闭,记处分一次。不久,俺爷爷奉命为全团准备过冬的给养,这也算是“戴罪立功”的机会。于是,他带上十几个人,买了箱大烟土,然后凭借当年的老套路和老关系,在“国军”和土匪中置换。几个月下来,竟变戏法似的换成了十几辆胶轮大车。那年月儿,这些大胶车不啻于现今的奔驰和宝马。
俺爷爷得意洋洋地骑着白马,挎着双枪,与前来接给养的东北民主联军G纵队新编独立团政委宁茹凇并辔而行。俺爷爷说,政委,这眼瞅要天黑了,前面就是五里屯,俺们在那儿宿营。宁茹凇说,就依你,这一带是你老家,情况你熟。
俺爷爷悄悄对二傻说,兄弟,寓家越近,俺的心越跟猫抓似的。二傻说,大当家的放心,今晚保管给你送个捂脚的。
队伍进了五里屯,俺爷爷对宁茹凇说,五里屯有家大户,俺们就住那儿,地方大,还有炮台,能应付突然情况。队伍进了大宅院,宅院一正两厢,院落的四个角都有戍楼,设多处炮眼和射击孔,俺爷爷派出了警戒哨,换下了炮台的家丁。
说话间,二傻回来了,真带回一个“捂脚的”——俺奶奶。俺爷爷见到俺奶奶,立刻心猿意马,顾不上人多,把俺奶奶抱起来放在马上,缰绳一勒,就出了屯子。据说,俺爷爷哼的就是现今最流行的东北小调:大姑娘美来,那个大姑娘浪,大姑娘钻进了青纱帐……等俺爷爷把俺奶奶驮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下来。
俺爷爷对宁茹凇说,政委你放心睡吧,这儿有我和老根,俺老鲍的枪从没失过手。
宁茹凇说,听说你爷爷就喜欢枪,到你爹,再到你,从来枪不离身。俺爷爷说,俺以前玩枪,是为了不被欺负。现在不一样,咱是为了解放劳苦大众。宁茹凇说,咱下一代一定能铸剑为犁。不需要再靠枪来打拼。俺爷爷说,您是说以后枪就没用了,那要是敌人打过来咋办?宁茹凇说,革命胜利了,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那时候,枪可以作为娱乐来进行比赛。世界上有个各国都能参加的运动会,50年前就有射击比赛。
俺奶奶说:哥哥,你的“枪打双飞”准拿第一!
宁茹凇说:有个飞碟射击,开始是放鸽子,后来改成扔盘子,和“枪打双飞”很相似。
老根说:等社会主义了,大当家的您真去试试。
这一晚,俺爷爷他们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进入了梦乡。
大约下半夜,俺爷爷听见他的鞑子马打了个响鼻。这马跟着俺爷爷多年,也算“老江湖”了,见了生人会本能地打响鼻提醒。俺爷爷打了个激灵,翻身爬起来,用枪挑起猫眼儿布望去,夜幕下几个人影一闪,向窗下猫腰摸来。俺爷爷急忙捅醒老根,朝黑影轻声说,蘑菇溜哪路,什么价?黑影一愣,少顷回答,想啥来啥,想吃奶。就来了妈妈(找同行)。对方略微放松了警惕,慢慢抬起身子。说时迟,那时快,俺爷爷照准黑影就是一梭子。
“哎呀!”几声慘叫,从窗外传来……接着,外面开始向屋里打枪。老式房子窗垛宽,窗子小,很适合掩蔽,俺爷爷一把将宁茹凇推到炕旮旯,将身体靠在窗垛里向外射击。老根也抓过卡宾枪一阵乱扫。洋人造的那玩意儿很顺手,自动供弹,一弹匣15发,打起来“乒乒乓乓”像下弹雨。
被枪响惊醒的俺奶奶“啊”的一声爬了起来,就在她张嘴惊叫的同时,窗外射进来的一颗子弹打中了她的脸腮,俺奶奶一头栽在炕上。外面的枪还在向屋里射击,火力挺猛,墙皮啪啪掉土,宁茹凇一把将俺奶奶搂过来,一骨碌下滚到炕沿儿下。
屋里一支卡宾枪,两支匣子枪,那火力在当时是很猛的。俺爷爷用两条大腿弯压子弹,供两把匣子枪射击,这是他拿手的“两腿装弹”。
炮台上的二傻急傻了眼,红着眼珠子大骂,我操,狗日的摸进来了,跟我来!说着带人冲到院中,匪徒已不知从哪儿跑了。大家搜索了一阵,只见院内一溜血迹,淌到墙根下。
俺奶奶在屋内叫唤起来,宁茹凇点灯一看,俺奶奶两个腮帮手直冒血。原来俺奶奶“啊”的同时一张嘴,子弹从腮帮子这边飞进,从那边飞出,一边一个眼,没硬伤,也算不幸中之大幸。
这时外面枪声大作。俺爷爷从枪声判断敌人虽然人数不少,但没有重武器,充其量是一群政治土匪,便透过炮台的射击孔向外望去,依稀听见一个声音喊道,妈的,冤有头,债有主,现在,杀死二当家的人就杵在那,不能放过他。俺奶奶捂着腮帮子说,天杀的,这是花子刘。
匪徒吆喝道,老规矩,贴头钱的,赏大洋200,大烟泡50个;贴二钱的,赏大洋100……所谓“贴头钱”就是第一个冲上去的,“贴二钱”就是第二个冲上去的。
匪徒像打了兴奋剂,拨马开始冲锋,接近炮台的时候,翻身下马,凭借着夜色的掩护向炮台涌来。炮台外是一片开阔地,没有什么障碍物,有几个匪徒已经冲到了炮台前。炮台内的机枪突然喷出了火舌,几个匪徒发现情况不对,刚想逃跑,就被机枪组成的交叉火力打倒了。
枪声中传来“啊!啊!”一阵阵惨叫。
匪徒开始烧炮台附近的房子,夜空被大火映得通红,一缕缕烟尘在空中凝聚,匪徒凭借浓烟的掩护一次次发起进攻,但都被挡了回去,双方一直打到东方露出了鱼肚白,战斗异常激烈,开阔地前流淌着鲜血,鲜血之上是横七竖八的尸体。
短暂的沉寂后,枪声大作,匪徒又开始进攻了这时,俺爷爷突然兴奋地喊道,听!小钢炮,咱的队伍来了。抗战胜利后,共产党抢先进入东北,缴获了不少小鬼子的追击炮,俗称“小钢炮”。这是土匪和“国军”都少有的武器。
土匪在“咣咣”的炮声中开始逃窜。
俺爷爷热血沸腾,牙龈发紧,对宁茹凇说,政委,俺要为儿子报仇,也为死在他手里的乡亲们和
弟兄们报仇。说着跨上白马,提着双枪,对俺奶奶说,月儿,杀了花子刘俺就回来娶你,二十台大轿!
九
俺爷爷这次是奉命剿匪。那时的土匪基本剿灭得差不多了,只剩下一些残匪纷纷逃往深山,花子刘就是其中之一。为最后剿灭花子刘,俺爷爷带着小分队从野草茫茫的平原一直撵到深山老林,终于在第一场大雪那天找到了花子刘的踪迹。
那是一处看山人搭的窝棚,在茫茫大雪中只剩下一个屋顶。俺爷爷示意大家从腰间解下一块铺衬裹在脚上,以减轻走路的声响,然后呈扇形向窝棚包围过去。
接近窝棚时,门突然开了,一个匪徒斜挎着枪出来解手。就在他转身回窝棚的时候,俺爷爷用手势指挥二傻和老根各守一側,自己突然起身,顺坡而下,冲到窝棚跟前,一脚把门踹开,大喝一声,狗杂种,老于今天索命来了。
花子刘从睡梦中惊醒,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俺爷爷就扣动了扳机,一串子弹飞出枪膛,沿着弹道飞进花子刘的头颅。花子刘没有片刻挣扎就“咕咚”一声摔在炕沿下,手中的枪落在了地上。
俺爷爷哈哈大笑,孬种,这是替俺儿子索的命。
一手握短枪的女人从花子刘身下挣脱出来,刚仰起头,一颗子弹穿过她的面门,从后面的发髻飞了出去,一只玉簪的碎片在血光中向四周飞溅……俺爷爷狠狠地说,这是欠俺月儿和乡亲们的。
炕旮旯的几个匪徒跳了起来,俺爷爷食指一搂,很自然地扣动了扳机,但枪声却迟迟没响。千钧一发之际。俺爷爷的枪机意外失灵。一个匪徒翻滚到地上,几乎是同时,手里的枪对已经闪出身躯的俺爷爷喷出了火舌。俺爷爷左胸中弹,明显地踉跄着后退了两步……
一切都发生在瞬间。缓过神来的余匪开始疯狂向外射击,门被火舌封住了。二傻几步跃上了窝棚顶部,从腰间拔出两枚手榴弹,顺着窝棚的烟筒掷了下去,而后顺势滚到雪地上。随着“轰”的一声巨响。窝棚顿时成了墓穴,余匪被炸得血肉横飞。
二傻抱起俺爷爷,俺爷爷使出最大力气说,如果月儿生个小子,把俺的枪给他,老子的儿子还他妈玩枪,当将军。
十
辽西山区一普通农户家中,传出一声声撕心裂肺的喊叫。这是女人分娩时痛苦与喜悦交织的呐喊。
土炕上,俺奶奶紧咬着嘴唇,艰难地对宁茹凇露出一丝笑容。她的一只手紧紧攥着绣着花蝴蝶的肚兜,另一只手漫无目标地挥着,那双原本美丽的眼睛显出了痛苦,有些凌乱的头发沾在略宽的额头上,带着褐色妊娠斑的脸扭曲的让人心怜。
哎哟……好痛啊!……俺不行了!俺奶奶不住地呻吟着,脸色变得惨白起来。
一个胖小子终于折腾着来到了这个世界,这就是俺爹。遗憾的是,俺奶奶由于胎位不正,不能正常顺产。导致产后大出血。她耗尽最后的气力把儿子生下来。又笑着和俺大伯、俺爷爷说了最后一句话:儿啊,娘知道你怕黑,娘来了。……哥哥,如果有来世,月儿还跟你钻青纱帐,还给咱鲍家留种!
宁茹凇哭了,二傻、老根和弟兄们都哭了。
俺也哭了,为俺仙女般美丽的奶奶,即使走到了人生的尽头,依然是那样的从容豪迈,那样的风情万种……
后记
俺爷爷的故事结束了。
俺爹由宁茹凇抚养成人。文革时,随丈夫在驻外使馆工作的宁茹凇专程回国,把俺爹送到了俺爷爷的部队。
老根牺牲在朝鲜战场,但二傻仍在这支部队。不过此时已没人敢叫他二傻,都称呼他的官衔:陆师长。这位与俺爷爷过命的铁杆兄弟决心要把俺爹培养成一名优秀的军人,希望能够延续鲍家的枪缘。他说,延续了鲍家的枪缘才是真正延续了鲍家的香火。
俺爹的确悟性甚高,宫至营长时,随这支部队参加了广西边陲自卫还击作战,荣立了二等功。遗憾的是,由于误人雷区,俺爹失去了左脚。战后。俺爹与一位女军医结为伉俪,并育有一子,这就是“俺”。
俺会爬的时候,俺爹也让俺“抓周”。俺二话没说,伸手抓那两支玩具枪。俺爹高兴地说,小兔崽子,行!像鲍家的种。
上初中时,俺去了省射击集训队,主攻飞碟射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