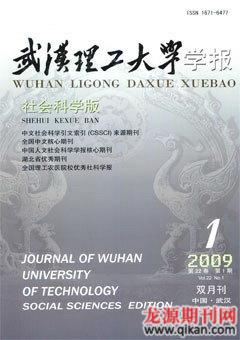论沈从文生命诗学的内在构成
吴投文
摘要:在沈从文的全部创作中,呈现出一个生命诗学的基本构架,这是其创作最为显明的标志,也是其创作独特性的根源所在。“生命”与“生活”,“人性”与“神性”,“人事”与“人生”是沈从文生命诗学的二对基本范畴,联结沈从文思想与创作的各个重要方面。
关键词:生命诗学;生命;人性;神性;人事;创作独特性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09.01.028
一、生命与生活
在沈从文的生命诗学中,“生命”是一个关键词,与之相对应的是“生活”一词,两者都具有特定的内涵。在沈从文论及生命的文字中,往往把“生命”与“生活”作为一对范畴对举的,形成一种互文与对照关系。从这种对举中,可以厘定沈从文赋予“生命”与“生活”这一对范畴的基本内涵。
沈从文对于“生命”与“生活”的看取与理解,显然与惯常的理解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具有强烈的思辨色彩与形而上意味,显示出沈从文站在人生价值终极性的立场上,对于生命价值与意义的独特思考与理性把握。检视沈从文论及到“生命”与“生活”的文字,可以发现,在沈从文的生命诗学中,“生命”与“生活”代表人生的两种基本形式,主要表现为两种具有对立性质的人生基本形式,因而,这两种人生基本形式的指向绝然不同,在不同的维度上显示出各自不同的内涵。
其一,在生存体验维度上,“生命”与“生活”都具有现实品格,都与现实人生紧密相连,然而,两者的指向却大相径庭。在沈从文看来,“生活”之于人类,不仅代表吃喝拉撒与种族的繁殖延续这些简单的物质功利需求,而且代表沉溺于这种物质功利需求的精神状态,因而,“生活”所指代的实质上是一种粘滞于现状而满足物质享受与性的满足的生存状态,一种尚未脱离兽性与物性的生存状态,是人性萎缩,“神性”在精神上缺席的典型表现。相反,“生命”之于人类,则代表一种健全的,不仅符合人性,而且具有“神性”的精神状态,指向人类精神性的生存体验,是人之为人的一种本质性标志。从这一意义上说。“生命”与“生活”是一对相互对立的范畴,代表两种不同的人生范式与人生境界。显然。“生命”居于形而上的超越性层面,“生活”则居于形而下的世俗功利层丽。从对“生活”与“生命”的这种体察与审视出发,沈从文指出:“仅仅有‘生活而无‘生命。人就与动物无别。是一种生物学上的退化现象。”这正是沈从文的忧虑所在,但在文明社会中,这种退化现象却普遍存在。人往往困于“生活”,难于向“生命”超升,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现代人往往粘滞于现实,无暇向理想凝眸,向人生远景凝眸,因而造成现代社会普遍的物欲横流和触目惊心的人性异化现象。在他看来,只有舍物欲而取理想,才能从形而下层面的“生活”升华到形而上层面的“生命”。真正实现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沈从文通过对“生命”与“生活”在生存体验层面上的比照,意识到“抽象原则”对于“生命”的重要性,一个人只有在“抽象”中,排除实际事物的干扰,才能真正领悟“生命”的真义。沈从文认为“人要抽象观念稳定生命”,这样,才能在“抽象”中抵达“生命”,真正实现“生命”的价值。
其二,在人性维度上,沈从文赋予“生命”与“生活”以各自的内涵,两者的歧异是硅而易见的。在沈从文那里,“生命”指向理想健康的人性,从中见出沈从文对人性健全形态的追求与向往。而“生活”指向病态扭曲的人性,从中则显示出沈从文的贬抑与拒斥态度。人性皆善是沈从文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代表沈从文抗拒现代社会人性普遍沦丧的生命理想,寄托他对理想生命形式的追寻与探究,而对人性堕落的挖掘与审视则是沈从文创作的另一重要方面,代表沈从文对个体生命的阉寺性和国民劣根性的审视与批判。不难发现,尽管“牛命”与“生活”的具体指向各异,但在深层内涵上二则又似异而实同,都关涉对人生意义与生命价值的终极性探问,共同构成沈从文创作的生命主题。因此,从根本上说。沈从文对人性的探究是基于对牛命终极意义的拷问与终极父怀的诉求,代表沈从文生命重造与文化重造的理想。沈从文对现代文明的病症有极为清醒的认识,对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人性堕落现象深感痛心,这种人性异化表现于生命个体为阉寺性,表现于社会群体则为国民劣根性,导致生命个体失去活力,现代民族国家缺乏生机。在沈从文看来,治疗这种人性异化的良药则是恢复现代人的自然人性与原始人性,恢复现代人失落的童心,也就是以感性的形式恢复现代人的精神力量,同时又以理性与意志的力量节制现代人无止境的物欲,使之从“生活”升华到“生命”。
其二,在价值维度上,沈从文赋予“生命”与“生活”以鲜明的价值取向。在沈从文看来,“神在生命本体中”,“神”并不仅仅只是柄居在“生命”之中,而是具有生命本体论意义,对于“生命”发挥着统摄性功能,规约着“生命”向着真善美的意义生成,“神性”则是“生命”的本质性规定。换言之,如果“生命”与“神”一体,“生命”就显露出“神性”,外化为真善美的理想生命形式。生命因之呈现出超越性意义。在这一意义上,“生命”具有超验色彩。代表一种化生万物,类似于柏拉图所谓“理念”的神圣事物,具有神秘与抽象的性质。同时,“生命”还具有变动不居的性质与不可抑制的内在冲动。“生命随日月交替而有新陈代谢现象,有变化,有移易。生命者,只前进,不后退,能迈进,难静止。”沈从文强调生命的创造性本质,认为“生命”只有通过创造才能显示出“神性”,在永不停息的行动与选择中显示出“神性”,才能达到美与爱,真正实现人生的价值与意义。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沈从文提出“美在生命”的命题。相反,“生命”一旦脱离“神性”,则成为空虚之物,就会呈随落趋势。由形而上的超验层面下降为形而下层面的“生活”,沾附到世俗的功利价值上,呈现出庸常的物质意义。这样,“生命”求真向善趋美的创造性本质就消解在庸常的物质意义中,呈现出假恶丑的“生活”原生态。这种“生活”符合一种牛物本能的外在要求,使人们仅仅满足于欲望的实现,因而造成灵魂与精神上的空虚,标志着现代人价值理性的彻底沦丧。沈从文通过“生命”与“生活”在价值维度上的比照。揭示出“生命”美化人生创造人牛的普适性意义,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生命”具有提升“生活”境界的升华功能。
在沈从文的生命诗学中,“生命”与“生活”这一对范畴具有统摄性意义,居于沈从文生命诗学的轴心,成为沈从文生命诗学的基点。通过对这一对范畴的分析与探究,可以对沈从文的创作进行一些具有规律性的揭示,把握到其生命诗学的基本特征,同时可以发现沈从文生命诗学内在构成的独特性和丰富性。
二、人性与神性
沈从文生命诗学的另一对基本范畴是“人性”和“神性”。长期以来,只要谈论沈从文的创作,似
乎就离不开“人性”这一话题。对人性的表现与彰显是沈从文创作的娃著标志,但如果仅仅停留于沈从文创作中的人性层面,则还远远不够,在他的创作中,还存在着一个更具超越性的层面——神性层面。正是在神性层面上,沈从文才真正地与其他作家区别开来,对神性的追寻与凝眸,成为其生命诗学的重要特征。沈从文创作中展示出来的人性形态,既表现出“普遍人性”的内核,又显示出与神性合一的超越性意义,由人性进到神性。使人性与神性合为一体,呈现出沈从文生命诗学的独特形态。
沈从文人性观的理论内核是普遍人性,他称之为“共通人性”,实质上是指自然人性与原始人性。沈从文认为创作必须以表现“共通人性”为准则,这是决定创作成功与否的条件。他多次指出“共通人性”具有恒定不变的性质,由于人性的这种恒常性与共通性,古今相距的时间差异与中外相距的地域差异,都可以得到消除,因而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之间的人们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相互理解与交流上的障碍,这也使文学能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交流工具,能使人心与人心之间取得沟通与连接,文学的价值与意义也就在这里表现出来。
在沈从文看来,作家应该是“人性的治疗者”。他的创作因为表现出“人性最真切的欲望”,显示出相当的人性深度,这是其作品具有长久艺术魅力的重要原因。尽管沈从文小说中的人物就单个而言,一般并不具有两极对立的组合型性格,大都性格比较单纯,往往代表一种单一的人性向度。但如果把沈从文所创造的所有人物形象作为一个整体来观照,则鲜明地呈现出一个两极对立的人性世界。湘西世界代表一种健全人性的生命形式,都市世界则代表一种人性异化的反生命形式,沈从文创作的人性深度就是通过这种对照与互见显示出来的。另一方面,沈从文创作中的人性深度又在一定程度上偏约为一种“片面的深刻”,他在对自然的凝眸中总是流露出对现代文明的疑惧,在神往于自然人性和原始人性时又着意消解人的社会性与时代性。因此,在沈从文的创作中,往往存在着一个无法化解的对立模式,其核心是湘西生命形式与都市生命形式的对立,又在这一总体对立模式下派生出各种各样的对立与冲突,这使他的艺术世界存在着一些不谐和音,显露出沈从文人性观的局限。对沈从文来说,由于过于粘滞于自然人性,在他精心建构的湘西世界中,自然人性与原始人性的充分展示,一方面固然可以映照出都市社会的病态与丑恶,在两相对照中表现出“人与自然契合”的生命理想,另一方面则导致在一定程度上对人作为社会性存在物的偏离,因而他所反映的人性具有某种程度的狭隘性,并没有揭示出人的全面性。长期以来,人们在领略湘西世界的胜景时,也对之发出各种质疑,也许与这一原因不无关系。
在沈从文的生命诗学中,神性是与人性相对应的一个重要范畴,两者互为补充和参照。他在谈及人性时,并不拘泥于自然人性的观念,而是在自然人性之上,另有一个超越性的存在,那就是具有理念色彩的神性。同样,在他谈及神性时,也往往有一个预设的前提,那就是基于自然人性之上,以自然人性作为基点,因此,神性范畴既是对人性范畴的补充,又是对人性范畴的提升,从另一维度揭示出沈从文生命诗学的丰富性与独特性。反映到他所创造的艺术世界中,人性与神性往往融合为一体,湘西世界的自然人性尽管显得那样单纯却并不显得单一,也并不缺少深度,而是在单纯与明净的自然人性中,蕴涵着丰富的意味,指向“生命神性”的超验层面,因此,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既不乏人性深度,又显示出神性的光辉。与之相反,都市世界则代表着人性与神性的双重失落,从中寄予着沈从文批判国民劣根性的生命理想。
沈从文并没有赋予神性这一范畴以确定性的含义,但从总体上来看,神性与他所说的“抽象观念”相连结,似乎具有某种不可言说的性质。从沈从文朦胧晦涩的阐述中,同时联系到他所建构的艺术世界,可以把握到神性的基本内涵。沈从文一再慨叹,“生命具神性”,“神在生命本体中”,“生命之最高意义,即此种‘神在生命中的认识”,“生命”因与神性连结,故而居于形而上的超越性层面,而“生活”因与神性远离,故而居于形而下的世俗层面,由此可见,神性乃是生命的本质性规定。在沈从文那里,“神”具有本体论意义,“神”就是生命的本原与根基,是决定生命价值与意义的最高存在,神性则是“神”内在于生命的诗性显示,指向生命存在的超验层面,关乎对生命存在终极意义的肯认。
作为一个具有强烈人性意识的作家,沈从文的独特之处在于,既张扬顺乎自然的人性形式,把彰显自然人性作为其创作的核心命题,又能超越自然人性固有的局限,赋予自然人性以神性的光辉。因此,沈从文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人性形态,并不是对自然人性原生态的简单复原,而是在对自然人性的审美观照中,沟通人性与神性的内在统一性,达成由人性层面到神性层面的超越。从这一意义上说,神性是人性的超越形态,是对人性的提升与优化,代表沈从文对生命超越性意义的体认。沈从文说他“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人性成为其全部创作负载的主要内容,然而往深处看,这神庙所供奉的为只是人性,还有更具超越性的神性。在他看来,美与爱存在于一切有生中,神亦存在于一切有生中,故而神性可谓无处不在,只是有待于去发现。沈从文对湘西乡土的精神皈依,实质上是对“神”的皈依,对神性的皈依,是在对湘西乡土的返顾中去寻找与发现那依然存在之“神”,而沈从文对都市世界的观照,实则是出于造神的精神需要与内心冲动,“神”在都市世界的解体。在沈从文看来,不仅代表生命个体的生存悲剧,而且代表现代民族国家的精神悲剧,“政治、哲学、美术,背面都给一个‘市侩人生观在推行。换言之,即‘神的解体”。因而造神就成为当务之急,以恢复现代人的生命信仰,重建现代人的生命理想。面对现代社会无处不在的病相与弊端,沈从文始终充满着寻神与造神的心理冲动,其实在沈从文的创作中,就始终纠结着寻神与造神的精神矛盾,湘西世界与都市世界就代表这种精神矛盾的两极,他的文本则是这种精神矛盾的记录。由此看来,在沈从文对人性的抒写后面,有一个深广的精神背景,神性作为人性的升华形态,赋予沈从文的创作以特异的色彩,从中隐含着沈从文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忧患意识与重造生命的热切愿望。如果说在沈从文的创作中,生命是一个全方位的结构性视角,那么,颂扬神性则是一种整体性基调,与此相关,如果说“生命神性”是沈从文全部创作的哲学基础,那么,建筑人性神庙则是沈从文生命诗学的全部归结点,人性与神性构成沈从文生命诗学一个极其重要的维度,从中显示出沈从文的创作独特性。
三、人事与人生
沈从文生命诗学的另一对基本范畴“人事”与“人生”主要落实在文学创作的具体操作层面上,联结着沈从文创作的各个重要方面,从中可以发
现沈从文文学思想的独特表现形态和充分个性化的艺术运思方式。在沈从文的文论中,很少发现“现实”、“社会”、“时代”这些当时文坛的流行词汇,即使在不多的情况下需要使用这些词汇时,也往往显得似是而非,与一般人的理解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沈从文往往用“人事”和“人生”这对范畴来取代这些流行词汇,他的这种取舍是深有意味的,既表明他持守着一种不合时宜的思想,也表明一种孤绝与偏离时代主流文学思想的姿态,这正是沈从文思想与创作独特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显然,“人事”和“人生”包含“现实”、“社会”、“时代”的某些内涵,但却不能等而视之,沈从文对于“人事”和“人生”的基本理解包含着一些不为当时主流创作所认同的“另类”思想。在他的文学观念中,“现实”、“社会”、“时代”始终是一些模糊的概念。没有被赋予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在他看来,这些概念要么具有抽象的性质,与文学和生命并不存在什么必然的联系,要么具有浓厚的世俗气味,不过是代表堕落与下降的社会趋势而已。因此,他不无偏执地认为,作家应该对“现实”、“社会”、“时代”保持足够的警惕,应该处于时代潮流之外来观察、理解、描述自己所处身其中的时代和社会。只有在与“现实”、“社会”、“时代”这些名词的区别与对照中,同时综观沈从文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实践,才能厘定“人事”与“人生”这一对范畴的基本内涵。
其一,“人生”与“人事”都关联着生命的存在状态,具有一定的相互包容性,但并不是一个同一性概念,各自具有特定的内涵。综合沈从文对于“人生”与“人事”的相关表述,并结合其创作实践。可以发现,“人生”是生命整体状态的呈现,是一个意义和价值的生成过程,也是一个意义和价值整体,关联着生命活动的各个层面。相对而言,“人事”则是生命状态的细节性呈现,表现出生命状态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在沈从文那里,“人事”并非纯客观的社会现象与现实世界。而是在作家主体情感的投射下,物象与心象合一,人、事、情、景、物诸要素融合为一体的形象世界,往往表现为生动具体的细节和情感化、氛围化的情节。因此,沈从文要求作家向内写心,向外写物,或内外兼写,由心及物由物及心混成一片。如果说“人生”是一个构架,对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具有宏观概括性,隐含着探索生命存在意义与价值的哲学寻思意味;那么,“人事”则是肌质,通过丰富的细节性和具体性显示出“人生”的整体性意义。沈从文是一个皈依“具体”但又追求“抽象”的作家,要求用“具体”来表现“抽象”,他的创作既有对“具体”丰富而生动的展示,又有对“抽象”的深刻思考。显然,在沈从文那里,“人生”作为生命存在整体意义和价值的呈现属于“抽象”范畴,而“人事”作为生命状态的细节性呈现属于“具体”范畴,通过“具体”的“人事”表现“抽象”的“人生”,可以说是沈从文创作的基本技术操作路线。沈从文一再言说的“人生形式”,正是通过细节化的“人事”表现出来的,他的创作往往从丰富复杂、流动不居的“人事”中抽象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形式”,这成为沈从文创作的基本操作方式。湘西生命形式和都市生命形式作为两种具有对照意义的“人生形式”,包含着丰富的人生含量和人事细节,显示出沈从文开阔的创作视野和巨大的思想概括力。
其二,“人事”和“人生”具有客观性内容,隐含着历史发展的基本走向和现实发展的无限可能性,在丰富的细节中呈现出具有高度概括性的“人生形式”,同时又是体验性的,具有丰富的历史积淀性和想象性内容。在沈从文看来,“人事”和“人生”包含着由人物和人物行为所组成的基本序列,与作家原初的生命经验有着直接的关联,对作家的创作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潜在地规约着一个作家的整休创作风貌和基本艺术选择。因此,他反复强调“人生”是一本大书和“人事教育”的重要性,认为阅读“人生”这本大书和“人事教育”是成为一个作家的草本素养,作家创作的原动力来源于“人事”和“人生”在作家心中燃起的感情,作家的创作动机由此产生。正是由于“人事”和“人生”所具有的这种客观性特征,沈从文指出“人事”和“人生”是不能“制造”的,凭空臆想出来的所谓“人事”和“人生”,只能使作品近于传奇。转入邪僻的异途,远离文学的真实与生命。另一方面,“人事”和“人生”又是在作家原初生命经验的基础上各种“官能”综合作用的结果,具有想象性成分,负载着作家生命体验的丰富性和独特性,“人事”和“人生”只有在经过作家的想象性加工和改造以后。才能转化为具有虚拟性特征和主体独特性的文学作品。沈从文对于“人事”和“人生”的这种主客观结合论,显示出一个观察文学与现实关系的独到视角和作为一个作家对于文学特征的深刻体认。
其三,沈从文对“人事”与“人生”这一对范畴的基本理解蕴涵着深刻的悲剧性内涵,包含着不可把捉的命运感和一种深沉的生命诉求。在沈从文看来,“人事”的基本形式是“常”与“变”及其错综变化,“人生”就是完成于“常”与“变”交错更迭中的宿命性结局。“人事”的新陈代谢,生命的倏忽消逝和命运的变化无常,都被一种不可知的神秘力量所掌握,人生的悲剧就在于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因此,沈从文常常慨叹:“这就是所谓人生”。沈从文这种对于“人事”和“人生”的理解表现在他的创作中,就转化为一种深沉的悲悯感,其创作中那种弥漫性的孤独与悲哀和“乡土性抒情诗”气氛由此形成。在沈从文那里,“人事”所包含的人生内容往往带着“美丽”和“忧愁”,他所向往的美善合一的人生形式在时代的变动中不可抗拒地沉落,这使他的创作显示出一种总体上的“‘神之解体”的挽歌情调。内蕴一种悲凉的哲学意味。他的创作似乎从整体上显示出一种冥想生命存在意义的性质,弥漫着一种忧郁和悲凉的气息,悲悯与悲郁成为沈从文创作的一种基本色调,这与他看取人生的悲悯眼光是完全一致的,他是一个对人生怀着悲悯而又能够真切地表现这种悲悯的作家。沈从文的这种艺术处理与其对于“人事”与“人生”的基本理解有着直接的联系,循此线索可以触摸到其独特的悲剧审美意识观。
“人事”与“人生”作为沈从文生命诗学的一对基本范畴,承载着沈从文的非主流文学思想。他是以一种别样的眼光去探索和思考人生的,他的全部创作关联着深广的人生内容,显示出一种观察人生,反思生命意义的独特眼光。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沈从文的全部创作显示出人生“长河”系列小说的性质。
(责任编辑文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