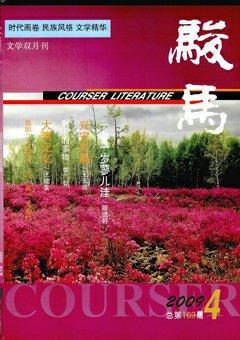大河记忆
王建友
大河并不算大,可也不算小。大河不是藏于山林幽谷中不为人知的急流飞瀑,而是城市中的一道长长的风景,它广袤的水域同它身边绵延的群山相得益彰;可是它在中国地图上却不能像长江、黄河那样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兴趣,甚至连名字都没有标注,只是短短的一道蓝线。
大河穿过的是一座小城,小城市里大多数人没有见过长江与黄河;因为大河比小河大,所以它是大河。也只有小城里的人才会指着地图上那道没有标注名字的蓝线说:“看,这就是我们的大河。”
大河其实有名字,但小城里的人们还是习惯叫它大河。
大河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飘渺的存在,是我寻找生命意义的地方。那种感觉很熟悉,却又很遥远。
我真正熟悉的,是家乡村中的那条小河。小河没有名字,人们以村名给小河起了名字。小河通着大河,但现在已经干涸了,沙石淤满,就像一根干瘪的鱼刺横亘在村子的中央。我曾多次到过小河的上游,深深的河槽,蜿蜒地在田野间延伸,这是它留给这个世界的疤痕。
念小学时,在我的作文里,小河是常用的题材:“春天小河冰化了,河水开始流淌了;夏天鱼儿自由自在地在河水里畅游,我们到河里游泳捉鱼;秋天天气开始冷了,树叶黄了,落叶随着河水漂去;冬天河面上结冰了,我和小伙伴们在上面快乐地滑冰。”而实际上,在我的记忆里,这条小河并没有给我的童年带来什么欢乐,因为它在干涸之前,河水就很浑浊,我童年时是不可能在这样的一条河里嬉戏的。只是听母亲讲过,在她小的时候,这条小河里长满了绿色的水草,她们曾在这里摸泥鳅、洗衣服。
人们喜欢把河比作母亲。长江、黄河不就都被喻为母亲河吗?小城里的人也不例外,把大河也喻为小城的母亲河。于是赞美大河的风光片、歌曲、诗文反复地在小城的电视台和报纸上出现。
但在小的时候,常听母亲对于大河的话就是:“大河馋了,又有人淹死在里面了。”
对于母亲而言,大河是吞噬生命的妖物,是不准小孩子前去游泳的地方。因此我也从来没有在大河里面游过泳。我甚至这辈子也没有游过泳,原因就是源于对大河的恐惧,对水的恐惧。我只在村中那条小河还未干涸之前趟着刚过膝的河水去岸的那边。
当我站在大河的桥上,倚栏遥望大河那蔚蓝如绸的河水的时候,大河似乎仍然是我记忆中的那个飘渺虚无的存在;我走下堤坝来到河岸边,手插入它的肌体里,它给我的感觉很冷、很陌生,遥远得让我无法轻易地融入到它的境界中,不如村中那条我从来没有在意过的小河实际。但这里却有一种神秘的牵引,她像勾起我内心当中的某种渴望,让我有莫名的向往,似乎这里才是我开拓生命的地方;但对未知的恐惧,却在心底泛起,使我在稳定与搏击之间徘徊。我一眼望去,不息的河水,浩荡悠远地流向远方。我的心底涌出一丝遐想,那就是我乘在一艘渡轮之上,倚栏望水,看着两岸不断涌现和消逝的群山与人家。而不像此时,站在岸边,看着不断消逝而去的流水。
海洋里有一种叫鲑鱼的动物,它每年繁殖的时候,就会从大河的入海口返回河域,游回大河源处的浅浅小河。当然这个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们要顶住湍急的河水,飞越瀑布、越过沙坝,而且在返回的途中会有许多的鲑鱼命丧鲸、熊、鹰等食肉动物的口腹。当它们历尽千辛万苦,抵达自己出生地的时候,已经是筋疲力尽,伤痕累累了。这时雌鱼就会选择比较合适的地点,与雄鱼完成产卵与授精。当鲑鱼完成新的生命延续后,奄奄一息的它们就会逐渐死去,把自己葬在出生的地方。而在第二年春天,孵化出的小鲑鱼苗就会顺着河水游向大海,重新踏上它们父辈的路程。
这是一个史诗般的生命征程,它的意义毫不逊色于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壮举。生命源于点滴,涓涓小河流向滚滚大河,滚滚大河流向滔滔长江,滔滔江水纳入浩荡无际的大海。生命在汇聚中融合,越来越宽,容量也越来越大,最后成为永恒。
大河并不是生命的开始,只是生命的征途。我的生命并不是大河滋养起来的,而是村中那条已经干瘪的小河,就像母亲乳液干瘪的胸膛一样。在我们的记忆中都有那么一条熟悉的小河,甚至平凡到可以在中国大地上的每个乡村都可以找到那么一条没有名字的小河,平凡到让人忽略它的存在。我们感叹大河的壮美,更渴望能够畅游长江,因为大河长江能让我们一展豪情。可又有谁曾记起,我们的生命,却源于那些再平凡不过的小河呢?
我们追寻着心底的那股莫名的向往,脱离平凡达到永恒,从大河大江冲入海洋之中,能够在大海的怒潮之中搏浪,追逐翻滚的潮头。然而生命真正的意义却在于达到巅峰之后的返璞归真,达到永恒之后追求平凡,循着来时的轨迹,踏上向生命的起点的折返,那才是胜利的开始。
(责任编辑 王冬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