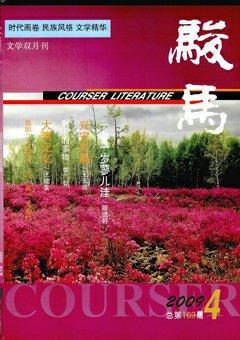剩下的事物
李广智
李广智,1974年出生,辽宁省作协会员,葫芦岛市文联2007年首届签约作家。“新辽西派”散文代表作家。2003年曾就读辽宁文学院,2005年开始乡村散文创作。作品散见于《散文》《中华散文》《鸭绿江》《海燕》《绿风》《青海湖》《红豆》《芒种》《满族文学》《辽河》《岁月》《北极光》等,有散文被《散文选刊》《读者·乡土人文版》《广州日报》等多次转载,并被收入年选及作为高考语文模拟试题等,著有诗集《乡村悟语》。
剩下一头骡子
屯子里还剩一头骡子,深青色,很长时间里,我都不能听不见它亢奋而长久的叫声。那偶尔的一声嘶鸣,在深夜里,划过屯子的天空,嘹亮而孤独。我不是一头骡子,无法进入一头骡子的世界,更无法理解那份孤独的声音。
一件东西或一种事物谈到剩下时,大体上已过了风光的时候,我是这样认为的。我清楚地理解,屯子里的许多东西,像是我们种在地下没能发芽的种子,被埋入屯子的土层下面,再不能进入我们的眼睛和情感的世界。
屯子里真的还剩下一头骡子。我管骡子的主人叫二姑父。一个有些历史的偏僻屯子,常常会这样,几个杂姓的大家族或相邻的屯子互通婚姻,让亲戚走不远,二姑父就是这样联姻的结果。其实,二姑父家原来有三头骡子,刚好拴一驾马车。屯子里习惯上把牛拉的车,称作牛车;驴拉的车,称作驴车;马拉的车,称作马车;把骡子拉的车,也习惯称作马车。二姑父家的马车是他挣钱养家糊口的渠道与本事。这样说,是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当好车老板的,能够让一驾套的骡子或马完全听话,认认真真、安安分分地完成每件活计是需要一种本事的。
多年前,这种马车行走的颠簸声和骡脖子上的铃声响彻在河套的土道上。好奇的我,时常喜欢追在马车的后面,争取搭坐在车尾一会儿,孩子们总是对每件事都会产生好奇。可车后面太颠,人坐不住,要双手拼命拽住车梁,以免掉下来。可屯中的许多孩子,都喜欢坐这种香油车,好像这种免费的颠簸好玩。记忆中的一次,那时我还太小,好不容易抓住了车梁,刚要蹦坐上去,可颠簸中的马车突然加速,我只沾到了车沿边,没坐实,人便被甩脱了下来。车没坐到,却直直地摔坐到地上,差点没摔伤。不知道骡子是否看到我的落败相,那一定很可笑。
二姑父家的骡子,身体较大,耳朵较短,是头马骡,为公驴和母马杂交所生。另两头,其中一头身体较小,耳朵稍长,为公马和母驴杂交所生的驴骡,都被二姑父挑车后转卖给了别人。只留下现在这头马骡。二姑父一定中意这头骡子,认为它是头塌实肯干的好料,把它留了下来。在草绿的季节,那头高大的骡子常会被二姑父和家人用绳子迷在一处荒草茂盛的地方,任由骡子吃食。我经过它身边时,它停下吃草的动作,用眼睛狠狠地瞄我一下,晃晃头,打个响鼻,然后向一边走走,旁若无人的样子。我常常被那种眼神刺痛,没能更近地走近一头骡子。我在人群中行走时,也会时常遇到这种目光,那是一种陌生人的目光。狠狠地瞄向另一个陌生人,然后把目光草草收回,拉开彼此的距离,仿佛一头骡子钻进他们的身体,我们成为在同一条路上行走的两个陌生动物。
一头骡子在一个屯子里吃草、犁地、拉车会是啥种感觉,我同样不清楚。一头骡子独自做着一头骡子的事,这是一头骡子留下来的理由。对于二姑父家的骡子,它担负着二姑父家族和亲戚、朋友耕地的全部责任。我们屯子大概有二百亩土地,它所担负的土地就大约有六十亩,每年要耕、趟两次,总计有一百多亩的样子,这是那头骡子一年的全部重活计,多半不会有谁为它分担。骡子别无选择。人和其它动物相处最终的结果,往往喜欢选择武力,对于一头毫无利用价值的骡子,一定离刀不远。或许骡子老早预料到了这种结果,再累的活计都让一头骡子坚持了下来。人在一头骡子的身上没能找出用刀的理由。
屯子里还剩一头骡子,这是所有屯人都要面对的事实。屯子里失去了所有的马车,大概不会再买入一头骡子,让剩下的一头骡子拥有自己的同类。我在经过那头骡子的身边时,偶尔会看见骡子的眼泪,在悄悄地滑落。我突然想知道,那头骡子的眼泪是为谁流的?它是不是更像我们一样需要温暖和幸福,那一定是一头骡子内心的声音。
最后的羊群
羊,养到最后,只剩一群了。我没能从院门里赶出最后一群羊。
满屯子里的人都奇怪这些羊。大伙儿一门心思,想把几十群羊养得再多些,让它们变成比几十群更多的羊,让羊群赶上山时,变成一片白云,那一定和满山的桃花、杏花盛开一样美丽,我在桃花和杏花间行走,就像在羊群里行走一样。现在,羊群养着养着,怎么就变少了,少得直让人捂眼睛,院落里的羊圈都空了。最后,只剩下老向家一群了,好像羊群也没壮大多少。
先前,屯子里的养羊户从外地买来很多种羊,每家有几十只,屯子里一下子多出了几十群羊,满屯子里到处响起羊的咩声。许多屯人认为养羊可以致富,他们花大力气买来了种羊,想把羊养成院子里的鸡一样,让它们鸡生蛋、蛋孵鸡地发展。那样,屯子里的种羊生小羊,小羊长大了,再生小羊,屯子里的羊一定能形成更大的羊群。屯人多少年没做过一次重大决定,他们想做一次影响生活的重大决定,让屯子变一下模样,只是屯人没有养羊的经验,这让他们的羊群始终没有壮大起来。我肯定也没经验,我常常因为缺少经验做错事,我的屯人常常依靠经验生活在一个屯子里。
屯人大概认为养羊和养猫养狗一样简单了,这让他们没有太多的心理准备。当种羊开始产羔儿时,那些小羊几乎未能存活下来。后来,种羊也开始减少了。养羊户们心里有了忧虑,结果把羊群都转让出去,只剩下老向家一家了。老向家的羊成为了屯子里最后的羊群。我也没有那份心理准备,这让我没能为屯子多留下一群羊。
什么东西到了最后,难免会让人有失落感。屯子里最后赶出的牛,眼里含着泪走出屯子时,那个跟在牛身后的人心里会想个啥。老向的家人每天把屯子里最后一群羊赶出赶进一个屯子时,他们的内心是高兴,还是悲哀。所有的养羊户一定有着别样的滋味。我进入过许多屯子,有的屯子只敲出最后一对老夫妻,他们很陌生、惊奇地看着我。我碰见老向家的羊群时,那些羊好像也是这种目光。我在经过羊群时,我会用那种目光看着所有的羊,那使我为羊群感到羞愧。
我每天乘车上班的路上,常能碰见两群老山羊,被人忽左忽右地赶着上山吃草。它们一个个洁白而散漫。我已经许多年没看见那样多的山羊群了。我们屯子养的都是绵羊。绵羊吃草,个大;山羊也吃草,个小,肉味却更加鲜美,三舅说的,他现在生活富足,对很多事情极富经验。我好像没吃过真的山羊肉,吃过我也不知道,我把它们通称为羊肉。更小的时候我看过山羊,被屯人养着的几只,现在早就没人养了,不知山羊是否活着,我好像对生存有着强烈的渴望。三舅特意开车到百里外的山区买纯正的山羊肉吃。我开始怀疑我吃过的羊肉都是绵羊的肉,绵羊个大,肉多。我吃肉的时候,一直未辨别出来,可我知道,山羊太少,禁不住人吃。
现在,屯子里再没有羊声鼎沸的局面了,那些羊身上的腥膻味儿也淡了,它们随着羊群到了另外一个屯子,也许被风送到更远的地方,连羊也不知道,它们走不了那么远的路,对外面的世界好像也不清楚。老向家的几十只羊,沉默了许多,它们已经不能和屯子里的其它羊群打声招呼,连礼貌也省了。屯子里一下寂寞了许多。那些外出求学或打工的屯人,有时也会这样突然离开屯子,让满屯子的人感觉不自在。羊会不会不自在。你知道,我现在一个人留在了城里,我将独自面对生活。
谁能留下脚印
我在经过一块儿松软的田地时,总能留下一行清晰的脚印,这是我在一个屯子奔走的结果。
在一个屯子里,一定会常留下一些各种各样的脚印。在屯子松软或坚硬的土地上,我迈着或缓或急的步伐,去经管一块儿土地,去办一件日常事物,在一个屯子里闲逛,总有些脚印或隐或现地在我身后紧紧跟随,那是我在屯子里生活真实的影子。我们常常感念母恩,尤其感念母亲的乳汁。可土地给予我们粮食、水果、水、蔬菜……那些东西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除了母亲的乳汁外,仍然供养我们长大、生存的东西。那会让我想到:所有在土地上生长的东西,都是大地的乳房,那些能够供养我们生存的食物是大地母亲乳房分泌的乳汁。我们是大地众多孩子中的一个,它只是想把自己的乳房区分开来,像一头母猪腹下的众多乳房,左边的和右边的,前边的和后边的,本来没有本质的区别。母猪想让众多小猪能够准确地认出每一个乳房,及时吃到食物。大地也不想让自己的每一个孩子挨饿。
脚印被我一双双留在屯子的土地上,我的脚印或许和前面那个人的脚印重合,也许后面那个人的脚印和我的脚印重合,大地一直原封不动地保存着。每个人都想保留住一些记忆,无奈另一件事,或许是另两件事,影响了人的记忆,让人记不清。屯子里的风、屯子里的雨、屯子里的另一些动物会把脚印悄悄留下来,这让屯子里的土地记不起先前的脚印,让一些脚印没留下来。脚印不是真的消失了,它被另一些脚印占了,那些旧脚印在新脚印的下面,被巧妙地掩盖起来,我们看不清,土地也记不准了。它不能把先前那些脚印拿出来给我们看,土地被一茬茬的脚印扰乱了思绪,它想记下些新脚印,它现在也没时间给我们找了。
我喜欢光着脚走在一块松软的土地上。土地凉爽抑或温暖的气息会涌动于我的脚心,然后游走入我的心里。每一个居住在屯子里的人,大概都会有着这种经历。小时候,因为舍不得鞋里进土,磨鞋。每次在园子中翻土,准备种菜时大都光着脚在园子里用锹翻土,我的脚会浅浅地陷入土里,泥土轻轻地裹着脚面,土地凉爽而潮湿,让每一次陷入土里的脚印清晰而深刻。有时,我会光着脚在雨中行走,泥土细腻而质感地留住我的每一个脚印,然后在泥和脚之间发出轻轻的呻吟。
其实,屯子里的男人对脚印更感兴趣。多年前的屯子,每一户人家的男主人会在早晨起来时到院子周围走上一圈。头晚上,屯子里狗咬了好几次,或许院里或邻居的鸡舍炸群了,男人不放心,到院子外再仔细地走走,他想查看一下脚印。脚印会暴露一些危险的行踪。我无数次地和爷爷或父亲到过院外查看过脚印,那些脚印有人的、大牲畜的、狐狸的,还有一种可怕的爪印,那是狼的。我和长辈们查看久了,能够清楚地看出哪些是新脚印,哪些是旧脚印,哪些是人的,哪些是牲畜的,它们都有着各自的特征。从那些脚印中,我清楚地看出一头跑缰的驴,夜里在我家院外走了两圈半,然后斜刺里向别处走掉,它或许想找吃的,也许找家,天黑,看不清路了,我不知道。一头年轻的狼在院外踟躇地走了一半,就跑掉了,兴许它被狗的叫声惊跑了,年轻的狼没经验。我从那些院子外脚印的形状、大小、间距、深浅,细致地分析出每一种动物在我家院外的活动情况,让我家在另一个夜晚,有着必要的防范。
在一个屯子里,人的脚印再多,一定多不过牲畜的。人不能放下双手在一个屯子到处奔走。即使能放下双手,也一定多不过屯子里所有的动物。屯子里的一户人家平均有四口人,可是大概有一头猪,一条狗,七只鸡,一只羊,或许一头驴,两只鹅,一只猫,二十二只老鼠,三千六百只蚂蚁。人看得见,却数不清所有的动物,更无法计算出所有的脚印。我家院子里每年都要养上数十只鸡,它们每天都在院子内外到处散步、寻找食物,把无数只脚印留在屯子的土地之上。我好像永远也数不清它们留在大地之上的足迹。在脚印上,动物远比人走得塌实。
我在锄一片玉米苗时,我的脚印总会跟着我。我用锄让一垄垄玉米两侧的土地变得松软、透气,却不经意地把脚印留在一侧,我只好在返回另一根垄时,用锄一下一下把脚印在大地上重新抹去,我不想把脚印留在田里,那会让脚印下的那块儿土地不松软,脚印近前的庄稼感到土地有些僵硬。我想松松一块土地,让庄稼长起来。我怀着这样的想法一次次将我的脚印从一块块土地上锄掉,不留下痕迹。
我在一个屯子时,肯定不能长时间地留下一个脚印。我故意在屯子不起眼的角落留下许多的脚印,它们用不了多少时日,便消失了踪迹,找不到一点儿痕迹。我在屯子里留下时间最长的脚印,是在雨中留在墙角的泥脚印,我想探探那堵墙在雨里是否结实,走到近前, (下转第45页)
(上接第43页)把脚印留在了那里。那块儿地方一直没人去,脚印很深,足足一年半的时间,风和雨水才将它在那儿抹去,看不出模样。或许地里的草、几棵庄稼、一棵树会把一个个脚印先行顶破,继而抹平。屯子里所有的生物都有机会或能力改变一下事物的状态,包括脚印。
我一直认为坟墓是一个人在大地上最后的脚印。我的祖先从山东迁居到现在的屯子,不知有多少年没有回去过,风会不会把一座坟墓抚平,雨会不会把一座坟墓冲平,比我的祖先更早的祖先,他们的坟墓远在山东,已经不知有多少年没人管理了,不知它们是什么样子!我看见屯子里有些无主的坟墓会在许多年之后,被人夷为平地,没人理会。那会让我觉得:在一个屯子里,没有谁能留下脚印。
(责任编辑 王冬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