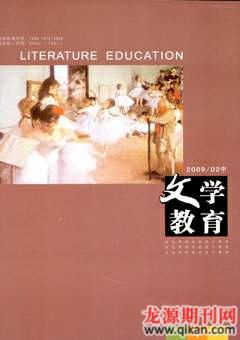浅议王安忆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摘要]当代女作家王安忆在涉笔性爱,使女性作品中的女性意识由社会层面发展到性别自觉阶段,达到了第一次飞跃和突破之后,其女性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并未仅仅停留在对内容的书写和挖掘上,而是进一步上升到对文本形式的改造和利用上。王安忆在其女性意识的发展过程中,成功实现了进一步突破,这奠定了她作为一个女性主义者的坚实的地位。
[关键词]人性;女性作品;女性意识
新时期以来,女性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得到了迅速发展。所谓女性作品,是女性创作的专门反映女性生活、女性心理与女性情感的作品。考察女性作品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女性意识。张洁、张辛欣等女性作家首开先河,张扬女性的自我意识。此后,又涌现了一批新的年轻女作家,她们重新审视女性自我的特异性,反思女性被压抑和被遮蔽的历史,重新认识属于女性自己的历史、心灵、情感、思想、文化以及语言。这是对女性自身角色的逐步体认和发展,也是女性意识的逐步深化。此时,文坛上林林总总的女作家构成了浩浩荡荡的队伍,推动着女性意识表现的进一步深化。但是,她们只是借助于当时的人道主义和启蒙主义思潮的“宏伟叙事”来阐发觉醒的女性意识,还没有真正以自觉的性别意识建立起自己作为女性审视世界的独特方式和角度,而实现这一突破性转变的作家正是王安忆,她最先把“性爱”引入女性作品,自觉的性别意识的引入引起了新时期以来女性意识发展的第一次突破。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她又自觉运用女性主义理论,通过女性话语的抒写,进行女性主义文本的建构,通过对语词的颠覆和对叙事功能的质疑达到对男权社会的颠覆和解构,实现了新时期以来女性意识发展的第2次突破。在此,就王安忆作品在表现女性意识中显示的特征作一探讨。
一、重新审视女性的生存价值
王安忆对女性的探索是完全涵盖在对“人性”的探索之中的,所以并不妨碍我们从女性批评的角度来阐释她的作品。1949年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氛围为千千万万的女性走上社会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为女性的基本生存权利提供了有力的保障。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就获得了彻底的解救。男女平等的法律权益,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男女两性的社会差异,尽管今天的时代大潮推动女性自我意识不断觉醒。在王安忆所塑造的女性身上也能发现这种状况。她的中篇小说《逐鹿中街》里的陈传青,在这方面就显得颇为典型。38岁的陈传青为了在50岁的古子铭那里实现自己“政治上依靠共产党,生活上则向中产阶级靠拢”的小康理想而结婚。结婚后,陈传青通过对家庭生活的精心安排与创造,对古子铭生活方式与习惯的训练与陶冶,来证明自己的身价,确认自己的社会地位。恰恰相反的是,这使她愈加落入自挖的陷阱。一个颇有素养的中年女教师,她一味地将目光紧盯着自己的丈夫,仿佛她的整个生命意义就是管住自己的男人。当她怀疑到丈夫有外遇时便采取了整天跟踪的愚蠢方式,为了虚荣自欺欺人,与丈夫演了一场无聊的游戏。王安忆通过对陈传青建设这个家庭过程的描写,深入地揭示了女性一味追求婚姻生活的致命弱点。她们只是把自己的生命意念局限于家庭、丈夫的囹圄中,根本没有意识自我价值的存在,也就更加谈不到去顾及其自身价值的实现了。王安忆对人性的关注是不断地更迭和演进的。在“雯雯的世界”,王安忆认识人性还基于个人情绪,甚至还带有几分天真、稚气的想法,那么紧跟其后的“直面现实人生”,王安忆就显得更冷静和从容了,她已把人性放在不可回避的人生百态面前进行解析。之后,当她通过男女情欲去展示人性,人性就显得更宏阔和犀利;当她在作品中深切地剖示女性的自我生命价值的意义时,其对人性解放的意义的感悟就越来越深刻。由此可见,王安忆的创作呈现一种不断跃升的势头,贯穿其中的是对人性探索的不断超越。
二、由社会意识上升到性别自觉意识
如果要研究中国新时期女性作品中女性意识的发展,就不得不先考察张洁和张辛欣的小说。她们的作品较早地反映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反映了旧有生活方式规定的女性性别角色与新主体意识的错位。无论是张洁的痛苦的理想主义还是张辛欣强悍的个人奋斗精神,它们所裹挟的女性意识都是十分狭隘和片面的,充其量是一种女性的社会意识,表现出女性对自身在社会生活中应有的地位的关注。女作家们注重的是人作为类对于自然的超越,是人的理性和社会性。她们刻画的人物总是要在社会的范畴内寻找生活的意义,女性意识更多地体现在追求女性自我价值方面。但这种女性只是简单地把男性作为攻击目标,把女性的主体意识融入当时所谓的人人平等的、“大写的人”这种思潮中去,忽略了对女性内心世界的描摹和对女性生命意识深层的开掘。王安忆是第一个大胆涉笔“性爱”禁区的女作家,她1986年前后所写的“三恋”(3个中篇小说《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在当时有着惊世骇俗、开风气之先的影响。不同于张贤亮等男性作家以性为工具,达到一种外在于文学主题的社会批判的目的,她更多的是直接地大胆地对性爱进行美好而自然的歌颂,这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感悟和吟唱。她首先肯定了作为人欲的性,率先突入“性禁区”,描写了一个个有爱和无爱的两性悲剧故事。“三恋”的核心视角就是写恋爱中的女性,写她们是怎样在这种“爱的冲突”中苦苦地挣扎,伴随着性意识的觉醒和成熟,又是怎样不断地与男性展开种种纠葛的,她们勇敢地承受着,孤独地思索着。这样的一群女性,“爱”使她们热情、盲目,但是也使她们体验到自己“身为女人的肉体的快乐”。王安忆不仅肯定人的自然本性——人类原欲中的性,而且还特别注重描写性别中的性,她是把女性放在两性关系中来表现的。表现女性的处境、心态、角色意识和自我超越精神,大胆地揭示了女性生命现象的内在冲突。
三、从自我情感的展示上升到对人性价值的重新审视
王安忆走上文坛后不久,就热切地关注人性问题。这使她的创作有了一个较高的起点,也使她的作品独具魅力。王安忆用她的艺术形象传达着对人性问题的见解,这些见解随着她的创作不断跃升而日益深化。她曾真切地写出自身“个人性”的影子,也曾超越时空反思不堪重负的历史文化;她曾把注意点投入到人性最敏感的区域“性”,也曾用冷静的目光审视女性自身。她在她的作品中营造出一个人性的世界,走进这个世界,我们会对人性问题有更多的感受、领悟。回顾王安忆的早期作品,虽没有对人性进行深入的剖折,但是作品字里行间把她个人的情感展露无遗。王安忆在她的早期创作“雯雯世界”里就具有关注人的心灵的倾向,也是她个人性格、经历的写照。这一类的作品大多收在短片小说集《雨,沙沙沙》中。这一时期的作品向人们展示了处于动乱多变的复杂环境中纯性少女的缠绵而又激荡的心灵,是一个青年女性作家笔下的女性青年对真挚爱情和温馨生活的深情呼唤,也可以说是一代纯真而又迷惘的青年少女的共同心声。虽然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中,王安忆对人性这样复杂而又危险的话题还不可能有明晰而自觉的认识,这种对人性的开掘还停留在对自我个人情绪的展露,还较肤浅。处处浸渍着自身经历的影子。尽管这时她对人性问题的认识还不是很自觉的,但她
常在不经意中在人性领域燃爆某些闪亮点。人性问题固然与人的内在情感有关,但它绝不是
四、对乡村女性的人文关怀
新世纪以来,女性作品从近年商品化的大潮中呈现出的畸形的虚假繁荣中渐渐挣扎出来,评论界也从高唱女性作品赞歌的喧嚣与浮躁中缓缓平息。她们展示了不断从误区中突围的姿态,女作家从“精英主义”、“个人”、“私语”等写作心态的困境中走出来,结束了面对现实长时间的失语现象而完成了对现实主义的回归。尤其是王安忆、方方、池子建描写乡村女性的力作纷纷出现,联系着女作家新的精神指向和心灵期盼,同时也给读者带来了丰富的美学感受和意义启迪。
五、结束语
不容置疑,新时期的女性作家中,在对女性意识的表现和张扬上王安忆是卓有成效的一位,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其作品在女性意识的理解和审视中还有着一定的局限甚至是缺陷。缺乏一种批判的眼光是王安忆在女性意识展现上一个重要的缺陷。当她自觉采用一种民间的叙事立场时就更应具备此种眼光。可是,在她对王琦瑶们的生存形式完全表示认同的时候,我们除了发现作者与王琦瑶一样具有某种倾向上层社会生活的虚荣之外,竟丝毫感受不到她理应具有的批判情怀。“民间”是一个能够激活人类想像的概念,也是一个藏污纳垢的概念,借用一句耳熟能详的老话,就是“民主性的精华和封建性的糟粕”往往混同在一起。因此,创作者只有把知识分子本应具有的批判意识带入广袤的民间大地,民间才会焕发出别样的生命活力。当然,这不是王安忆个人的失误,而是整个20世纪90年代文学在民间重塑问题上的失误。同时,在王安忆炉火纯青的叙事技巧中,人物失去了应有的光芒。王安忆擅于把纸上的世界描绘成一个心灵的世界,她的小说往往沉浸在历史真实的精雕细刻之中。然而,一部好作品的意义永远在版本之外,对技巧和形式的研究无法洞察其真正的价值,构成作品高贵品质的一切,是主人公身上所散发出来的美妙的光泽。在《长恨歌》中,王琦瑶所有的命运宛如一场游戏一场梦,李主任也好,康明逊也好,萨沙也好,长脚也好,老克腊也好,都是游戏和肉欲的结果。在这一间没有光亮的屋子中,没有激情,没有血性,没有时间的倒错,没有季节的变换,没有时代的变迁,只有梦魇和夜晚。尤其是王琦瑶,无肝无肺、无情无义,稀里糊涂地上床,无缘无故地做爱。叙述的语言表面上细腻,其实是白头宫女说闲话,没有一个人物有灵魂。
参考文献:
[1]王安忆.长恨歌[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
[2]安映洒.论王安忆作品对人性的探索〔J〕. 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2(2):21.
[3]张敏.“她”的自塑—论新世纪以来王安忆、方方、迟子建笔下的乡村女性〔J〕. 平原大学学报 2005(4):12.
[4]孙俊青. 新时期文学中女性意识发展的两次突破——论王安忆小说中女性意识的历史地位〔J〕. 贵州社会科学, 2006(3):8.
作者简介:彭恬静,湖南益阳人,广东金融学院助教,汉语言文学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