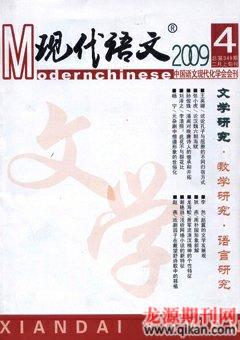当代文学史书写与“回到文学自身”
彭 丽
摘 要:我国当代文学史的编撰在新时期一直呈繁荣的局面。吴培显先生的《当代小说叙事话语范式初探》另辟新径,从叙事话语范式视角对中国当代小说史进行新的梳理。它联系中国当代文坛内外因素,集中研究中国当代小说的各种叙事现象,突出了小说作为叙事艺术的特征,对中国当代小说史进行了“另类”书写。本文粗浅分析该书的著述特色,阐述其在中国当代小说发展研究中具有的开拓性意义。
关键词:吴培显 当代小说 叙事话语范式 历史语境 “另类”书写
中国当代文学历时50余年,历史虽算不上漫长,但学界对“中国当代文学史” 的研究和撰写却一直呈现出繁荣的景象。这首先表现为文学史著作和教材的数量之多,更突出了中国“文学史大国”的称号;其次表现在编撰思路和体系的花样翻新上,学者们往往试图按照自己的文学史观和对当代文学的理解力图构建新的文学史框架体系。但是,文学史观以及学术研究的惯性思维模式使得当代文学史著述又总难免体系僵化的缺憾和大同小异的单一感,难以跳出一种传统的陈陈相因的体系模式,用吴培显先生的话说,即套用社会历史阶段分期的框架而做“填充式”研究的“泛王朝体系”的文学史模式。正如中国古代文学一般是以王朝更替为文学史分期界线一样,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也大多以建国后的几次“重大历史事件”为分期界线来划定若干阶段,实质上仍是沿袭“泛王朝体系”模式,使得文学自身发展演进的轨迹被历史事件生硬切割,“文学史”失去了“文学之史”的本然意义。同时,百年来文学史研究中带有普遍性的另一问题是文学史缺乏“灵魂”,“缺乏足以支撑一部文学史的核心范畴,缺乏明确的、贯穿性的理论评价体系和价值标准。”[1]正是在这样的文学史研究背景上,吴培显先生的《当代小说叙事话语范式初探》(以下简称《初探》)对中国当代小说发展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开拓性意义和丰富促进的贡献。
《初探》以西方叙事学为参照系,详尽地考察了当代西方叙事学的发展历史,深究了结构主义叙事学与叙事文学的结构与批评原理,肯定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的优点,同时对它的缺憾和局限提出了批评。叙事学理论将文本看作一个不受外部规律制约的独立自足的封闭体系,极力摒除制约具体的叙事法则的社会、历史、作者意图和心理因素等对作品的干预。按照文学创作规律,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都不可能独立于外部环境而孤立存在。因此,叙事学由于隔断作品与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的关联,形成了狭隘的批评立场。吴培显先生在全面分析、比较西方叙事学的优劣长短之后,开创性地提出了“叙事话语范式”这个理论命题。该命题借鉴西方结构主义叙事学的研究成果,既注重文本内在,又强调文学内外因素的相互作用,注意考察叙事行为背后所隐含着的主体性和社会性,关注社会、文化和历史环境对一部作品的影响,从纵向或横向的方面客观公正地考量文本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叙事话语范式”保留了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的优点,弥补了它的不足,融合了认知范式、讲述范式和语体范式,拓展了西方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这样,相比之下,《初探》的理论框架既显得更为合理,更具有辩证色彩,显示出独特的理论风姿,同时又自成体系地从叙事话语范式视角切入,对中国当代小说史进行了新的梳理,联系当代文坛内、外因素,集中研究中国当代小说的各种叙事现象,突出小说作为叙事艺术的内在特征。
吴培显先生指出,曾有理论家在探究文学内在规律时得出这样的结论:“就美与艺术的创作来说……无论创作之前和之中都是在某种‘范型的支配和规范下进行的”[2],当代小说同样如此。无论是具体作家的创作历程,还是某一阶段上的群体创作特征,当代小说大都体现着某种潜在“范型”的支配和规范。从建国初期的文坛来看,对创作起支配和规范作用的主要是这样两种“范型”,或者说两种“叙事话语范式”,即牧歌叙事话语范式和正反对举叙事话语范式。这也是中国小说进入“当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即小说创作整体上纳入了“牧歌”和“正反对举”叙事话语范式的支配与规范之中。[3]《初探》认为,研究小说,不能不在叙事研究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因为小说是一种叙事文体。在某种程度上讲,小说创作的理论就是关于叙事的理论,小说美学就是叙事美学。而小说这一文体的发展,从远古神话、传说,到传奇、话本,再到成熟形态的古代小说、新小说,以至现代派小说,也首先表现为叙事艺术技巧这一形式要素的发展。”[4](p28)因此,面对浩繁的当代小说,论者选择从文坛整体动态和具体创作实践层面,对当代小说的叙事话语进行了综述和评析。《初探》体系严谨,结构合理,且宏观把握与微观考释并重。在对整个中国当代小说发展进程的历时性梳理中,论者发现并概括出了以下几种主要的叙事话语范式:牧歌叙事话语范式、羽扇纶巾叙事话语范式、正反对举叙事话语范式、思辨叙事话语范式、叙事崇尚叙事话语范式、提纯叙事话语范式和直击欲望叙事话语范式等。文学创作是人类有意识性和目的性的创作活动。作家对文坛的整体背景的认知不尽相同,导致了他们在叙事层面上也各不相同,因此叙事话语范式具有多元性特征和动态变异性特征。于是,这些划分在具体实践中又被细化,以期对中国当代小说叙事发展进行更为准确的跟踪式批评。《初探》通过分析不同时期小说在叙事层面的不同探索,揭示小说叙事话语的演变轨迹,从而彰显出当代小说被以往研究所遮蔽的一些层面。
《初探》首先对“牧歌叙事话语范式”作了厘定,并认为这一叙事话语范式可以作为“对1962年前当代文坛整体叙事话语范式的一个概括”。[5](p46)即所有文学形式都在主导意识形态规约下组成对中国新生活的“颂歌”大合唱。在20世纪50年代的小说创作中,不论是以城市为题材的浪漫化“青春牧歌”叙事话语,还是以反映农村生活的新时代新气象的牧歌叙事话语,都充满了喜逢盛世的热烈礼赞。以致这种意识形态化的大众狂欢话语与严峻的现实生活形成强烈的反差,“牧歌”所具有的天然、纯化、理想色彩等本质完全蜕变,“小说创作成为图解新政权、政策的工具”。[6]与许多文学史论著不同的是,吴培显先生认为20世纪60年代初期之前,所谓“阶级斗争”在当代小说创作中的体现是十分微弱的,它并未改变小说叙事的话语方式。很多人以为“整个十七年的文学旋律就仅仅是阶级斗争的鼓角和两条道路的火并厮杀声”,而《初探》则认为这是对十七年文学总体基调的一种误读。其依据就是“两条道路的斗争仍基本定性在认识和观念的分歧上”、“关于生活矛盾和冲突的讲述,其效果恰恰是强化了其叙事话语的和谐色彩和牧歌情调。”[7](p50)吴培显先生以浩然为典型个案具体分析了以1962年为界的文坛叙事话语的这种转向。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主导意识形态的调整,文坛的叙事话语范式开始整体转向,由太平盛世的牧歌叙事话语转变为对抗、仇恨叙事话语。如浩然的叙事话语范式就是从最初构建的集体化田园牧歌的“金光大道”上,逐渐走向“希望自己的每一部作品都是真正的阶级斗争的武器”[8](p51)的认知歧途。论者还细致地考释了以王蒙为代表的“浪漫化青春牧歌”叙事话语,非常敏感地从王蒙对“官僚主义者形象”的刻画中捕捉到了一种潜在的倾向,即林震对党的领导机关干部形象的浪漫化理想化的设计中,暗含着“作家以及作家所代表的一代青年的认知范式的影子”。[9](p56)
论者对“争先”风尚牧歌叙事话语的把握非常精准,抓住了这类叙事话语的主旨意向,即“着重看取生活横断面中的‘新的因素”,[10](p59)如谷峪的《新事新办》反映了移风易俗等社会风貌和人物心理,蕴含着历史性变革的意义。《初探》从叙事话语范式角度客观地肯定了这部作品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和作用。但在王汶石的《新结识的伙伴》中,因为作家刻意强化这种“争先”风尚,这一叙事话语范式烙上了极“左”的浮夸印记。在阐述集体化田园牧歌叙事话语范式时,论者探究了浩然式集体化田园牧歌形成的原因,浩然的一生都对集体化有无法释怀的深厚崇拜情结,他在创作中刻意粉饰和美化农村生活现实,即使在集体化遭受严重挫折时,他的叙事中也一如既往地洋溢着祥和与温馨之气。然而,赵树理以一个作家的良知和冷静,清醒地发现了集体化背后的某些潜在的负面因素,并在创作中秉承一贯的现实主义精神,把这些消极因素展示出来。于是,赵树理式的乡村牧歌叙事话语就与当时文坛主流的叙事话语范式格格不入,属于“不和谐旋律”的乡村牧歌叙事话语范式。论者高度赞扬了赵树理的现实主义精神,但对他正面讲述的干部们的做法表示了怀疑。进入新时期,牧歌叙事话语范式又焕发出新的活力,传递出新时期的新政策给农村和农民带来的喜悦与忧虑,反映了时代民众的心声。
战争题材小说在文学史上一直层出不穷。由于受文坛内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形成了不同的战争叙事话语范式。《初探》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此类题材小说中总结出了“战争牧歌叙事话语范式”。新中国经历了浴血奋战才建立,因此20世纪50—80年代中期,英雄崇拜和英雄主义精神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文化主旋律,既而文坛整体创作中也充满了英雄崇拜的认知和审美倾向。在分析了这种叙事话语范式产生的背景之后,论者接着指出这种叙事话语范式与传统小说叙事的全知全能讲述之间存在的差异,在这里作家不仅是西方叙事学中全能的上帝,还担当了“英雄”的代言人。同时,论者还将在叙事中充盈着理想英雄的本色和气概的抗战题材小说,概括为“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叙事话语;讲述解放战争的小说突出英雄共性,强化英雄意志,凸现英雄的传奇色彩,是“班师英雄的传奇式”叙事话语。
对于在小说创作发展史上源远流长的“正反对举叙事话语范式”,论者更是花了大量的篇幅和笔墨。以1962年为分水岭,正反对举叙事话语范式在当代小说中经历了一个从“先进/落后”对比到“好人/坏人”对抗的模式转变。其中独树一帜的是柳青的《创业史》中的正反对举叙事话语,避免了简单化和表面化,具有独到深广的艺术意蕴。这种叙事话语受传统因素的影响,人们在接受惯性中形成了“非此即彼”的简单二元对立审美心理和判断法则,束缚了小说叙事艺术的发展。这种倾向在“穷人/富人的宗族复仇式正反对举叙事话语”、“楚河汉界式正反对举叙事话语”、“煽仇式正反对举叙事话语”体现最为显著,人物活动被按照阶级属性机械演绎,故事讲述图解先验逻辑,强化阶级斗争的“激烈、复杂、尖锐”。正反对举叙事话语的这种先验的阶级属性定位的弊端,在新时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和反腐小说中得到延续,造成了小说人物形象性格简化、作品审美内涵淡化。
此外,《初探》对文坛上出现的新型叙事话语也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概括。思辨叙事话语范式中,以物质生活准则论折射出历史的发展与进步的悖谬性;在善/恶二元基础上的历史文本重读式叙事话语中仍带有先验的善、恶冲突色彩;正统历史观念的解构式叙事话语,用历史偶然性消解历史必然性,解构了传统历史小说的宏大叙事。文化思辨叙事始终灌注着历史使命意识,审视传统文化,批判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而人本思辨的兴起标志着文坛整体上的文学观念的变更,摆脱了两极化的思维方式,疏离了种种非文学的外在干扰性因素,从而让文学本质特征的观念回归到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之中。叙述崇尚叙事话语范式的出现对小说创作的文体自觉产生了革命性意义。80年代中期的小说创作虽然大多表现出一种共同性的叙事崇尚,但《初探》注意到了它们不同的意义取向,具体分析了东方意识流叙事话语、迷宫式叙事话语和蕴藉化叙事话语三个基本范式。通过与西方意识流的比较,挖掘出东方意识流叙事话语充满着理性控制色彩的特质。结构崇尚与叙事展开的拼贴式、迷宫式叙事话语对“现代形态小说”的生成功不可没,但在现代形态的探索中,叙述崇尚也逐步走向了极端化,沦为某种艺术的文本空壳。人性礼赞的简约化、蕴藉化叙事话语弥补了前两类范式的局限和弱点,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便是最有力的证明。然而以往研究界对汪曾祺的小说评价视点仅限于“文化”层面,吴培显先生从“抒情的人道主义”视角透视出汪曾祺独特的人生观念和认知方式,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范式与人生姿态。
社会的转型形成了多元价值观和文化观,新时期文坛对这一现象迅速作出反应,新写实小说改变了关于“人”的观念,认为“万物”是“人”的尺度,形成了非牧歌叙事话语范式,对中国文学发展构成了一次大的超越。提纯叙事话语范式是思辨叙事话语范式带有极端倾向的产物,对抽象意义上存在的“人”的认知,为读者提供了新的审美体验和感受,如余华和残雪的小说。吴培显先生赞许了抽象提纯叙事话语范式为文学的“认识自我”开创了新的认知方式,开拓了文学的想象空间,批评了该叙事话语疏离历史语境的“主观真实”的缺失。
总之,经过作者细致入微的分析和精辟论述,作为全书核心范畴的“叙事话语范式”得到了新的阐述,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同时,透过作者的论述,我们也察觉到了中国当代小说研究中一些被遮蔽、被忽略的事实。论者从叙事学的层面对小说的发展史进行历时梳理,这不啻引入了新的研究小说的角度,也是对当代小说史的“另类”书写。它让我们明白,“当代小说的自身运行轨迹,并非完全循着社会历史的阶段性更替而变化,而是与叙事话语范式的演进密切关联的。中国小说史进入‘当代阶段,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小说创作自觉或不自觉地纳入、置于‘牧歌和‘正反对举叙事话语范式的支配和规范之中;恰是这两种叙事话语范式的延续、递嬗和分化,构成了新时期小说的演进和繁盛,而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小说的现代形态的形成,又是与对这两种叙事话语范式的超越和解构相伴随的。”[11]
注释:
[1]吴培显:《文学史观的局限与盲点》,《理论与创作》,2005年,第2期。
[2]赵宪章主编:《西方形式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7-48页。
[3][11]吴培显:《当代小说的演进与叙事话语范式的分化》,《创作评谭》,2005年2月号。
[4][5][7][8][9][10]吴培显:《当代小说叙事话语范式初探》,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6]龙其林:《当代小说史观的理论拓展——评吴培显〈当代小说叙事话语范式初探〉》,《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3期。
(彭丽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41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