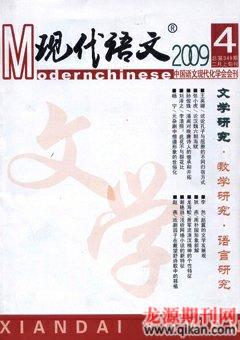浅论鲁迅笔下“看客”形象的悲剧意蕴
李 楠
摘 要:看客是鲁迅作品中具有代表意义的一类人物形象,在看客身上表现出深厚的悲剧意蕴,本文从三个方面分析了看客形象的悲剧意蕴:人性毁灭的悲哀;民族历史的悲哀;特定时代的悲哀。
关键词:鲁迅 看客 悲剧意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一些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但是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吗?”[1]这是在面对钱玄同先生“做点文章”的邀请时,鲁迅做出的回答。尽管如此,经过深思熟考虑,鲁迅还是拿起了手中的笔,从此直到1936年离世,他的生命再也没有同推翻这个“铁屋子”的努力和奋战分开过。尤其是1918年到1925年,这期间鲁迅创作的26篇小说结集为《呐喊》和《彷徨》,成为他小说的代表作。这些小说主要是以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状况为主题,但是很少描绘社会生活的外在情状,而是直指人物内心,他的小说“多来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2]。所以在鲁迅的小说中,他着力于揭露阴暗的国民性,看客便成为了小说中极其重要的一类人物形象。在鲁迅收入《呐喊》、《彷徨》的26篇小说中几乎三分之二的小说都不同着墨地勾勒、描画了看客形象,其描写的看客人物众多,层次繁杂,组成了一个看客群落,具有泛指意义。鲁迅在小说中,用几近残忍的笔触,白描看客形象,勾勒看客灵魂,从而揭示了深刻的悲剧意蕴。
一、表现了人性毁灭的悲哀
对于看客,鲁迅曾经下过一个悲观性的结论:“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3]对这遍地皆是的麻木看客,鲁迅可谓痛心不已。麻木之外,这些看客似乎更热衷于从别人的悲哀中咀嚼快乐,这更是人性毁灭的悲哀了。《祝福》中,祥林嫂第二次回到鲁镇,逢人便讲述阿毛的故事,“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直到她说得呜咽,她们也就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地去了,一面还纷纷评论着。”祥林嫂失去丈夫和儿子的悲惨遭遇并没有引起这些看客的同情,她们来只是为了在品评鉴赏祥林嫂的悲惨遭遇中得到一种自我满足。不但如此,当阿毛的故事被咀嚼成为渣滓后,这些看客们不约而同地开始在祥林嫂身上寻找新的看点。善女人柳妈提出了祥林嫂额角上的伤疤的问题:“你额角上的伤疤,不就是那时撞坏的吗?”“你那时后来怎么竟依了呢?”并且提出了一个更加尖锐的问题:“祥林嫂,你实在不合算,再一强,或者索性撞一个死,就好了,现在呢,……你将来到阴司去,……阎罗大王只好把你锯开来,分给他们。”正是善女人柳妈提出的这个问题,使得祥林嫂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最终精神崩溃,走上了死亡的道路。在《祝福》中,看客们仿佛已经丧失了作为一个人的基本同情心和人性美,他们齐心协力地把祥林嫂推上了死亡的道路。当这些看客以个体的面目在作品中浮现出来的时候,他们的内在欲望便凸现了出来。与《祝福》不同,《阿Q正传》中的看客,多是以一种嘲讽,戏谑的形象出现的。对于阿Q的疤癞头,未庄的人们一见面便假做吃惊地说:“哙,亮起来了!”“原来有保险灯在这里!”直到阿Q被揪住黄辫子,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闲人这才心满意足地得胜走了。阿Q成了一个类似于小丑的角色,但同时,阿Q也是作为看客而存在的。在城里看了杀革命党之后,阿Q到未庄眉飞色舞唾沫横飞地讲述:“你们可看见过杀头吗?咳,好看。杀革命党。唉,好看好看……”因为这一节,“阿Q这时在未庄人眼中的地位,虽不敢说超过赵太爷,但谓之差不多,大约也就没有什么语病了。”富有戏剧性的是,阿Q最终也成为了被杀头的人,而且围着阿Q观看的人并不理解阿Q何以要被杀头,也没有任何人同情阿Q,他们只是拿他的杀头当一出戏看,听到阿Q说出半句话来便喊好,而城里人还“多半不满足,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而且那是怎样一个可笑的死呵,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一句戏:他们白跟一趟了。”在看客身上,丝毫看不到人性的光辉,我们能感受到的是看客的是非感、正义感和同情心的缺乏,甚至是类似于野兽的野蛮习性,他们不但会咀嚼人们的肉体,而且会吞噬人们的灵魂。
二、再现了民族历史的悲哀
国民性的形成必然有其漫长的过程,看客行为也是如此。因此鲁迅描写看客群落的悲剧并非仅停留于人性毁灭的悲哀的揭示上,而是从更深更广的历史角度,表现了一个民族历史的悲哀。在漫长的封建宗法制社会中,统治阶级垄断了教育,使用儒家思想来实行愚民政策,加上特定的生产方式的制约,民众形成了一种麻木不仁无聊散漫的精神状态。这样的精神状态造成了民众精神生活的极端空虚和无聊,在这种情况下,稍有可看之事物,民众们就会蜂拥而至。除此之外,历史上长期的愚民政策也使得国民产生了强烈的盲从心理,鲁迅举例说:“倘使一个人,在路旁吐一口唾沫,自己蹲下去,看着,不久准可以围满一堆人;又假使又有一个人,无端地大叫一声,拔步便跑,同时准可以大家都逃散。”[4]正因为如此,才产生了大批的看客。于是就有了《示众》这样一篇专门表现看客众生相的小说。一囚犯被警察牵着在街上示众,立刻引来无数看客围观。最先发现的是一个叫卖馒头的“十一、二岁的胖孩子”,他“像用力掷在墙上而反拨过来的皮球一般,他忽然飞在马路那边了”。紧接着其他人也很快围了过来,霎时间就围了几层的看客,水泄不通,“续到的便只能屈在第二层,从前面的两个脖子之间伸进脑袋去。”这些人围在一起,初为看囚犯,很快便互看起来。看客们看相丑陋,“有一个瘦子竟至于连嘴都张得很大,像一条死鲈鱼”。而正当这帮人看得无聊之时,不远处一个车夫摔了个跟头,竟引来几个人同声喝彩:“好!”“连巡警和他的牵着的犯人也都有些摇动了。”车夫成了新的看点,很快,车夫离开了,“大家就惘惘然目送他。起先还知道那一辆是曾经跌倒的车,后来被别的车一混,知不清了。”这就是小说《示众》的主要内容,整篇小说没有情节没有主角,所展现的只是看与被看。在看客中,有卖馒头的孩子,有小学生,有老头子,有胖大汉,有工人,甚至还有抱小孩的老妈子,可以说涵盖了各个年龄段各种身份的人。由此,“看”便成为一种社会化的行为,显示出看客这一群体牢固的历史和社会根源。
三、揭示了特定时代的悲哀
人物形象之所以鲜活,是因为这些人物具有时代的特色。鲁迅在再现看客的历史悲剧意义的同时,也表现了那个特定时代的悲剧内容,特别是辛亥革命失败的悲剧根源在这些看客身上表现得相当鲜明突出。在《药》里,革命者夏瑜抱着解放群众的心愿而被杀戮,但他的牺牲非但没有得到民众的同情和理解,反而成了被赏玩被谈论的对象。《药》中的看客们为了看杀革命党夏瑜,天不亮就聚集在一起,“一阵脚步声响,一眨眼,已经拥过了一大簇人。那三三两两的人,也忽然合作一堆,潮一般向前进;将到丁字街口,便突然立住,簇成一个半圆”“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在对这些看客聚光灯似的描写中,可以看出看客是多么的愚昧落后,他们不仅不对刽子手投以仇恨的目光,不仅不对革命者报以同情和理解,而且以观赏为乐事,一个个看得津津有味。更令我们感到悲哀的是革命者的血最终被自己想要拯救的对象——愚昧的民众当作药给吃了下去。如果说刽子手给予革命者的是身体上的屠杀,那看客们给予革命者的则是精神上的虐杀!另外,还有《风波》里许多不知名的人对革命的迷惑,《阿Q正传》里许多看客对革命的看法,都带有鲜明的时代悲剧内容。正因为辛亥革命没有从根本上铲除封建势力,没能看出革命的真正力量,革命只能是一个“无根的花环”,革命以后“招牌虽换,货色依旧”,因而悲剧也就势所必然。看客的麻木、无知正是这一时代悲剧内容的鲜明表现。
看客群体是鲁迅向中国文学画廊贡献的一群生动深刻的形象,通过鲁迅笔下的看客,我们深切地了解到了中国时代的悲剧。这不仅仅在当时有着深刻的意义,现在,我们仍然可以从鲁迅笔下的看客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只有看客不存在了,中国人的人性才能算是真正的升华了。
注释:
[1]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9页。
[2]鲁迅:《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12页。
[3]鲁迅:《娜拉走后怎样》,《鲁迅文集(第二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0页。
[4]鲁迅:《一思而行》,《鲁迅文集(第五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6页。
(李楠 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人文系 255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