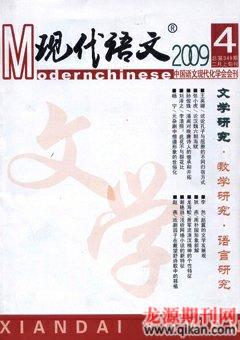论《文心雕龙·体性》篇中的风格说
摘 要:风格是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对于风格的本质古今中外历来有着不同的看法。在我国古代最早专门论述风格的文章是刘勰的《体性》篇,刘勰通过对风格与作家个人气质、创作个性、后天学习等三方面关系的分析,提出了比较完整的古代风格理论。
关键词:《体性》 个性创作 风格
风格是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风格”一词源于希腊,本意为“雕刻刀”,后来引申为表示组成文字的一种特定方法,或以文字装饰思想的一种特定方式。后来引申到文学领域里,风格指主体与对象、内容与形式的特定融合。文学风格就是作家创作个性与具体话语情境造成的相对稳定的整体话语特色,是一个作家创作成熟的标志,一部作品达到较高艺术造诣的标志。
一、风格与个人气质
对于风格的本质古今中外历来有着不同的看法。一种是偏于形式方面的理解;一种是“文如其人”与“风格即人”的观点。扬雄认为言为心声,从诗文里可以看出人格的高低。钱钟书认为文格不等于人格,不能一味的以文观人。他认为文如其人的“文”,不是指的“所言之物”[1](P163),而是指作品中的格调,格调是作者的性格“本相”的自然流露。布封认为,风格“仅仅是作者放在他的思想里的层次和调度”[2],与作品的表现对象无关,“风格却就是本人”[3],即是一个作家的创作个性。“风格即人”论者重视生成风格的内在因素,比较忽视风格与客观内容的联系。歌德认为风格必须“奠基于事物的本性上面”[4]。马克思既肯定了文学风格的“精神个体性”[5]的本质特征,又肯定了风格的客观属性,认为文学风格就是作家用客观事物本身的语言表达和突出客观事物的本质特征的同时,表现自己精神个体性的形式和方式。
在中国古代,风格的概念出现较早,时间大概为汉魏,起初称为“体”,但并不是用来品文的,而是用来品人的:评价人的体貌、德性和行为特点。到了后来,则慢慢涉及到文学艺术的领域,据后来的专家学者研究,陆机的《文赋》“夸目者尚奢,惬意者贵当,言穷者无隘,论达者唯旷”,在将风格问题进一步引入文学理论起着重要作用。
但真正最早专门论述风格的文章却是刘勰的《体性》篇,刘勰的“才性说”是在前人所提供的资料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但他并不是因袭前人的旧说,而是在前人的基础之上经过整理和改造后才提出的。
《体性》篇中的“体”是指体貌、风格,“性”指作家的才性。“体”是表达“性”的工具,“体”与“性”是文学作品的形体和性情,形体不能离开性情而凭空产生。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描写与构思愈相符合,或者用更普通的话说,艺术作品的形式同它的思想相符合,那么这种描绘,就愈成功。”[6]。《体性》篇又说:“赞曰:才性异区,文辞繁诡”,就是说由于作家的气质和才性不同,从而构成了不同的作品风格。
《体性》篇“才性说”的内容包括才、气、学、习四事,但是在中国古代真正把“气”这一概念引进文学领域的是曹丕。他在《典论·论文》中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论孔融,则说他“体气清妙”,论徐幹,则说他“时有齐气”。这里的“齐气”,人们一般认为是文章的气势所形成的风格特征。《典论·论文》所标示的“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正是指明气是形成作家创作个性的基本元素。这一看法得到了刘勰的赞赏,在《体性》篇中写到:“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吐纳英华,莫非情性”,“岂非自然之恒资,才气之大略哉”,进一步阐明了这点。就作家的创作个性来说,“气”相当于气质,属于天资秉赋,不可强力而致。就作品的风格表现来说,“气”相当于气韵或语气,可以比之为音乐中的格调音色。语气、格调或音色是作家的气质在创作对象上的情绪投影,作家的创作个性是形成作品的内在动因,格调、色彩、气势、节奏、题材、意象等构成的具体的话语情境是作品风格的外在表现。它显示了作家观察生活时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为他个人所独有的的特征。作家的创作个性,无论通过怎么样的渠道,终究要在作品中表现出来,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这就是风格的主观因素。作品的体裁规定了结构的类型,从这种体裁本身出发,要求作家必须顺应它的特定风格,而这种特定风格是不以作家的个人意志转移而转移,因而是排斥主观随意性,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这是风格的客观因素,也是造成风格稳定性特点的主要原因。风格的主观因素是通过风格的客观因素而表现出来的,二者并不是坚硬对立,毫无关系的。所以我们可以说由作家创作个性所形成的个人风格在主客观因素作用下体现了不同作家内在气质的差异性。
二、风格与创作个性
《体性》篇“才性说”并不是仅仅限于论述“才”与“性”这两个概念,而是通过这两个概念统摄了更多的广泛内容。这在本篇一开头就说的很清楚:“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分析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刘勰在文章的开篇就已经道出了以下几层意思:首先在于阐明了内外之旨,即文学的内容和形式关系。其次,这种内在关系是专门就作家的创作个性和由此形成的作品风格而言的。再有,就作家的创作个性的构成因素来说,包括才、气、学、习这四种因素,或情性所铄与陶染所凝这两个方面,构成了作家的创作个性。最后,作家的创作个性由隐以至显和因内而符外的艺术规律,就形成了笔区云谲,文苑波诡的无限多样化的不同艺术风格。本篇下文又称:“吐纳英华,莫非情性。”并列举了贾生等十二家为例,以证明创作个性和艺术风格“表里必符”的原则。明代的李卓吾也有过类似的观点,他说:“性格清澈者音调自然宣畅,性格舒徐者音调自然舒缓,旷达者自然浩荡,雄迈者自然壮烈,沉郁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绝。”(李卓吾《焚书·杂述·读律肤说》)可以认为是对于刘勰观点的进一步发挥和延伸。黑格尔则更加肯定了风格与个性的关系的。他说:“风格一般指的是个别艺术家在表现方式和笔调曲折等方面完全出他的个性的一些特点。”[7]
风格与创作个性有着密切的联系。刘勰认为文学作品是作家才性的表现,因此必然显示作家的个性。创作个性是作家在创作实践中养成并表现在他的作品中的性格特征。这种性格特征,是作家的世界观、艺术观、审美趣味、艺术才能以及气质秉赋等综合形成的一种习惯性行为方式的表现。时代是培植作家创作个性的气候和土壤,不同性格造成作品的不同风貌。
三、风格与后天学习
在《体性》篇[8]中刘勰认为作家的才性包含才、气、学、习四个方面,四者的不同决定了作家创作个性的不同。其中才、气是先天的禀赋,学、习是后天的努力。“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就是说要把来自先天的才气再经过学习的熏陶和磨练才可以构成作家的创作个性。本篇所说的“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以及《神思》篇“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事类》篇“才自内发,学以外成”,都是在说明先天的禀赋还需经过后天的锻炼。《体性》篇末“夫才由天资,学慎始习,斫梓染丝,功在初化,器成采定,难可翻移”,这句话表明刘勰十分重视教训的功能,逐步积累的作用。《体性》篇赞中说的“习亦凝真,功沿渐靡”,就是以为习惯一旦养成就很难翻改,渗透在性格中成为定型。这种情况在作品里面就会由作家的创作个性形成一种特殊的作风。因此,如果不在学习过程的开始就注意“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那么这种风气就会变成不好的习气。例如《体性》篇所列举的八体中的“新奇”和“轻靡”两体,前者“摈古竞今,危侧趣诡者”;后者“浮文弱植,缥缈附俗”,就是这种情况。可见刘勰认为风格的形成是先天禀赋和后天努力的结合所致。
风格形态是作家创作个性表现在作品中的客观存在形式。风格的形态异常繁多,就表现的内容、方式和效果等不同的情况,刘勰认为风格千差万别,但可以归纳为八种类型: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轻靡、新奇。八类又可分为互相对应的四组: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包含了一定的辩证法因素。文学的基本风格虽只有这八类,但作家可以根据个人的特点吸收、融汇诸家之长,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刘勰另有《定势》篇,着重论述风格形成的客观因素,《时序》篇则论述了时代风格,文体论各篇也论述了各种文体的特殊风格。
综合来说,刘勰《文心雕龙》建立了相当完备而丰富的风格学理论,他给我们后人留下了一份值得重视的遗产。
注释:
[1]钱钟书:《谈艺录》,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
[2][3]布封:《谈风格》,《译文》,1957年9月号。
[4][德]歌德:《自然的单纯模仿·作风·风格》,王元化编译,《文学风格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6][俄]普列汉诺夫:《没有地址的信·艺术与社会生活》,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7][德]黑格尔:《美学·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8]文中《体性》篇的原话全部摘引吴林伯著,《<文心雕龙>义疏》,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赵艳菊 新疆库尔勒市且末中学 841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