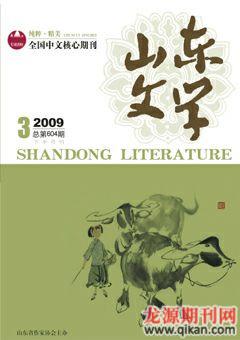从东晋南朝时期的人名看僧侣的影响
按照大多数学者的意见,佛教早在两汉之际就传入我国中原地区。东汉末年,安清、支谦等为避战祸,先后南渡过江;稍后,康僧会也从交趾北上,到建业(241年,一说247年)后,设置佛像,从事传教,又在孙权支持下立建初寺,译注佛经,“由是江左大法遂兴”,佛教在江南得到初步流传。到了东晋,佛教开始“被士人普遍接受,而在中国真正站住脚跟”。
佛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其发展需要一定的群众基础。东晋南朝是佛教发展的关键时期。当时,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是僧侣们分散的、自发的行为,正是这种无组织的状态,给广大僧人的活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他们可以自由地选择志同道合的人士交往,其范围逐渐扩展到社会各阶层。佛教僧侣们通过辩论、讲经、示法等活动,对人们施加影响;高僧们更是以身作则,以其渊博的学识、过人的智慧和高尚的品德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和崇敬。世俗统治者也频频主动与高僧们交游,谈玄论佛,以为良师益友。帝王请僧侣讲经也是司空见惯之事,继而发展到让僧侣们常居皇宫。所以,僧俗往来已经成为社会交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长期的交往使僧俗之间产生了浓厚的感情,僧侣对俗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使得世俗之人在多方面模仿前者——颇似时下的追星族——甚至连取名也不例外。
古人云:“黄帝正名百物”。人是万物之灵,名字自然就尤为重要。人名是人类社会中的普遍现象,是人们通过符号区别于他人的特定标志。古人命名非常讲究,《礼记•内则》中记录下了十分繁杂的命名礼。关于名,《说文解字》解释说:“名,自命也”。将名与命运相联系,足以说明古人对命名的重视。
不同时代的人们有着不同的心理,名字的时代色彩较为浓厚。例如:商周时期,人名常与天干、天象、五行相关;而汉代随着儒家思想的确立,名字中的礼教色彩则浓重起来。所以,名字往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个时代的风尚,而追逐风尚正是东晋南朝社会的突出特点之一。随着佛教的盛行,僧侣也成为人们仿效的对象。晋时,河内人昙徽投道安出家,后随其在襄阳。苻丕进攻襄阳,昙徽为避战乱,来到荆州上明寺。他宣传佛法,受到了僧俗的普遍欢迎。他常对道安的画像行礼,这本是表达对师父的敬仰之意,没想到却使得“江陵士女,咸西向致敬印手菩萨。”
随着佛教对社会的不断渗透,俗名中也常出现一些佛教词汇。这种现象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效仿僧侣法号的结果。法号是所有僧尼都拥有的,通常在字面上给人以十分浓郁的佛教气氛,在社会交往中引人注目。
在各种命名用字中,最常见的就是“僧”。如:东晋时的南昌公郗僧施、南蛮校尉羊僧寿等。到了南朝,这种情况更加普遍,在此依据《晋书》、《宋书》、《南史》、《世说新语》等信史,择取位高或名显者列于下。
宋:太子舍人王僧谦、湘州刺史王僧朗、左光禄大夫王僧达及其从兄弟侍中僧绰和尚书令僧虔、兖州刺史沈僧荣、青州刺史明僧暠、博士颜僧道、宜都太守袁僧惠、太子中庶子江僧安等;
南齐:冠军将军戴僧静、越州刺史陈僧授、前将军刘僧副、宁朔将军王僧炳、交州刺史范僧简、太学博士王僧孺、湘东内史王僧粲等;
梁:散骑常侍吕僧珍、义州刺史文僧明、大司马王僧辩、司马王僧珞、车骑将军胡僧佑、谯州刺史湛僧智、兖州刺史杜僧明、太府卿沈僧杲、厢公王僧贵等;
陈:巴州刺史戴僧朔及其族兄右将军僧锡、合州刺史焦僧度、定州刺史周法僧及其弟散骑常侍法尚、巴山太守蔡僧贵、征南谘议阴僧仁等。
“僧”,是僧伽的简称,意为和、众,原指僧团,后亦用于单称。
除“僧”外,几乎所有僧尼法号中的字都成了时尚。
以“法”命名的主要有:东晋穆章何皇后(名法倪)、孝武定王皇后(名法慧)、庐江太守张法顺;刘宋时明帝陈昭华(名法容)、越骑校尉戴法兴、征北参军管法祖、梁州刺史甄法护、益州刺史甄法崇、阴平太守沈法兴、司马管法济、南海太守陆法真、东阳太守沈法系、略阳太守庞法起;南齐时的宁州刺史程法勤、始兴太守房法乘、中书舍人茹法亮、总明学士何法冏、宜都太守郑法绍;梁时有太尉元法僧、平北将军薛法护、骠骑将军杨法深、司徒陆法和、安南将军刘法瑜、琎州刺史陈法武等。“法”,音译为达磨,为通于一切之语。“法”虽非佛教专用词,然遍查前四史,仅《史记》有“法章”一名,属偶见。
佛教非常重视智慧,知俗谛曰智,照真谛曰慧。“智”、“慧”二字也常见于僧尼之法号。
“慧”,音译般若,确知诸法真相的智慧。在俗世,以“慧”命名者有:东晋交州刺史杜慧度、宋湘州行事何慧文、竟陵太守孟慧熙、淮南太守刘慧明、宁朔将军沈慧真;南齐散骑常侍何戢(字慧景)、南兖州刺史陆慧晓、平西将军崔慧景;梁敬帝(字慧相)、太子右卫率萧慧正、巴东太守萧慧训等。
“智”,音译阇那,深明事理之意。以“智”命名者有:宋武陵王赞第九子智随、宁朔将军江智渊、南昌令诸葛智之、中军行参军吕智宗;齐梁州刺史阴智伯、东昏侯萧宝卷(字智藏)、和帝萧宝融(字智昭)、高昭皇后刘智容、江夏王宝玄(字智深)、庐陵王宝源(字智渊)、鄱阳王宝夤(字智亮)、邵陵王宝攸(字智宣)、晋熙王宝嵩(字智靖)、左军将军徐智勇;梁安成郡王萧机(字智通)、南浦侯萧推(字智进)等。
以“昙”命名的有:晋游击将军王昙之、给事中王昙亨、宋御史中丞王昙生、祠部尚书沈昙庆、广州刺史袁昙远、侍中王昙首、乌程令盛昙泰、广兴郡公沈昙亮、南阳太守朱昙韶;齐通直散骑常侍庾昙隆、给事中谢昙济、越州刺史孙昙瓘、黄门郎殷昙粲;梁中书侍郎王昙朗、著名孝子滕昙恭、刘昙净等。昙,为昙摩的略称,意即佛法。
“道”,音译为末伽,佛教特指通往涅槃之路;又为菩提,即大智慧之意译。当时佛教徒被称为“道人”。在《高僧传》、《续高僧传》等佛教史籍中,僧人自称为“贫道”的例子不胜枚举。慧远法师在给桓玄的信中,也多次以“贫道”自称。僧人亦有称为“道士”的。“道”亦为僧侣法号的常用字。这一时期,世俗中以“道”命名者非常之多:晋明帝(字道畿)、简文帝(字道万)、废帝皇后庾道怜、元帝之子琅邪王裒(字道成)、东海哀王冲(字道让)、武陵威王晞(字道叔)、简文帝之子会稽思世子道生、征西大将军刘道规、司空刘道怜、晋陵太守殷道叔、镇西将军周抚(字道和)、侍中郗鉴(字道徽)、尚书郗恢(字道胤)、散骑常侍刘波(字道则)、太常诸葛颐(字道回)、吏部郎江逌(字道载)、征西将军刘牢之(字道坚)、王凝之妻谢氏(字道韫);宋高祖之弟长沙王道怜和临川王道规(字道则)、婕妤胡道安、司空檀道济、雍州刺史刘道产、广州刺史程道惠、益州刺史刘道济、交州刺史荀道覆、青州刺史刘道隆、冀州刺史崔道固、龙骧将军刘道符、司州刺史姚道和、骁骑将军高道庆、左卫将军孙道隆、龙骧将军薛道渊、黄门侍郎刘道宪、辅国将军薛道标、侍中刘穆之(字道和,小字道民)、征虏将军刘粹(字道冲)、司马蒯恩(字道恩)、太子左卫率胡藩(字道序)、员外散骑郎荀雍(字道雍)、散骑常侍刘秀之(字道宝);南齐开国皇帝萧道成及其母陈道正、宁朔将军高道庆、直阁将军曹道刚、司州刺史姚道和、员外散骑常侍王道宝、冀州刺史崔道固等。可见当时“道”用于字的现象十分普遍。儒家、道家等也强调“道”,所以人名中的“道”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后汉书》有“道房”(官婢名)、道幽;《三国志》中,孙吴有光禄勋薛莹(字道言)。但到了东晋南朝,以“道”入名者陡然增多,显然与佛教的兴盛有关(其中不排除有的是受道教的影响)。
刘宋时,南郡王义宣之子分别名为悉达(释迦牟尼之名)、法导、僧喜、慧正、慧知、明弥虏、妙觉、宝明,既反映出他个人崇佛的倾向,也是命名风格的表现之一。
南朝时,人们开始试图将“佛”用于名字。刘宋时有南豫州刺史段佛荣、步兵校尉陈佛念、临沅县男孟佛护;南齐时有骁骑将军张佛护;梁时有宁西将军王佛辅等。“佛、法、僧”号称佛教三宝,“佛”字见于人名晚而使用者不多,究其原因,其一是本土僧侣中几乎无人用此字,其二是佛在人们心目中具有一定的威慑力,唯恐有所冒犯。可以看出,用佛命名者常以“念”、“护”、“辅”等字佐之,更能体现出希望得到“保佑”的心理。佛的全称是佛陀,本义是真理的觉悟者。
也有将佛教词语用于小字或小名的,如:东晋后废帝司马昱(小字慧震)、散骑常侍王珣(小字法护)、王珣弟中书令珉(小字僧弥)、荆州刺史王忱(小字佛大)、宋孝武帝(小字道民)、顺帝刘准(小字智观)、会稽太守褚淡之(小字佛)、齐郁林王萧昭业(小名法身)、梁敬帝(小字法真)、陈开国皇帝陈霸先(小字法生)等。
更有甚者,在小名或小字中直接采用佛、菩萨之名。如:梁昭明太子统,小字维摩。维摩是维摩诘的简称,释迦牟尼的在家弟子,相传为金粟如来的化身,精通大乘佛教教义。长沙嗣王业弟藻,小名迦叶。迦叶,全名摩诃迦叶,为释迦牟尼十大弟子之一,亦名饮光。佛经中称“迦叶”者尚有数人,在此从略。以大智著称的文殊师利菩萨,文,译为“妙”;师利,译为“德”或“吉祥”。梁有秘书丞王训,小字文殊;陈宣帝顼,则小字师利。陈废帝伯宗,小字药王。药王,阿弥陀佛二十五菩萨之一。
至于上层社会中的妇女,大都将目光投向尼僧。晋宋之际的建福寺道瑗尼,“晋太元中,皇后美其高行……富贵妇女,争与之游”;宋普贤寺法净尼,“宫内接遇,礼兼师友……荆楚诸尼及通家妇女,莫不远修书?求结知识。”而在尼僧法号中,“妙”字是最能体现性别特征的,故在俗也多用于女名。如:宋明帝陈贵妃,名妙登;梁长山公主名妙;陈世祖沈皇后,名妙容。当然也有其他情况,东晋卫将军谢尚就将二女分别取名为僧要、僧韶。因史书中少有关于妇女的记载,至于妇女之名更是罕见,故无法进行详细的总结。
“名字是现实的反映,也很自然地为思潮所溅湿。”人名作为一种文化形式,蕴含着丰富的时代信息,铭刻着一定文化观念,是反映人类社会文化的一面镜子。人名的发展和变化,是社会发展变化的一部分。同时,人名也常常隐寓着个体的爱好和情趣。在某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人名具有自己的主题特征。周一良先生在《论梁武帝及其时代》一文中指出:“南北朝时人名尤其小字往往反映宗教信仰。”总体来看,以上人名固然反映出宗教信仰以及命名者希望借佛教之力增福减灾的心态,但“法”、“僧”、“妙”等极少出现于名尾,显然是模仿僧侣法号的结果,而非单纯只是一种宗教崇拜心理。一千多年过去了,当我们翻开史书时,便可以寻觅到打在这些姓名上的历史痕迹和时代烙印,从而依然可以想见当时人们崇佛的情景……
参考文献:
[1]慧 皎:《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
[2]严耀中:《江南佛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3]《礼记•祭法》,《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
[4]王孺童:《比丘尼传校注》,中华书局,2006。
芮诗茗: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