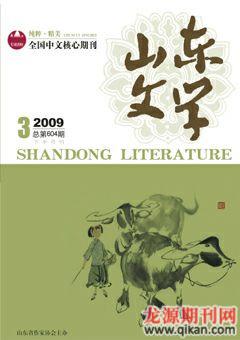“一致——和谐”与“家国——社会”
张 莉
摘 要:政行不畅其特点是科学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遭到集体的有意曲解。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众多素质很高的政治精英做出这样非理性的行为?本文指出,中国重“一致”而非“和谐”,知“家国”而不知“社会”,政行不畅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的一个顽疾。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要减少人情权宜空间,包括细化政策和表明立场。直抵问题实质,这是求发展的中国人必须做出的改变。
关键词:政行不畅 人情 面子 能动社会 公民社会
一、问题的提出
十七大召开之际正值我国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与肯定改革成就并行的是国内外各界对十七大提出的各个重大实际问题的热烈讨论。从交流结果来看,参与讨论者的态度冷静而乐观,主要的担忧是良好的政策“热在上层,冷在基层”,新制度遭遇老格局的强大抵制,最终让科学而惠民的方案变形、扭曲甚至流产。
政行不畅通常有两种情况:一是政策本身不符合现实,在自上而下的推行过程中会遭遇“反动”执行者的抵制,会引起大众的激烈对抗。另一种情况是,政策本身能够科学指导实践,然而,在执行过程中被集体地有意曲解和误读,结果还是会引起大众的不满和怨言。目前,我国改革实际中出现的政行不畅就属于此类。
因为,改革是在各个利益集团的博弈,新老格局的寸土寸金式的争夺过程中展开的,从中央到基层存在着巨大的对政策理解和执行的变动空间,即使在正确理解和科学执行的情况下还会出现不一致,更不用说某些既得利益拥有者们用心良苦的“解读”所带来的混乱。
为什么被公认为科学的政策从中央通过层层地方传递到基层就不再科学?排除少数的腐败分子,大多数执行者们都是受过良好的教育,德才兼备的政治精英。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让这些理性的行动主体做出了看起来很不理性的行为?因为,事实上政策执行者们的投入远远大于自己的利益获得,甚至有时要以损害自己的利益为代价来维持政策被曲解的局面。
二、解读“一致——和谐”与“家国——社会”
1.“一致”而非“和谐”。中国人素来看重人际关系,凡事讲“人情”,重“礼”,要“面子”,“以和为贵”。关于此问题,中国学者翟学伟在其《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一书中有深刻而独到的见解。中国的“家本位”和“乡土特色”孕育了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人际交往模式,其特点是情感关系至上,以个人为中心的级级外推。这样“人情”就从家庭走到了整个社会结构的方方面面,只不过越靠近个人中心的“人情”越亲密,越远离个人中心的“人情”越淡漠。是什么让淡漠“人情”的维持成为可能? 重“礼”和“要面子”在这其中起着重要作用。受“礼”引导的“情”具有了礼貌和客套的人际牵制意味,让假意的人情可以当作礼物赠送;重视关系因而将做人的重心放在“面子”上,极度重视他人的评价因而往往心理和行为不一致,导致了人情的交往不在乎是否真心只要面子上过得去就行。
“以和为贵”的思想让中国人懂得权宜,为与其他人都保持良好的关系个人可以在不同场合有不同的表现,即使前后矛盾也可以为人所理解。这种奇特的身心分离的二元现象让中国人的交往模式变得复杂而辛苦,在人际关系极为敏感的政治领域,深知利害的政治精英们尤其小心翼翼地保持人际平衡。平衡就是平均,就是“与他人保持一致”,在这种状态下会感到平等,感觉到“没有被当作外人”,因而局面保持稳定;反之,差别待遇会引起心理失衡,会导致局面的不稳。越是复杂的关系网,减少不必要麻烦的最简单、公平的方案就是越要尽量保持群体的一致,这个让中国传统大家庭维持稳定长久的关键已经套用到到家庭外的各个场合。
平衡让人际关系达到了表面的“和”,真正的差异却被埋藏在“一团和气”之下,往往问题越严重,表面却越“和谐”,因为谁都背负不了“丢面子”的严重后果。如此我们便可以理解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种种问题,这是被关系紧紧包裹的中国官员维护自己人际平衡的本能反应。处在新旧体制交锋前沿的官员其既得利益受威胁最大,他将以种种合法或非法的方式捍卫自己的权力。单纯牵涉法理的行为是清晰而透明的,加入“人情”之后事情就变得复杂了:久居官场的官员早已编织了密密麻麻、无限延伸的各种关系,人情的反复借贷和转移已经让其中的“人情债”不可能两清:即使和主角本身没有关系,但因为“欠”与主角有关的人的情,也要看在那个人的“面子”上施与主角“面子”,维护他的“面子”。可想而知,被无穷无尽的人情和面子压迫的科学怎能不低下自己高贵的头颅?
2.“家国”而非“社会”。社会不是中国的本土概念,纵然是儒学也只谈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先天不足的情况下如何构建社会,这是有识之士都会认真思考的问题。关于此问题,沈原在其《社会的生产》一文中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阐述。按照马克思的定义,社会是自由的社会成员之间的自主联系。但是,马克思的“社会”是对共产主义社会的预想,除了谈到最多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外,没有给社会留下太多的空间。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填补了这个“盲区”,波拉尼和葛兰西分别提出了处于一定具体历史时空条件下的“社会”概念:前者是在与市场的冲突中具备意义的“能动社会”,目标是要反对“社会嵌入经济”的市场专制主义(market despotism);后者是在与国家又勾连又斗争夺的复杂情境中成长起来的“公民社会”,目标是要反对“国家吞没社会”的政治专制主义(political despotism)。这样,“社会就是定位在市场与国家之间的那个宽广领域,它在与市场和国家的双向搏斗中,时而扩大、时而收缩着自己的地盘。”
因此,如何“在欠缺必要资源的条件下同时将这两个‘社会生产出来,并将它们融为一体”是目前面临的现实问题。能动社会中的主体是工人阶级和底层阶级,公民社会的主体是公民,两者的关系是:“单独的市场不能催生工人阶级,也不能立即催生能动社会。有了公民社会的某些要素,如索摩斯所提出的‘民权、‘底层的公共性等要素,构成一个有利于工人阶级形成的外部环境,才会最终使工人阶级走向存在,进而使工人阶级(以及其他阶级)在‘社会的名义下,形成各种联系和组织,抵抗市场的入侵。”
另一个更为直接的产生公民权的渠道是转型期特有的各种社会运动。我们的社会在法律和制度安排上尚不具备社会运动自主发生的情景条件,所以,中国的社会运动需要参与者发挥极大的主体能动性。然而事情也不会朝着这个理想方向发展:中国地区发展水平非常不均衡,公民意识的程度也有高低,“能动社会”和“公民社会”可能在不同的地区呈现不同的景况,最为可能的情况是两者共同发展。这就存在一个公民和阶级如何融合的问题:公民权本质上体现的是“社会平等”机制,与“社会阶级”在功用上是相互制约的。也就是说阶级体现的是群体间的差异,公民体现的是个人间的平等,随着贫富差距的增大,阶级差异显著,随着公民权的完善,差距又被一定程度地缓和。如果差距的速度远大于缓和的速度,社会运动甚至革命的动员在底层阶级中才有可能。目前,贫富差距和公民受保障实现程度存在地区差异,所以全国范围的社会动员不可能实现。更重要的一点是,如前文所述,中国人的集体行动逻辑是寻求表面平衡一致、权衡利弊、明哲保身,有多少“公民的勇气”(civil courage/Zivilcourage)能被激发出来尚可未知,即使有公民“为了信念儿不惮于行动,即便为了信念而冒着支付高昂代价的风险”,响应者也不会太多。公民集体的容忍延缓了公民社会的进程,放弃了监督和努力的权力,允许了政行不畅的存在,因此“社会”建设任重而道远。
三、结 论
和谐反映了民生的诉求,社会反映了民主的需要,这是走科学发展之路,强调“以人为本”的中国必然的政治选择。然而,“和谐”和“社会”都是需要认真分析的概念:中国素来就有追求人际和谐的价值观,但不是追求表面一致的“伪和”,掩盖冲突的形式主义不是真正的和谐;在只知“家国”不知“社会”的中国建立起“公民社会”和“能动社会”实属不易,缺乏有勇气的公民让任重而道远。政行不畅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难以克服的一个顽疾。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之一是减少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人情权宜空间。决策层所制定的方针政策要考虑到地方的适应性,所以一般不会特别具体,否则,会成为不科学的教条。正是这种政策的通融性为人情权宜提供了便利,宏大的表述为变通提供了保护。其次,出于“和谐”的考虑,中国人在表达观点和意见时大都客气而含糊,这也为人情的权宜留了余地,谁都不想得罪人,结果问题依旧难以解决。如果政策具体而立场鲜明,会给人情权宜以压力,逼迫其做出选择而没有权宜的余地。放弃中庸之道而直抵问题实质,这是求发展的中国人必须做出的改变。
参考文献:
[1]李承志:《谨防民生政策“热在上层冷在下层”》,2007.10.21,新华网。
[2]钟立华、吴可望:《腐败的预防制度》,《求实》,2007.9。
[3]沈 原:《社会的生产》,《社会》,2007.2。
[4]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张 莉:上海大学文学院社会学07级秋季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