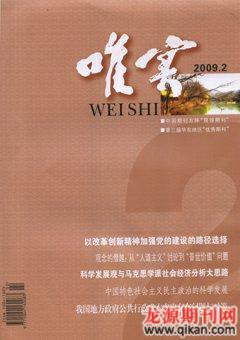土地流转制度的经济伦理学解读
薛 葵
摘 要:为深化农村土地改革,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出台允许农民进行土地承包权流转的政策。从经济伦理的角度解读,此举标志着政府处理“三农问题”伦理原则的重大转向,实现了从多予少取的补偿性公正原则到赋权放活的应得公正原则的转型。
关键词:土地流转;多予少取;补偿性公正;赋权放活;应得公正
中图分类号:B82-0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9)02-0030-03
30年前,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画卷从农村开始;30年后,以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农村改革再一次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这次会议通过的在确保土地承包经营权长久不变的基础上,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探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政策成为新一轮改革的核心和焦点。我认为这不仅仅代表一条新政策的出台,从哲学的角度看,任何经济政策和制度都隐含了一种伦理取向,土地流转政策的推出意味着政府处理涉农经济利益伦理原则的重大转向:从以往的补偿性公正原则到赋权放活的应得公正原则。
补偿性公正原则是经济伦理的基本价值之一。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认为,人们由于天赋的不同而带来的社会不公平是客观存在的现象,但社会可以通过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安排来补偿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从而实现公平。中国现代史上两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业化进程都凝聚着中国农民的奉献和牺牲,他们的确是社会真正的弱势群体。建国伊始,为了尽快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基本的国家工业体系,我们搞了第一次工业化,但由于国家经济实力和经济丰裕程度的有限性,我们采取了城乡分而治之的抑农政策——城乡二元体制。先城市后农村,先工业后农业,先市民后农民,以城市为中心,把农村和农民仅仅作为社会发展的外围与补给线;同时,农村的主要经济资源控制在国家手中,国家为积累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持久的压低农副产品价格的政策,使之成为工业化所需资金积累的基本来源。据统计,在1952-1992年的40年间,农业因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形成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12580亿元的巨额积累资金,扣除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和财政从农业部门的收入差额,广大农民在自己生活水平很低的情况下为国家提供了10636亿元的积累资金。[1]正是由于农民的奉献和牺牲支持了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保证了我国工业体系建设的完备。改革开放以后,以农村改革为先声,我们又开启了第二波工业化进程。农村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农民,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但和城市人口相比,他们的“相对”受益还是很小,而且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城市对劳动力、土地的需求不断高涨,致使农民工涌现、打工潮兴起,大量农村青壮劳力进城务工,遗留在农村的承包地或是被贱卖和不当征用,或是被抛荒。而被贱卖和不当征用的土地交易利润却往往被农村基层政府所截流,农民又一次成为工业化大潮中的利益受损方。
如何破解困扰中国发展已久的“三农”难题一直是党中央关注的大事。因此,在制度安排上很自然地采用补偿性公正原则,千方百计地通过各种政策倾斜“三农”,实行补贴和优惠。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回答记者有关“三农”问题的提问时,说了这样两段话:一是“我想起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的一句话。他说,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我们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也就懂得了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二是“世界上大多数穷人以农业为生。因而,如果我们懂得了农业,也就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温家宝总理借助舒尔茨有关“穷人的经济学”原理所讲的这番话表明,政府对农民的贫困是抱有深切的道德关怀的,而且还千方百计最大限度地帮助农民脱贫。据统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发布实施的指导农村改革的重要文件约79个,其中,有10个文件作为中央“1号文件”颁发,而这10个中央“1号文件”都贯穿着同一个主题:对于“三农”要多予少取。1982年和1983年,两个中央“1号文件”旨在解放农业生产力,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给予农民生产自主权。1984年,第三个中央“1号文件”强调继续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延长土地承包期至15年以上,同时,大幅度提高粮食和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促进农村经济的繁荣。1985年,第四个中央“1号文件”进一步规定,取消30年来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制度,对粮、棉等少数重要产品采取国家计划合同收购的新政策。1986年,面对整个国家物价波动较大、农业生产出现滑坡的不利形势,中央出台第五个“1号文件”,提出力保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稳定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九十年代以来,为了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1996年,中央颁布《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提出努力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农民增收。1997年,从政策上承诺土地承包期15年到期后,继续延长30年保持不变。2000年以后的五个涉农中央“1号文件”更是加大了支农、惠农力度,在统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高度上认识“三农”问题在整个改革布局中的重要地位和意义。2003年,第六个中央“1号文件”和2004年的第七个中央“1号文件”都提出对种粮农民实行种粮直补、良种补贴和农机补贴,促进农民增加收入。2005年第八个和2006年第九个中央“1号文件”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决定大幅度增加国家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的投入,扭转长期以来农民负担过重的局面,推进城乡户籍、就业、财税、金融、社保等方面的改革,探索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加快形成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政策体系和惠及农民工的城乡公共服务体制,尽快构建起强农、惠农的政策体系。随即,政府宣布全面取消农业税,标志着我国实行了两千多年的古老税种退出了历史舞台。2007年12月,第十个中央“1号文件”发布,强调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切实关注农村民生,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大农村扶贫力度。
政府一系列支农、惠农、强农政策背后所折射出来的多予少取的补偿性公正伦理原则本无可厚非,但落实在中国农村发展的具体实践中却出现了令人费解的悖论:一方面,政府对农民政策倾斜和补偿的力度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城乡差距也越来越大。2008年8月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农民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从1984年的1∶1.81扩大到1999年的1∶2.6,再扩大到2007年的1∶3.3,人均收入差距绝对额则从5300元扩大到9600元。究其原因,多予少取只是从外部给予补偿和支援,况且还不能保证这种补偿和支援的足够度和持久性。好比救治病人,根本的解决之道是变输血为造血,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贫困问题,就要在多予少取之外找寻新的路径:放活。放活就是确认农民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农民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给其所应得,用经济伦理的语言表达就是应得公正原则。
应得公正是经济伦理的重要原则。英国哲学家米尔恩认为:“公正如果表现为‘给每个人他所应得的这种基本的形式,那么它在任何社会共同体中都是一项必不可少的道德原则。它要求每一个成员依其成员的身份,给予伙伴成员们应得的东西,并从他们那里获得他应得的东西”。而且,“不论一个社会共同体特定的文化和价值如何,有一种东西是每个成员都应该得到和给与的,这就是公平对待”[2]。美国政治学家德沃金认为,公正就是任何人都应该得到同等的对待,社会的发展不能建立在剥夺一部分人的应得权利和利益的基础上,“经济功利主义是不公正的,因为它把贫穷当作效益的手段而使之永存”[3]5。“分配应使任何一个种族或人种集团并不比其他集团更差。”[3]27可见,“给每个人他所应得的”是确保社会公正的必要原则。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表面上看是出台又一项惠农政策,但实质上是拓宽了农民对土地的权利范围,赋予广大农民本应得到的更全面、更切实的土地处置权,从而让农民拥有搞活经济的基本条件,让他们真正成为农村经济的主体。
土地流转政策的推出标志着政策导向从多予少取的补偿到赋权搞活的转型,这是历史的跨越。其意义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只有农民得到了包括土地流转交易权在内的完全的土地自主权,才能切实保证自身的权益。很多年里,政府的补偿性政策收效不大,农民的贫困没有根本改观,就在于农民并没有真正享有对自身赖以生存的,也是惟一的资本——土地的自主处置权。我国宪法规定,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改革开放后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保持土地集体性质不变的情况下,允许农民拥有所承包土地的使用权和经营权,这种两权分离极大地激发了农村的活力,为当时农村改革的成功奠定了基础。但只拥有使用权和经营权并不是完整的土地支配权,土地支配权中和农民权益收入最直接相关的交易权、流转权实质上却被农村基层政府僭越了。地方政权利用手中的权力任意征用农民的土地并占有了大部分的本该属于农民的交易利润,农民在土地方面的权益得不到任何保障。而且,这方面的问题似乎越来越严重,既造成农民和地方政权之间的高度紧张,影响社会稳定;又诱发了官员和资本在土地问题上的严重腐败。只有赋权给农民,才能真正盘活农民手中的土地资本,使农民获利。比如:让农村建设用地上市流转;农民以地为股,经集体转让获稳定租赁收益;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将农业用地集中到龙头企业和种植养殖大户手中,实现土地的集约化经营;针对农业用地改为城市用地的情况,采取对征地动迁农民采取现金补偿+股份补偿的方式;集中配置宅基地等非农用地资源,把更多的非农用地释放出来进行交易获利;对离开农村去城镇务工或经商的农民可以通过转让土地获得补偿,等等。土地流转或者资本化显然可以是农民收入的一个很大来源,反之,如果土地不能资本化,地方政府实际上一直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掠夺农民的土地,损害农民的权益。
第二,土地流转制度的实施有可能为农村的下一步发展提供巨大的动力。通过赋予农民土地流转权,农民的主体地位更全面地得到确认,可以预测,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势必会被激发出致富奔小康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像当年创新承包制和乡镇企业模式那样,摸索出新一轮农村改革的有效路径。同时,赋予农民土地的流转权,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家庭承包责任制与土地规模经营之间固有的悖论,从而实现农村本身生产方式的转型。我们知道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显著特点就是土地分割到户,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显而易见,这种细碎化的小农经济结构无法获得规模效率与范围经济,也无法从农业内部发展出专业化与分工体系,而通过流转形成的合作经济和规模经济可以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第三,土地流转制度也符合社会发展的大趋势,那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从各国发展的经验来看,农村问题的根本解决还是要依靠工业化和城市化,就是说,只有当工业化和城市化有能力吸收大部分农业人口的时候,中国农村问题的解决才有希望,实行土地流转显然是符合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需要的。长期以来,我们对农业、农村和农民有着错误的浪漫化倾向,试图通过补偿式的大量投入和政策倾斜把农民和土地永久地绑在一起,使得农民和农村永久化,甚至认为保持庞大的农村劳动力是中国经济崛起的“优势”。实践证明,此路既不道德也不奏效。“三农问题”的解决最终必须依靠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从农村和农业转移出去,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专家论证,随着农民的土地和宅基地流通权问题得到解决,一方面城市的资本、知识、人力等资源可以向农村流动;另一方面,相当数量的农民也可以离开农村,转变为城市人口。这种双向互动的结果是把城市的知识、资源、文明带入农村,也把农村充足的劳动力输往城市,实现真正的互补双赢和城乡的同步有机发展,从而最终破除阻碍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城乡二元体制。
参考文献:
[1]罗建文.农民待遇与制度道德问题[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
[2]米尔恩.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人权哲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58.
[3]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戴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