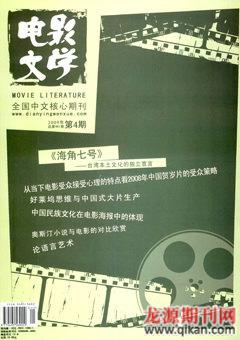试论卡夫卡和余华笔下父子冲突的文化内涵
赵光平
[摘要]父子冲突是卡夫卡和余华共同关注的主题。其外在形式表现为:卡夫卡是单向的,余华是双向的,其文化内涵表现为:卡夫卡是线形的,余华是圆形的。他们笔下的父子关系都表现出非理性特征,卡夫卡非理性成因主要来自家庭的压制,余华非理性成因主要是社会环境的影响。
[关键词]父子冲突;单向;双向,线形,圆形
一直在黑暗中苦苦探寻的卡夫卡照亮了20世纪乃至以后的世界文学,点燃了余华前进道路上的火把。余华坦言:“在我想象力和情绪力日益枯竭的时候,卡夫卡解放了我……使我的想象力重新获得自由。”因此余华把卡夫卡奉为自己的导师,同时卡夫卡作品的父子冲突主题也必然会被余华所关注。
父子冲突是西方文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被认为是人性的根本问题之一,也是反权威的标志之一。无论是弑父夺权的宙斯,还是杀父娶母的俄狄浦斯,父子冲突都是最突出的主题,为此弗洛伊德还演化出“俄狄浦斯情结”来解释其内因。这个主题如滔滔江水,奔流直下,从古希腊流到了20世纪卡夫卡的笔下,无论是被父亲判处死刑的格奥尔格,还是被父亲砸伤的格里高尔,父子冲突都是摆脱不了的宿命。父子冲突就像人身体里的盲肠一样寄居在人类社会里,不时会带给人类疼痛,是人类与生俱来摆脱不掉的赘疣,同时也是永恒的文学主题。
然而父子冲突主题在中国文学中就不那么被关注,如起伏绵延的山峦,时断时续,若隐若现。虽然古代文学中也曾出现过李靖和哪吒的父子之战,薛仁贵和薛丁山的父子相残,甚至曹雪芹也曾浓墨重彩描画过贾政杖责贾宝玉。但没有哪个学者对此专门做过深入地研究,也没有哪个中国作家对这个主题特别关注,直到当代作家余华出现。他的三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中,父子冲突就成为一个重要的显性主题。
卡夫卡认为斗争是人的存在方式,孩子与父母之间的关系也不例外。“父母是孩子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必须与之进行的是第一次反抗,同他们的讨论是一生中后来所有斗争的模式。”基于这样的认识,父子冲突必然会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有所表现。有意思的是,余华对父子关系的看法和卡夫卡是惊人的一致:“人生就像是战争,即便是父子之间也同样如此。”卡夫卡的孤独气质濡染了余华,唤醒了余华心中同样沉重的东西。“斗争”和“战争”是两位作家对人生内容的解释,对人际关系的概括,当然也包括父子关系。但是卡夫卡生活在20世纪初期的奥匈帝国,余华成长于20世纪后期的中国。他们笔下的父子冲突,其表现形式、文化内涵必然有所不同。因此对卡夫卡和余华笔下的父子冲突进行比较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一、单向和双向
卡夫卡笔下的父子冲突,是单向的,父→子。父亲是绝对的权威,可以对儿子发号施令,为所欲为,儿子只能被动地服从,不能反抗,或是不敢反抗。在卡夫卡的小说创作中,最集中表现父子冲突的是《判决》、《变形记》和《司炉》。《判决》中的格奥尔格被父亲判决去投河自尽,格奥尔格竟真的冲下楼去,投河自杀了。格奥尔格,一个已经订婚的成年人,一个在商场上打拼的成功男人,对于已经衰老的父亲,他是有能力反抗的。但他没有一点反抗,而是像个听话的孩子,按着父亲的话去做了。父亲是施令者,他只是默默地承受者,哪怕是让他去死,他都要执行。儿子在这里不再有力量,他的力量在父亲强大的权威面前被瓦解殆尽了。父亲尽管衰老,但父亲的权威像大山一样压着儿子,使儿子无力反抗。《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本是家庭的经济支柱,然而一旦某天早晨他变成甲虫,情况将完全改变。首先是父亲表现出不可遏制的恼怒,后来他又给甲虫形的儿子扔去一个烂苹果,造成儿子的致命伤。这跟判决儿子的死刑实质上是一样的。《司炉》的卡尔·罗斯曼只因年少无知,被一中年女仆引诱发生了关系,却被父母无情放逐到美国,他同样是无力反抗的。在卡夫卡这几篇表现父子冲突的小说中,父亲都是强大权威的代表,是施暴者,儿子是弱小的承受者。父子之间的关系是单向的。
比较起来,余华小说中的父子冲突要复杂得多。概括地说,是双向的,父←→子。父亲是施暴者,同时也是承受者。儿子是承受者,同时也是施暴者,是有来有往的。甚至有时儿子的力量更强大,无可奈何的是父亲。《活着》中的福贵年轻时嫖妓赌博浪荡胡闹,当父亲的是一定要管的。福贵不但不听,反而恶语相向,拳脚相加,直到把家产全部输光,气死了父亲。古人遣训:“子不教,父之过。”父亲管儿子,天经地义。但儿子不服管,反而反抗父亲,甚至把父亲气死。在这里,父亲不再具有权威性,甚至没有伦理道德,没有作为社会人的其他属性,有的只是俸力的较量。来自儿子的力量大于父亲,儿子就是胜利者。更有甚者,儿子还会成为主动的进攻者、挑衅者。《在细雨中呼喊》中的孙广才对他父亲更是不敬不孝,他把丧失了劳动能力的父亲当成累赘,嫌他白吃饭。一顿饭只给一小碗,而且还不让上桌子。于是父子俩斗智斗勇,父亲故意把碗掉到地上,并说这碗不能摔破,以后他儿子还要用呢。这使孙广才明白他也有老的那一天,他也没有好下场。
在余华描写的父子冲突中,缺乏一种起码的人道主义关怀,只是一种体力的较量,父亲衰老了不再有力量了,就不再具有权威性。父亲可以揍儿子,儿子也能打父亲。父子在心理上是对等的,没有权威,没有伦理,没有道德,简直就是动物的弱肉强食。
二、线形和圆形
文化内涵决定表现形式,卡夫卡和余华笔下的父子冲突,外在形式上是单向和双向的不同表现,是由其中包蕴的不同文化内涵所决定的。卡夫卡的父子冲突折射出其中的文化内涵也是一种直线形的结构,从父亲出发,指向儿子,父亲发令,儿子承受,直来直去。父亲判格奥尔格去跳河自尽,格奥尔格就去跳河,没有犹豫,没有反抗,更没有背叛。格奥尔格冲出去。外面的路很多,他走任何一条路都意味着生,他可以到他的商店里,看到他的生意兴隆,他可能会产生一种自豪感,他可以去看他的未婚妻。他可能会产生一种幸福感。一个生机勃勃的青年,有太多的理由活在世上。但他放弃了所有的理由,单单听从了父亲的话,选择了父亲指出的方向,没有回头。他走的是一条直线,没有迂回,就那么走下去,直至死亡。在这里父亲像上帝一样具有生杀予夺的大权。
卡夫卡直言不讳:“人对上帝的想象是不由自主地产生于对父亲的交往之中的,可是反过来的可能性同样不可排除。”世界上最了解卡夫卡的马克斯·勃罗德也持同样观点:“精神分析学认为,人对上帝的想象是不由自主地产生于对父亲的交往中的(也就是说上帝是根据父亲的形象塑造的),可是反过来的可能性同样不可排除:善感的人,如卡夫卡。正是通过对上帝的交往丰富了、扩展了对父亲的想象,使之形象丰满。”
通过父亲想象上帝,卡夫卡把父亲的权威无限扩大了。父亲像上帝一样具有绝对的权威,一言九鼎,不仅操纵着今生,还控制着来世,儿子是不敢反抗的。既然他判决儿子去死,格奥尔格们就不会有生路了。然而父子之间是有亲情
的,儿子的血管里是流着父亲的鲜血的。在卡夫卡那里,血缘抗拒不了权威,他强调父亲权威的至高无上。动物世界重遗传,讲血缘。尽管卡夫卡经常让他的人物变成小动物,但那只是外在形式。实质上卡夫卡笔下的人物,动物属性被削弱了,社会属性被强化了。家庭就是等级森严的社会,权威大于血缘。因此卡夫卡笔下的父子关系很单纯,从父亲出发,指向儿子。一条直线而已。
余华笔下父子关系外在双向性的表现,是由其文化内涵的圆形结构所决定的。父亲向儿子发号施令,儿子可以承受,也可以反抗。因为儿子是父亲生命的延续,父亲宽容儿子也就是宽容自己,于是就容忍了儿子的反抗。指令从父亲出发,画了一个圆,又回到原点。儿子之所以敢于反抗父亲,一个深层的原因。就是中国人心中从来就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上帝。在西方,尼采说上帝死了。权威倒塌了,世界失去了主宰。而中国从来就没有这样一个权威主宰着天堂地狱,因此中国人没有最深层的心理恐惧,不怕来世报应。但中国还有现世的统治者——君王和父亲。三纲五常中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君王和父亲的权威并不比上帝小。可是君王太遥远了,威胁不到普通老百姓,也就没有惧怕的必要了。惟一可能威胁到自己的就是父亲了。“我意识到父亲和我之间的美妙关系,也就是说父亲是我的亲人,即便我伤天害理,他也不会置我于死地。”余华一语道破天机,抓住了中国父子关系的精髓,中国人讲血缘,重亲情,亲情可以重于伦理。
《活着》里福贵的父亲宁可自己被气死,也不会把输光家产的福贵置于死地。《在细雨中呼喊》里孙广才一心盼着父亲早死,父亲也愿意成全儿子。他对儿子说:“儿子呀,我的魂一回来,你就又要受穷啦。”临死他想的还是为儿子节省粮食,不让儿子受穷。这就是血缘的力量。在血缘面前,一切权威都披瓦解,一切伦理都被消融。什么也挡不住血的力量。尽管余华的人物没有变形为动物,都是作为人的外形而存在,但实质上余华的人物比卡夫卡的人物更接近动物性。
三、非理性和理性
卡夫卡和余华笔下的父子冲突都表现出非理性特征。《判决》中的父亲反复无常,开始说儿子根本没有一个远在俄罗斯的朋友,后来又说自己早已写信把格奥尔格订婚的消息告诉那个朋友了。儿子稍一顶撞,父亲就判决儿子去投河自尽。《变形记》中格里高尔四处奔波,挣钱养家,但他变形以后。不能再为家里效力了,父亲暴跳如雷,竟然用苹果砸他,给他带来了致命伤。导致了他的死亡。余华小说《在细雨中呼喊》里的男孩苏字脑血管破裂陷入昏迷之中,没能起床去打水。他父母两次叫他起床去打水,他都无力回答。但他父母吃过早饭上班走了,谁都没到如此反常的儿子身边看一看,他默默地死去了。男孩苏字之死,和格里高尔变形死去,情节不完全相同,但本质是一样的,父子之间的冷漠。
精神分析学家告诉我们,要理解一个人性格的形成,必须从他的童年开始,卡夫卡的童年几乎是在恐惧和战栗中度过的。在人们的潜意识里,父亲代表着自己生存的世界,代表着世界的生存法则。卡夫卡有一个过于强大的父亲,由于自己的成功为人非常傲慢,对儿子形成一股强大的压力。压得卡夫卡直不起腰,抬不起头来。“在我看来,你具有一切暴君所具有的那种神秘莫测的特征……我的心灵之所以受到压抑,则因为你要我遵循的戒律,你,我至高无上的楷模,你自己却可以不遵循……我,是个奴隶,生活在其中的一个世界,受种种法律的约束,这些法律是单为我而发明的。”暴君式的父亲对卡夫卡童年的摧残是致命的,家庭生活带给他的惟有憎恨和绝望。使他觉得“我在自己家里,在那些最亲近的、最充满爱抚的人们中间,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父亲的压制使他感到整个世界似乎都在威胁他。卡夫卡这样形容自己的处境:“和每日世界直接的联系剥夺了我看待事物一种广阔的眼光,好像我站在一个深谷的底部。并且头朝下。”头朝下,有别于世人看世界的角度,一个可能带来全新发现的角度。头朝下就意味着不合常规,因此他看到的世界是扭曲变形的。他从另一个角度看见了别人没有看见的非理性的人性景观。
弗洛伊德充分肯定了父子冲突对卡夫卡艺术创作产生的影响。“就卡夫卡作为一个艺术家,其审美良知和意识受到个人的经历很大的影响而言,这正是他对世界文学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粗暴的父亲客观上成就了卡夫卡,给文学带来了全新的视角,他的父亲是伟大的。但从个人感受上说,粗暴的父亲伤害了卡夫卡,使他在抑郁中走完自己短暂的一生,他的父亲又是可恶的。
余华的父亲是一位专注于工作的外科医生,在余华童年的记忆里,父亲在家的时间极少。因此让余华感受到父子关系是美妙的,他心灵的土壤是温情的、理性的。他的非理性是社会影响的结果。他成长于中国文化大革命那样一个非理性的时代,使他过多地看到了人性的丑恶,埋下了非理性的种子。卡夫卡的作品为这颗种子提供了适合的气候,它就破土而出了。在余华的心灵中经常进行着理性和非理性的争斗,这种争斗必然反映在他的作品里。因此《捂着》和《在细雨中呼喊》中出现了非理性的父子冲突。但是理性对非理性的胜利催生了《许三观卖血记》。许三观用鲜血支撑他的家庭,完成了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他明明知道许一乐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但当许一乐生病住院后,他一路卖血换钱给许一乐治病,自己几乎丧命。这种父子关系超越了中国人最看重的血缘,是一种人类的大爱,是余华理性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