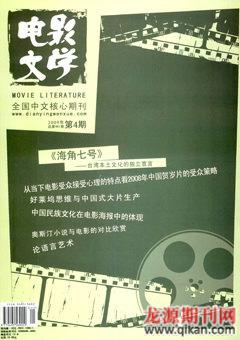西方小说“现代性”的借镜
沈庆会
[摘要]“通俗文学之王”包天笑在西方小说的翻译过程中,由模仿那些他“亲密接触”的西方小说开始。在短篇创作中努力吸取西方小说的思想内容、艺术形式、表现技巧,短篇小说既有对传统文言及明清白话小说的延续承继,又有19世纪中期以后对西方小说的借鉴模仿,在某种程度上可称得上五四新文学的开路先锋。
[关键词]西方小说;现代性;意识;叙事;细节
清末民初的小说家们在中国小说从传统向现代的变革中进行了积极而又举步维艰的尝试,他们在短篇创作时努力汲取西方小说素养,借鉴其优长,使其作品成为中国小说现代化发展历程中不可或缺的过渡桥梁。被誉为“通俗文学之王”的包天笑在大量西方小说的翻译过程中,由模仿那些他“亲密接触”的西方小说开始。渐渐从事独立的小说创作。他在短篇创作中努力吸取西方小说的思想内容、艺术形式、表现技巧,使其作品在主题内涵、叙述方式、叙事结构上具有不同于传统小说的变革创新。体现出他对小说文体的现代性的自觉追求。
一、“人”的意识的自然觉醒
中国古典小说往往不脱志怪传奇、才子佳人的叙事模式,深受西方小说影响的包天笑,其小说作品在取材和立意上都表现出新的因素,那就是对世俗社会生活百态的关注、描绘同强烈的社会现实意识、人文关怀精神自然而然地相互结合,从而具有较以往作品更加深厚的生活底蕴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以包天笑为代表的清末民初小说家“人”的意识的朦胧觉醒。
《军阀家之狗》依据事实写来,深刻揭示了军阀统治之下,普通老百姓连军阀家的一只狗都不如的残酷现实,对军阀灭绝人性、无恶不作的野蛮行径自有一股控诉力量。作品中带有强烈政治倾向的议论将矛头直指当时的军阀统治,表现出对虚伪、腐败政治的绝望,反映了一个老报人对时事政治的高度敏感和冷静洞察力。《谁之罪》则叙述了贫穷的小摊贩王国才以帮东洋杂货商代销洋广杂货为生,在五四运动抵制日货的风潮中,小摊上的日本货被爱国学生所砸,王国才想想今后生活无着,只好吃有毒的火柴头自杀身亡。罪人并没有在小说中出场,但读者明白那就是日本侵略者。小说很明显地有着新文学的问题小说的模式,表达了作者对被残害的弱小生命的深切关注和同情以及对日本侵略者的控诉和谴责,并让读者自己去思考。
《沧州道中》是包天笑短篇中最值得称道的一篇。该小说以短小的篇幅,描绘了千百万灾民被饥饿、病痛、灾荒驱赶得无处生存的最广阔的现实生活画面。作者从沧州道中一个火车站停留的瞬间,通过他那凝重的笔触向我们描绘了在站台上、火车上各色各样的人们的情形,虽然作者并没有议论什么,但是在他的笔触中,感受得到的是他对这些饥饿的灾民们深深的同情和怜悯,和对那些“为富不仁”的国人和洋人的谴责。小说的最后,以“一个没有脚的残疾乞丐”的困苦和他那不知所终的命运,来折射出千百万贫苦大众的水深火热的悲苦生活。用一个车站为窗口来反映社会现实,是这篇小说成功的切入点,使得作者可以用短小的篇幅反映最广阔的生活画面!20世纪初新文学时代的这篇作品,现今读来依然给人以强大的感染力,令人对当时贫富不均的社会现象有着深刻的理解。《四等车》也是将视角集中在一个车站,通过昆山车站候车的形形色色的人群以及专供贫穷人民乘坐的“四等车”的细致描摹,向读者展现了由贫富不均造成不平等的阶级划分。该小说虽没有《沧州道中》洗练的表现手法,反映的生活画面也没有那样深广,但在该文中由于“叙述者”和少年阿秀不同叙述视角轮番交替地观察、感受,不同等级之间的巨大反差,强烈地叩打着读者的心扉。尤其作品后半部,年幼无知的阿秀一系列稚嫩的问题以及爷爷意味深长的回答,不仅更增强了作品的批判力度,还使读者倍觉真实、亲切。
包天笑对社会底层的关注重点放在那些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广大妇女身上。《一个被遗弃的妇人》讲述了一个被丈夫遗弃的妇人的生活遭遇,尽管没有以上两篇的简练笔法,形象描绘也较弱,但该文中作者并非停留在当时众多小说家仅仅停留于提出问题以引起社会注意的层面上,而是指出了妇女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重要原因是过于依赖男子,自身不能自立,因此在文中指出女子要为自己“谋一个自立之道”。在当时追求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进步思潮中,能够从社会的经济根源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实属可贵。当然作者还不能进一步认识到若没有强大有力的社会环境和制度保障,寻求自立之道依然会遭到现实生活中更多的沉重压力和打击!《街头的女子》,写一个下等妓女在寒夜踯躅街头的悲哀场面,凄冷的寒夜、无情的冬雪、单薄的衣服、过路人的侮辱嘲笑,还有在警署里的睡梦及醒来后冷酷无情的罚金事实,都蕴涵着对底层女性的深切同情!
包天笑的短篇小说创作将关注和同情的眼光移向下层,用写实的创作手法,真实地描述了社会底层民众的贫苦人生。在这些作品中,自然而然流露出的是作者对贫苦人民不幸遭遇和悲苦命运的同情,以及对社会贫富悬殊及专制统治者鱼肉人民现象的不满。
二、描绘现实人生的“横截面”
包天笑在短篇小说创作中对现代性的追求,还主要体现在对传统小说以故事为中心,以情节为叙述结构与叙述方式的努力突破上。他的一些短篇小说改变了传统小说故事有头有尾,人物有始有终的习惯创作写法,而是以生活现实、社会人生中的一个场面或片断作为作品所要表现的中心。这种淡化情节、削弱故事性的尝试在《无线电话》中得以全面体现,使该作品在小说结构艺术突破上成为最具代表性的一篇。小说虚构了一个寡妇与亡夫世间与阴间的对话,通篇全是人物对话,完全没有叙事的成分,但却将寡妇的种种生活重压及痛苦心理完全展现出来,又在深层意义上反映了“人在人情在,人亡人情亡”的炎凉世态。《未亡人语》更加强烈地体现了作者谋求短篇小说结构形态变革的积极态度。“善士驻足,且听侬言”,小说以“疯女”之语开篇,她喋喋不休地向路人哭诉,被一群孩童围堵,在孩童的戏谵下,“疯妇”讲述了自己夫死子亡的生活遭遇,最后再以“善士驻足。且听侬言”结束。笼络垒篇的是表面看似毫无逻辑细看却有迹可寻的一连串的“疯言疯语”,读者得劐的却是一个下层女子的不幸遭遇并由此而生的同情。小说作为打破中国小说以情节为中心的传统叙事结构的尝试,非常有意义。
早在胡适对“短篇小说”做定义的1918年之前。包天笑已经精心结构、创作了一些“横截面”短篇小说。“横截面”叙述结构的短篇小说,打破了中国传统小说中按一般时序结构来建构文本的惯例。《影梅忆语》将与“我”相识相知的下层女性“娴”多年的命运变迁,浓缩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交代,展现了她从儿时的穷困,到被迫沦落风尘,再到现在苦痛境地这一完整的人生经历,过去的遭遇随时通过回忆和讲述穿插入现在的故事情节,小说文本的故事容量和时空表现得以扩大。与此篇极为相似的另一言情小说《牛棚絮语》,更体现了作者在艺术结构上的精心剪
裁。小说描写“余”(忆英生)回苏州扫墓,火车上遇到昔日妓女碧梧。扫墓途中在牛棚避雨又遇碧梧,听其讲述浮沉于恨海的人生遭遇,近年如何阅尽人间沧桑、最后嫁一老人为妾。两篇小说都是第一人称“我”的介入,作为一个并非“听书人”的角色联结现在、过去时空。在这两篇小说中,时空的前后转换并非完全是西方小说的严格意义上的倒叙、插叙等叙述手法,而是同时继承有古代文言小说中“叙事人在某一特定情景下听某一人物讲述他自己或别人过去的故事这一模式”。但包天笑的这些短篇已经明显不同于古代文言小说的叙事传统,因为第一人称叙事的“我”或“余”不再仅是一个存在于作品开始和结尾的“旁听者”,而是时隐时现地同“讲述人”发生着或深或浅的联系,介入到所讲述的故事中,因而作品也就更真实,从而增强了感染力。《堕落之窟》不足三千字的笔墨,却以平淡、自然的文笔,为读者描绘了一幅生动逼真的都市人生“写生画”。该文令人重视的是作者揭开“堕落之窟”的帷幕时所采用的全景扫描式的视角,作者并未直接对窟中人物的外貌、心理和他们的胡作非为作正面描述,而是将其中的人物和物品采用细节放大的特写手法,把瞥见这个“堕落之窟”的那一瞬间的印象、情绪和感觉传递给读者。纷乱的“堕落之窟”的具体景象,再加上作者又从不同的视角进一步丰富画面的内容,增添了色彩的对比,同时也透出了这一场所特有的“又热又腥又香又臭”的气氛,并使整个画面充满戏剧性的暗示,鲜明地表露出作者的冷嘲热讽之情。全文首尾照应,层次清晰,在描绘窟中景象时既注意突出人和物品的细节特征,又注意使之交互映衬,通过画面的措置,气氛的渲染,不言而喻地显示出窟中人生活的猬邪淫靡,灵魂的卑鄙可憎。小说的结尾通过茶房的对话,又对揭露洋场恶少的丑恶灵魂重重地涂了一笔。该篇构思精巧,情节淡化到几乎无情节可言,却包容有丰富的思想容量和生活内容。
三、叙事时空、视角的启由转换
中国传统小说多用客观的第三人称全知叙事,缺乏由叙述者“我”讲述故事主人公“我”的故事,而西方小说中叙事方法则多种多样。中国译者对西方翻译小说中第一人称限知叙事有一个从难以理解接受到逐渐模仿应用的过程。第一人称叙事即作品通过第一人称“我”进行叙述。由于故事是从“我”的观察中得来而又由我将所见所闻讲述给读者,因此便增加了作品的真实感和生活气息,也由于创作主体和叙述主体的统一而产生独特的艺术效果。刚才提到的《影梅忆语》、《牛棚絮语》中便运用了主观、个性化的第一人称叙事。《牛棚絮语》中“余”同故事讲述人碧梧原是相识,“余”之朋友与碧梧之生活道路大有关系,作品正是通过这些关联,以“余”之视角观察、倾听、感受碧梧的现在和过去,于是整个作品带有“余”的个人感情色彩,尽管这种感情体验是轻微的、淡淡的。作品将“余”同碧梧的相遇归之于“缘”字,因而在同碧梧的三次相遇中,通过“余”之视角营造了缥缈虚幻的环境氛围。这些情景交融的景物描写带有传统文人诗画的韵致,淡笔白描,而一种闲淡的情绪却含蓄在其中。透过这情景交融的背景和景物描绘,背景中人的碧梧也完成了“出污泥而不染”的形象塑造。由于第一人称叙事视角的运用,作品尽管不是作者个人的生活经历却带有主观性的个人抒情色彩。作品由于第一人称视角的叙述,所以显得十分真实。
《牛棚絮语》中从“我”的角度观察、叙述、推进情节故事的发展,尽管已经具有作者个人的情感抒发,但这份情感毕竟极淡极轻。更具有现代意义的叙事方式应该是小说中的故事并非为“我”所见闻,而是为“我”所经历,这是侧重主观表现、个性化的第一人称叙事。即作品直接以“我”作为主人公介入故事,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泪点》即成功地展示了第一人称讲述主人公自己故事的艺术魅力。小说所写内容其实确是包天笑个人的一段情感经历,这在他的“回忆录”中曾有相关记载。作品中“我”与舅家表妹宝幼时两小无猜,但由于“我”家贫寒,终未能结合。“我”另娶他人,而宝却不知为何终身未嫁;于二十岁左右即郁郁得病而亡。宝临终前邀我前去,两人回首幼年情事,悲哀不已。死后由“我”料理她的后事。该小说由“我”娓娓道来,描写了一段纯洁真挚却文裹伤难舍的男女之情,于简单平淡中自有一种令人感动的力量。
包天笑的短篇创作中还有第一人称叙事的男一种形式即书信体,日记体小说,这些作品显然是在西方小说的启迪和影响下模仿创作而成,这不仅是由于他本人就翻译了一些日记体小说像《狗之日记》、《馨儿就学记》等,还因为当时已经出现了不少模仿《茶花女》的《玉梨魂》等日记体、书信体小说。《海滨消息》以三封书信的形式讲述了“我”、秋航与翠娟三人之间的情感纠葛,《冥鸿》则由十一封书信连缀而成。辛亥革命中洒血救国的烈士大哀,生前与夫人有约,每周通一封信,“未亡人”遵守前约,依旧每周写信一封遥寄亡夫在天之灵。前五封信主要控诉辛亥革命之后,政局逆转,军阀混战不休,政客图一己之私、鱼肉乡民,整个社会动荡不安,较清末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种种卑劣行径。后六封信主要抒发了“未亡人”回忆新婚燕尔,哀怜亡夫之后的身世。作者借此小说表达了哀痛革命先烈为国捐躯的苦心付之流水,国家前景灰暗不明的悲凉心情,抒发了对时局的焦虑和忧愤情绪。小说更多地融入了政治、时代内容,全篇贯穿着作者的人文关怀及社会批判精神。
四、细节描写烘托气氛
在包天笑的短篇小说创作中,由于作者有意对情节的淡化,描写的重心逐渐转移,因此细节方面如环境、心理的描写大量出现。其实晚清以来不乏有关环境,心理精彩描写的文学作品,但包天笑在其短篇中更加纯熟地将景物描写同人物心理、情感自然地结合于一体,做到了情景交融。例如小说《无线电话》就通过环境烘托人物惨淡哀婉的心理,整篇虽无故事情节发展,掩卷却仍感到愁云笼罩。小说开篇即是以环境描写同人物的内心独白交织在一起交代了故事背景,凄冷静寂的夜晚同女主人公孤独悲凉的心境水乳交融,也象征、蕴涵着世态的炎凉。包天笑本人曾说:“余读之如闻孤鸾哀鹄之音,不自知其凄然泪堕。”诚如是言。
《无线电话》中的内心独自在清末民初的小说作品中并不少见,但是《奇梦》中将潜意识化为梦幻、《冢中人语》中细致描述人死亡降临前的神秘幻觉,这类小说至民初时期却不多见。前者描写“缥缈生”在梦境中再次与人婚配,已经拥有婚姻的现实事实使他竭力想摆脱此梦,可内心深处却又对此怀有向往,因而对梦境难舍难分,于是他在“梦境”与“现实”中彷徨挣扎,既有对发妻的悔恨自责,又有对梦中女郎的痴迷渴望。《冢中人语》共有五章节:“余死”、“医生检验”、“埋葬”、“地底之汽车”、“大彻悟”,详细描述了“余”从病重而濒临死亡,到被放入棺材埋葬后进入地狱之门,然后乘坐地狱中之“列车”,最后又从病中醒来的整个幻觉过程,细腻生动地将中国普通大众对“死亡”、“地狱”等的种种幻想描述出来。作者成功地使用第一人称叙事方式,使整个作品不断地在一息尚存的“余”之幻觉世界和感受到的现实世间来回穿梭,“余”对生的眷恋、死的恐惧,以及从幼时直至现今整个一生的生活经历等都由“余”通过“回忆”、“幻想”等丰富的内心世界来完整地传达和展现。
综上所述,包天笑的短篇小说创作不仅在题材内蕴上开创了一片新天地,在艺术表现技巧上也进行了有意地探索。这些在西方小说影响下创作的短篇小说充分展现了中国古代小说向现代小说发展的过渡痕迹,它们既有对传统文言及明清白话短篇小说的延续承继,又有19世纪中期以后对西方小说的借鉴模仿,成为“五四运动”之前小说变革的一道亮丽风景,在某种程度上可称得上五四新文学的开路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