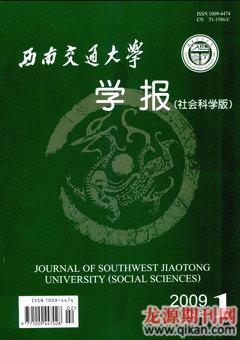李贺的长安经验与其宫怨、闺怨诗的创作
魏 娜
关键词:李贺;宫怨诗;闺怨诗;长安;太常寺;奉礼郎
摘要:在李贺的官怨、闺怨诗中,他在长安任职期间的作品不仅数量多,而且创作时间、地点非常集中,诗中女子在身份、生活环境和精神世界上呈现出一些明显的共同性,即她们都养尊处优,渴望感情的滋润,但却往往遭受冷遇,情感极度孤寂,生活也被边缘化了。这与李贺贵为皇族、踌躇满志而在长安任职期间却无人赏识。官居九品、壮志难酬的人生际遇和心理感受极其相似。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无奈使得李贺的宫怨、闺怨诗超越了对女主人公命运的单纯同情哀叹而转为对自己潦落抑郁的长安生活的叹息和对失败的仕宦生涯的自伤,从而意蕴深远。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09)01—0015—07
就李贺宫怨、闺怨诗而言,可分为长安任职前后和长安任职期间的作品。前者为六首,创作不集中于一时一地,且诗中女性在身份、生活环境、情感世界方面也呈现出多样性。后者为九首,与长安任职前后的创作相比,不仅数量更多,而且创作时间、地点非常集中。更重要的是,诗中女子在身份、生活环境和精神世界上呈现出一些明显的共同性。对这些共性进行阐述分析并挖掘其成因,就成为本文的重点。
一、宫怨、闺怨诗中的女性形象特征
李贺此类诗中的女性,要么是达官显贵家的妻妾,要么是身份更为尊贵的后妃,如《嘲谢秀才四首》、《难忘曲》、《答赠》、《感讽六首》之一都是以达官显贵家的妻妾为主人公。从李贺对女主人公穿着和生活环境的描写中可以看出这一点。《嘲谢秀才四首》中女主人公的服饰是“荷丝制机练,竹叶剪花裙”,绢质的绣花衣衫透露出轻盈、精美。《答赠》中女主人公则身着金色衣裳,显得华丽富贵。她们的夫婿,要么是持金鱼袋的武将,要么是玉树临风的贵胄公子,身份不同凡俗。《感讽六首》之五、《堂堂》则描写了被冷落幽闭的后妃,前者是失宠于汉成帝的班婕妤,后者是幽居破败宫院的妃嫔。这些女性因与权贵之人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与普通女子拉开了距离,不再是过着粗茶淡饭生活的平常女性,而是被带入富贵与权力世界的一群人。《难忘曲》和《感讽六首》之一则展示了女主人公不同的居住环境:一个是“夹道开洞门,弱杨低画戟”,一个是“舞席泥金蛇,桐竹罗花床”。这种画戟列门前、丝竹奏于室的环境,已明确了其中人物的身份。
这样一个衣食无忧的群体却大都体现出一种温柔富贵中的孤独感、哀伤感。这些女性多生活在侯门皇宫或骄奢之家。“飞香走红满天春,花龙盘盘上紫云”(《上云乐》),这是后宫的气派;“沉香熏小象”、“露重金泥冷”(《答赠》),这是达官富贵家的奢华。无论是哪一种生活环境,都华丽得足以让人眩晕,也温软得足以让人陶醉。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种令人羡慕、近乎完美的生活环境中,却弥漫着女子们的孤独哀伤之感。这种孤独和哀伤,不是心满意足后的无病呻吟,而是根本就有的、无论如何都弥补不了的遗憾和缺失。引发这种遗憾和缺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或因被弃置冷落而黯然神伤,或因与心上人不得相见、长相厮守而感到阵阵钻心的痛楚,或因虽风光一时却终难逃脱冷落、凄凉命运而倍感无奈。
《难忘曲》的描写有助于我们理解以上的特征概括:
夹道开洞门,弱杨低画戟。帘影竹华起,箫声吹日色。蜂语绕妆镜,画蛾学春碧。乱系丁香梢,满栏花向夕。
开篇就已构建了一个相当豪华气派的生活环境:“洞门”一词透露出幽深、高贵之感,层层洞门使这处官宅显得高不可攀、使人望而生畏;“画戟”一词更突出了宅第主人的尊贵逼人之气。在这样一个弥漫着权势的空间中,嵌入了由帘影、竹华、箫声、蜂语、画眉构成的仅属于上层女性的精致而优雅的生活。在诗情画意的环境中,女主人流露出对恩爱欢情的甜美企盼,而等待她的却是遭受冷落、坐待春老的命运。“乱系丁香梢,满栏花向夕”是极富深意的象征:前者蕴含着期待的幸福,后者则是在失去希望与关注后,一种萎谢的状态、伤感的叹息。清代方扶南《李长吉诗集批注》对此诗的批语是“写闺怨也”,这怨情就源于富贵闲雅中的幽独生活、盎然春意中的失落心境。
再如《嘲谢秀才四首》:
谁知泥忆云?望断梨花春。荷丝制机练,竹叶剪花裙。月明啼阿姐,灯暗会良人。也识君夫婿,金鱼挂在身。(其一)
铜镜立青鸾,燕脂拂紫绵。腮花弄暗粉,眼尾泪侵寒。碧玉破不复,瑶琴重拨弦。今日非昔日,何人敢正看?(其二)
洞房思不禁,蜂子作花心。灰暖残香炷,发冷青虫簪。夜遥灯焰短,睡熟小屏深。好作鸳鸯梦,南城罢捣碪。(其三)
寻常轻宋玉,今日嫁文鸯。戟干横龙虞,刀环倚桂窗。邀人裁半袖,端坐据胡床。泪湿红轮重,栖鸟上井梁。(其四)
这组诗描写一位新婚不久的贵妇,诗中多次提到她的装束打扮:“荷丝制机练,竹叶剪花裙”、“燕脂拂紫绵”、“腮花弄暗粉”。这样精美别致的服饰,这样细腻香柔的打扮,决非寻常女子所能做到,而她的夫婿又是“金鱼挂在身”,可见地位的不凡。如此锦衣玉食的生活,如此有身价的夫婿,非但没有让新婚少妇感到喜悦与甜蜜,反倒使她“眼尾泪侵寒”、“泪湿红轮重”,原因便在于她发现自己所嫁非人,对心上人的思念、期盼能与之长相厮守的愿望冲淡了甚至早已超过了新婚的喜悦和对荣华富贵生活的享受。诗中“灯暗会良人”、“好做鸳鸯梦”都是一种渴望与幻想,是对内心深处真实情感的再三回味。然而“碧玉破不复,瑶琴重拨弦”的现实彻底撕碎了她所有的幻想,绝望的心境与优越的生活现状形成极端的对峙、隔阂。精神上的牵挂与孤独感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无法得到弥补,因而这种环境只是她的居住之所,而无法成为她赖以寄托心灵的家园。
《感讽六首》其五则把对女性凄恻哀怨的咏叹转向受汉成帝恩宠一时的班婕妤:
晓菊泫寒露,似悲团扇风。秋凉经汉殿,班子泣衰红。本无辞辇意,岂见入空宫?腰裰珮珠断,灰蝶生阴松。
据《汉书·班婕妤传》记载,她被汉成帝恩宠一时,并非因色而是因德。她拒绝与成帝同辇出游的事迹就很受史学家和文学家的赞赏。这并不仅仅因为她在面对皇权威慑力和恩宠的诱惑力时,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无畏无惧和冷静平淡,更因为她在恳切犀利的陈辞中所表现出的自谨自律。但在帝王眼中,女子的美色似乎比德行更重要,德行是应该置于朝堂上的严肃话题,而当帝王脱下朝服,走向令他心旷神怡的后宫世界时,他从一个充满神性色彩的天子变成了一个充满七情六欲、风流缠绵的男人。这种角色的转变决定了他的取舍亲疏,他所期待的是妃嫔们能以其挑逗和多情迎合他完成这段对人生享乐本能的回归,以此来平衡朝堂上的拘束庄严与后宫内的任性随情。而班婕妤的悲剧恰恰在于她将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德行的实践上,并在这种实践中显现出坦然于皇权的不卑不亢,而不谙也不屑于尤物之道、谄媚之姿。从某种意义上讲,她在后宫这样私密化、生活化的环境中以她的
端庄和无可挑剔唤起了帝王的社会角色意识和由此意识带来的逼仄感,并以高度的自律削弱了作为女性,尤其是作为妃嫔应具的娱情悦性色彩。这对于扮演男人和帝王双重角色的汉成帝来说是终难长久欣赏的。虽然班婕妤最终退居长信宫,侍奉皇太后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和体面的结局,但终究掩饰不住失势于尤物、情绝于帝王的凄凉无奈。
李贺这首诗正是基于班婕妤这个形象所富有的历史文化内涵进行的深情咏叹。诗中撇开对班婕妤优越生活的正面描述,只是让读者从人物身份自然联想到她良好的生活环境,而将笔墨集中到对其孤独感的揭示当中。首两句诗中,以托名班婕妤所作《怨歌行》中的团扇意象抒写出恐被弃置的焦虑与担忧。这种心理上潜在的不安是几乎所有古代女性普遍的感受,特别是像班婕妤这样处在相互倾轧的后宫生活中的妃嫔,对未来命运的焦虑就更为突出;中间四句将被弃的预感和担忧推向了现实境地:她充满伤感的自怜和哀怨不平的自我审问,都是在其封闭的内心世界中完成的,流露出无人交流的精神孤寂;末四句将这孤独、寂寞随时间而推移,从当下推向未来。“佩珠散地”、“纸飞阴松”暗示着主人公的生命行将完结,即使她是以一生的孤独为代价也换不回他人对自己的关注。
此诗的特别之处在于对红颜寂寞背后的根源做出进一步追问。“秋凉经汉殿,班子泣衰红”展现的是班婕妤在长信宫中寂寞度日、容颜空老的画面。从表面上看,她像是为容颜的凋零而哭泣,而人们也极易将她的伤感和孤独归咎于年老色衰。但令人寻味的是班婕妤的凄凉孤独并不由她的色衰而致,恰恰相反,容颜的凋零与孤独的相伴都是她被弃后不得不承担的痛苦。在李贺看来,“本无辞辇意,岂见入空宫”才是班婕妤被打入冷官的真正原因:她谨守后妃之德,品行端庄,反而酿成了自己的人生悲剧。这样的结局较之于色衰被弃,显然带有更浓重的荒诞意味。正是基于这种荒谬的因果关系,李贺对班婕妤独坐“泣衰红”的寂寞就不仅仅是叹息和同情,而是开始对这样的命运做反思和审问。“本无”、“岂见”这样的词语表露出的绝不是女主人公发现过失后的懊悔之意,而是她对完美品行被否定的疑惑不解。疑惑之情越强烈,越显现出班婕妤在内心孤独的折磨下所承受的委屈和哀痛。李贺对班婕妤精神孤独剖析的深刻之处,不仅在于体现了导致其精神孤独根源的荒诞性,从而使得对其命运的态度从简单的感性哀叹走向了理性的反思,更在于他并没有将班婕妤的孤独感简单地归为色衰被弃,而是通过对她命运的陈述,向读者提出了两难选择:弃德取宠,不使红颜空寂寞;或是自律谨严,却要寂寞老去。
总之,李贺宫怨、闺怨诗中的主人公,无论是被弃置的女性、思恋心上人的女性、还是风光过后独守寂寞的女性,她们与周围富贵荣华的环境之间都是一种僵硬、冰冷的关系。生活环境中过于华美的陈设与女子的叹息、独坐或是哀伤形成鲜明对比。无论是雄伟的宫殿,还是精美的闺房,对这些女子来说,都像养尊处优的牢狱,困住她们的青春,也窒息了她们的生命与温情。既然在这样的环境中已失去了生活的色彩和意义,她们怎么可能不叹息,不伤感,又怎么可能不与之疏离?
二、李贺的长安经验
以上对李贺宫怨、闺怨诗特征的分析仅止于诗歌的文字层面,而文字毕竟是诗人生活状态、生活环境的物化形式。因此,这些绮罗香泽之气与感伤叹息之情相交织的宫怨、闺怨诗与诗人在长安三年特定的生活境况、人生体验到底有无关系,是怎样的关系,就成了值得关注和不可回避的问题。
从身份上看,李贺身居长安时,正在太常寺任奉礼郎。太常寺是唐代九寺之一,主管国家礼乐、郊庙、社稷之事,设奉礼郎二人,从九品上。《旧唐书·职官志》载,奉礼郎一职主要是:“掌朝会祭祀君臣之版位。……大凡祭祀朝会,在位拜跪之节,皆赞导致之,赞者承传焉。……凡春秋二仲,公卿巡陵,则主其威仪鼓吹之节而相礼焉。”李贺所任的奉礼郎虽只是从九品的小官,在朝廷权贵眼中,也只是个微如草芥的小角色,但他毕竟肩负着朝廷赋予的使命与职责,在祭祀、巡行等庄严重大的活动中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所见识的人亦非等闲之辈,他们的威仪、精神境界对李贺不会不产生一定的影响。
而从生活环境看,诗人起居的小环境是相当简陋的,“古壁生凝尘”(《伤心行》),“柴门车辙冻,日下榆影瘦”(《赠陈商》),是他对自己居所环境的勾勒,我们确实无法将诗中的景象与高门大户相联系。但从另一方面看,李贺在长安的住宅位于崇义坊,此坊在朱雀门街东第二街、从北向南第二坊,与长安城最繁华的两条街——朱雀门南北大街、含光门至春明门的东西大街分别只有一坊之隔。更重要的是,长安城的地势是东高西低,以长安城南北主干道朱雀门街为界,街东各坊较之于街西各坊的地理位置偏高,水质也好,因此,特殊的风水结构使朱雀门街以东各坊聚居了大批朝廷官员、世家贵族,而朱雀门街以西各坊则成为经济实力雄厚而政治根基薄弱的富商巨贾及普通民众的聚居区,由此形成了长安城东贵西富的居民分布格局。李贺所在的崇义坊恰属于王侯贵族密集的朱雀门街以东的坊群,他就在这个达官显贵云集的地方生活了三年,耳濡目染的自然是绝不同于市井小民、寻常巷陌的官家气派和上流社会、名门闺秀的雍容气度。而这一切又都融入了他的生活,成为他生活环境的一个基调。
李贺任职的地方在太常寺,位于皇城之内,东邻安上门街,街东为太庙;西邻承天门街,街西为鸿胪寺;北邻太仆寺、太府寺。在唐代,九寺属中央机构,在其中供职的官员不乏品级较高者,如各寺的卿、少卿分别为正三品、正四品大员。李贺供职的太常寺就被九寺中的三寺——鸿胪寺、太仆寺、太府寺所环绕。不仅如此,太常寺就处在三寺一庙所构成的包围圈中心,与太庙只有一街之隔,而太庙又是大唐王朝列祖列宗灵魂的安息地,神圣庄严。置身其中的李贺自然也处于权力与威严相结合的网中。若放眼整个皇城,就能更加清晰地看到大大小小的中央机构整齐而密集地排列着,构成了一张更大的充满无限神圣感的网。而李贺以奉礼郎的身份活动在太常寺乃至皇城中,在这样一个砌起高高城墙因而也就和庶民社会几乎隔绝的地方,他的种种活动必然与上层社会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
如果从更大的范围看,李贺生活在天子脚下,长安城是大唐帝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集中了无上的权力与无限的财富。“鸾车迥出仙门柳,阁道回看上苑花。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便展示了一幅气度恢弘的长安图景。在李贺所处的时代,唐王朝的国势已不可扭转地渐趋衰落,但中唐时期的社会却掀起了追求豪奢绮靡生活的风尚,历几代帝王而不衰。这与中唐的帝王希冀以此种泡沫繁荣来重缔盛世太平景象的心理需求有关,是战乱后萌生的一种自我补偿与怀旧情绪。集中体现在大兴土木、耗费钱财建造或购置家宅、厚葬成风、奢于游宴上。《旧唐书·元载传》中记载了代宗朝宰相元载府邸无以复加的恢弘华美
之势:
城中开南北二甲第,室宇宏丽,冠绝当时。又于近郊起亭榭,所至之处,帷帐什器,皆于宿设,储不改供。城南膏腴别墅,连疆接畛,凡数十所,婢仆曳罗绮一百余人,恣为不法,侈僭无度。…
这种骄奢已到了僭越法度、畸形膨胀的地步。像元载这样财大气粗、制造声势的官员还有很多,如平定安史之乱的名将郭子仪,据《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载:郭“宅在亲仁里,居其里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者不知其居。前后赐良田美器,名园甲馆,声色珍玩,堆积羡溢。不可胜纪”。
与以豪宅夸饰富贵一样,厚葬也成为中唐时代的人们炫耀财力的一种方式。《唐会要》“葬”条云:
元和三年五月,京兆尹郑元修奏:王公士庶丧葬节制:一品二品三品为一等,四品五品为一等。六品至九品为一等。凡命妇各准本品,如夫子官高,听从夫子,其无邑号者,准夫子品。荫子孙未有官者,降损有差。其凶器悉请以瓦木为之。是时厚葬成俗久矣,虽召命颁下,事竞不行。
从这则材料中可以看出当时社会上层厚葬攀比之风的积习已久和愈演愈烈,以致在这种比富斗阔的风气笼罩下,连诏命的权威性和震慑力也显得微不足道。
在社会上层厚葬之风的影响下,下层社会也竞相效之,进而形成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和社会观念。在此推动下,人们对厚葬的追求和实际操作到了近乎疯狂的地步:
长庆三年十二月,浙西观察使李德裕奏:缘百姓厚葬,及于道途盛设祭奠,兼置音乐等,闾里编甿,罕知报义,生无孝养可纪,殁以厚葬相矜。丧葬僭差,祭奠奢靡,仍以音乐荣其送终,或结社相资,或利息自办,生业以之皆空,习以为常,不敢自废。人户贫破,抑此之由。
与购置豪宅、追求厚葬同样风行的是以社会上层为主的游宴娱乐。这是上层社会纵乐享受的表现,更是中唐帝王刻意制造国泰民安、太平繁荣景象的需要。《册府元龟》卷110载:
贞元六年四月,帝日:“朕顷以四方不宁,宵衣旰食,百僚亦遑遑无暇。今兵革渐息,夏麦有登,朝官有暇日游宴者,令京兆尹不须闻奏。”
唐德宗是一位疑心颇重的皇帝,史载其当政期间,“朝士有相从者,金吾皆伺察以闻,宰相不敢私第见客。”但他对宴游活动非但毫不忌讳,反而政策十分宽松。这足以说明中唐帝王为营造四海升平景象所作的努力,而群臣必然要以积极的姿态对此做出推波助澜式的回应,从而使游宴之风大兴。宪宗即位后,为群臣游宴活动创造了更加宽松的条件:从大型的暇日宴饮到平时的交往饯别,均无须上奏。不仅如此,宪宗还特别强调群臣在这些活动中可尽欢尽兴。
虽然这种豪奢富贵之景充满畸形和荒谬的色彩,但在客观上确实为中唐时期的社会生活披上了一件精致华美的外衣。而李贺正值这样一个尚奢之风尤重、积淀尤深的时代,他身处的长安城正是时代所炮制的繁荣景象最真实的缩影。李贺个人居住环境的清贫、简陋是个不争的事实,但他不仅仅是居住在“灯青兰膏歇,落照飞蛾舞”(《伤心行》)的陋室中,也生活在一个以权力为经、以财富为纬的充满贵族气的空间里,在他周围,到处散发出公子王孙、浮华都市的气息。他陋室中泛青的灯光丝毫也妨碍不了他生活中更为广阔的环境空间——崇义坊、朱雀门街以东的贵族区乃至整个长安城的五光十色。
长安是唐帝国的心脏,大唐王朝的精华几乎都在这里沉淀、凝聚。对于像李贺这样的读书人来说,长安必定是他梦寐以求的地方,因为在这里最有可能碰到千载难逢的机会,也最有可能实现他的人生理想甚至出现他一生命运的转折点。李贺不是一个能看淡功名前途的超脱者,他有自己的理想,也热衷于仕途政治,有过“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南园十三首》其五)的壮志,有过“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雁门太守行》)的信念,也赞美钦佩甚至羡慕驰骋疆场建功立业的将领。
李贺是个资质颇高的诗歌天才,他十五岁就以乐府歌诗名于世,与前辈李益齐名。更重要的是,他常以宗室王孙自居,在很多诗作中他都很自然地将自己归入皇室的行列。如其《唐儿歌》称“眼大心雄知所以,莫忘作歌人姓李”,《金铜仙人辞汉歌·序》中有“宫官既拆盘,仙人临载,乃潸然泪下,唐诸王孙李长吉作《金铜仙人辞汉歌》”。他对皇室后裔身份的看重不仅仅是出于一种虚荣和自尊,更源于与李氏王朝血脉相连而产生的责任感、使命感。屈原以“帝高阳之苗裔”自居,所以李贺在《赠陈商》中有“楞伽堆案前,楚辞系肘后”的诗句,表现出对楚辞超乎寻常的喜爱,这或许正是源于他对自己皇族身份的强烈认同感。
理想、才华、热情,甚至和唐王室这种特殊的亲密关系,李贺已是占尽占全了。照理,凭借这些资本,他应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但事实并非如此,他只是以从九品奉礼郎的身份在大唐最繁华的城市中生活了三年,满腹才华无人赏识,理想和热情也只能渐渐冷却。在长安城这个人生机遇最多的地方,却没有他实现人生价值的一方舞台。他的那份因血脉相连而无法祛除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一再地被压抑于心灵深处。尽管他是皇室后裔,但家道已然中落;尽管他才华横溢,但长安城中绝不少他一个。这种尴尬无奈的现实状态与理想境界的巨大落差,使李贺的心灵充满了挫败感和无尽的叹息。在繁华的长安城里,当其他人还在摩拳擦掌、满怀理想的时候,他已经是“长安有男儿,二十心已朽”(《赠陈商》)。信念的落空,理想的受挫,竞让他吟出“秋姿白发生,木叶啼风雨”(《伤心行》)这样沉重的诗句;“驱马出门意,牢落长安心。两事向谁道,自作秋风吟”(《京城》)更是把他那种“落莫谁家子,来感长安秋”(《崇义里滞雨》)的孤独、失落写得淋漓尽致。
在长安失意失志的经历,使李贺的心灵游离于喧闹、浮华的城市之外,游离于他周围花花绿绿的生活之外。虽然在其中他也有过宴饮游乐的畅快,但那只是瞬间的美丽,与从他内心深处渗出的彻骨的孤寂与落寞感相比,那样的玩乐享受只是浮在水面上星星点点的油花,因理想受挫而生的低落、伤感构成李贺私人生活的灰色基调,使他与长安城的明亮、繁华相隔阂、疏离。
三、伤人伤己的诗歌意蕴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李贺与其宫怨、闺怨诗中女主人公在身份、生活环境及心灵世界方面均存在着一定的相似之处:两者的身份及所接触的社会群体均不寻常,对上层社会来说,他们是微不足道因而也是极易被遗忘的;但他们的身份和人际圈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成为普通的平民,所以在百姓眼中,他们却又是完全不会或不完全会属于普通生活世界的人。上层的忘却和下层的疏离使他们进退失据,处境尴尬。无论是李贺还是他笔下的女主人公,他们周围的生活环境都充满了令人惊叹迷醉的精致华美和雍容贵气,但置身于其中的他们都表现出“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凹的孤独、哀伤、落寞之感,从而与光鲜诱人的外在环境产生了巨大反差,表现出心与境的疏离。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也能明显看出李贺长安生
活对其宫怨、闺怨诗创作的深刻影响。这类诗歌从表层文字形象到深层心灵世界,无不打上了他这段人生历程的印记。就表层文字形象看,诗人以上流社会中的女性为表现对象,与其所处环境有很大关系。他生活在显贵云集的街区、生活在繁华大气的长安城,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所目睹的多是身份高贵的女性而非贫家女子。对于她们的生活和心境,他并不陌生。正是因为对上层女性的身份角色有深刻的理解和把握,李贺才能准确地捕捉到她们绝不同于市井女子那种“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的坦率明快心理,并在对这些女性生活环境与精神世界的对比中完成对其细腻无助、欲说还休的抑郁愁苦心态的发掘,进而将这些上层社会女性内心的孤寂忧郁恰如其分地展现出来:他写出了这些女子被红墙绿瓦困住的青春与性情,写出了她们渴望感情但往往遭受冷落的忧伤和叹息,也写出了她们因身份与修养而不得不将愿望深埋于心的孤独与无奈。
就深层意蕴看,李贺对女主人公表示深深同情与理解的同时,也是对他自身命运的哀叹与诉说。他不是单纯地怜香惜玉,讲述女子不幸的故事,而是与她们同病相怜,由伤人到伤己,由伤己而更加伤人。在这些一生凄凉的女子身上,我们总能隐约看到李贺的影子,听到他的叹息。女子们渴望被重视、被关怀、能与心上人两情相悦的内心需求,和李贺急切希望能为朝廷所重、为慧眼人所识的愿望是何等相似。一言以蔽之,他们同处在繁华掩盖下的寂寞角落,扮演着微不足道的角色,但都在执着地追求自我人生价值和理想生活状态。
但是,雍容舒适的生活并未给李贺诗中的女性带来相应的幸福与满足,相反,极度优越的外部生活环境与其极度孤寂的情感形成了巨大落差,从而使看似处于其生活空间中心的女主人公们因内在精神世界与外在生活环境的极端错位而被边缘化。同样,当李贺无法在长安这个充满机遇诱惑与缤纷色彩的城市中实现最佳的人生定位,无法体味融入主流社会的优越感时,长安的满目繁华和优游闲适对他来说就成了随时都可以剥离掉、无法渗入他生活的过眼云烟。当李贺及他笔下的女性的人生价值均无法实现,理想的生活状态将永远可望而不可及时,他们都不禁产生了彻骨的悲凉与满怀的愁绪。人生际遇和心理感受的相似,让“二十心已朽”的李贺更加了解这些被弃置于角落的女子。对她们的吟咏也就超越了单纯的同情哀叹,而更深地转为对自己潦落抑郁的长安生活的叹息,对失败的仕宦生涯的自伤。于是,与笔下的女主人公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悲人悲己之情,便顺理成章地在李贺的这些宫怨、闺怨诗的墨迹中洇染开来,化也化不开。
(责任编辑:武丽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