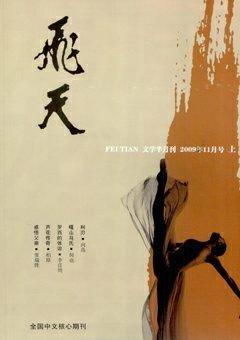试析勃洛克《十二个》中的音乐精神与形式
在阅读勃洛克长诗《十二个》的过程中,你会有一种强烈的感觉,那就是它形式的严整与内在的律动给你一种欣赏一曲交响乐的感觉。诗人在谈起他创作这首诗的心情的时候也说:“当我在写作和完成《十二个》之后,我一连好几天在生理上、听觉上,都感觉到周围有着巨大的喧响——一种混合的喧响。”[1]我对诗人这句话产生了追问,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喧响”?为什么诗人会在创作中产生如此强烈的生理感受,特别是听觉感受?诗人在此前几乎同时发表的文章《知识分子与革命》的结尾写道:“精神即音乐。恶魔曾经要求苏格拉底听从音乐精神。用整个身躯、全部心灵、完整的意识去倾听革命吧。”[2]基于此,我们稍微有点明白了,原来诗人是在“用整个身躯、全部心灵、完整的意识去倾听革命”。
同时我们会从《知识分子与革命》这个结尾很自然地联想到尼采的《悲剧的诞生》。这就不得不从俄国象征主义说起了。“俄国象征主义在理论上从尼采、叔本华和瓦格纳那里拿来并发展了‘音乐核心、‘艺术综合等艺术观”[3]。在叔本华看来,“音乐乃是全部意志的直接客观化和写照”[4]。只有音乐才能最直接,最深入地表现世界的本质。尼采在主要反映其艺术观的《悲剧的诞生》中也认为“音乐象征性地涉及到太一的核心的原始矛盾和原始痛苦,它象征着一个超出一切现象的领域,比之于音乐恐怕一切现象都只是譬喻”[5]。并用“酒神”这一代名词加以强化,认为音乐以一种理性所无法把握的力量直接进入世界的本质之中,揭示了世界心灵深处的“原始冲突”和“原始痛苦”。俄国象征派的思想之父弗·索洛维约夫主张“在人类艺术中对完美的先验有三种类型”,其“首要的一类称为直接的或者有魔力的”,即“音乐和某种意义上的纯抒情诗”[3]。有“太阳诗人”,“音乐诗人”之称的巴尔蒙特深受尼采酒神艺术观的影响,认为“音乐是最具有魔力的艺术,音乐家和诗人一样,阐释世界,确定人与自然的联系,从混沌创造和谐的世界”[3]。亚·勃洛克本人在自己的审美体系中同叔本华一样将音乐作为世界的本质来看待,“音乐创造世界,她是世界的精神之躯”,“世界在强劲的节奏中发展……世界的发展即文化,文化即音乐的节奏”,“音乐原子是最完美的……因为她富有创造性”,“若诗歌走到尽头,她大概将……沉没在音乐中”[3]。这样,勃洛克认为文学进程的逻辑在于越来越把诗歌与音乐相融合。象征主义理论的代言人,“青年象征派”的最大代表之一安·别雷更是直截了当地宣称:“对于成为主音的音乐来说,展示美好的其他一切形式难道不将仅仅占据泛音的位置吗?”[6]
由以上论述可见,尼采、叔本华对于音乐精神的强调对俄国象征主义在理论上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在这种艺术理论指导下,象征主义艺术家进行了诸多的创作尝试。在这里主要关注其在文学上的创作实践。
文学创作方面最典型的“有意结合”的代表是亚·杜勃罗留波夫。他的作品集《笔记第1号》的各个章节都冠以音乐的名字并加注音乐提示术语,以点化读者注意作品中文字与音乐的结合,如《葬礼进行曲》(庄严的柔板),《合唱》(近乎柔板的行板),“哀歌”(柴可夫斯基第六交响曲《悲怆》)。显然这种结合给人以有点生硬的感觉,另外安·别雷在自己的早期创作中也有类似的做法。他的诗作《前交响曲》中也附加指示性的音乐术语,在稍后的四部《交响曲》中不再用这种加注的方式,但也保留了音乐名称和音乐主题:《北方交响曲》(《第一英雄交响曲》),《戏剧交响曲》(《第二交响曲》),《复归》(《第三交响曲》),《风雪高脚杯》(《第四交响曲》),他还在谋篇布局上借鉴交响乐的曲式结构,使得作品既像散文,又像韵文,充满着节奏和韵律。同时,象征主义诗人都注重作品的节奏感,音乐感,在巴尔蒙特,勃洛索夫,安年斯基,勃洛克,别雷,伊万诺夫等诗人的诗作中,都能或强或弱地感受到诗歌的节奏性。从这些创作我们可以感觉到,大多数象征主义作家追求的是一种音乐一样的美感和节奏感,并且他们的诗作大部分是抒情诗。勃洛克早期的诗作也是这样,随着俄国国内形势和历史发展的变化,及诗人思想和艺术的不断变化和成熟,勃洛克逐渐摆脱了对抒情诗创作的偏爱,开始尝试诗剧和叙事诗的创作。这段时间勃洛克在日记中写道:“当今有才华的人的缺点,人们已经说过多次,就是作品太短小,缺乏深呼吸……蜻蜓点水 ,浅尝辄止,然后敲锣打鼓,万事大吉。”[7]不久后诗人写信给别雷:“……今后我不再是一个抒情诗人”[7]。勃洛克逐渐同象征主义疏远,象征主义在俄国的主流地位也逐渐被新的现代流派所冲击。但是勃洛克并没有彻底扭断与象征主义联系的纽带,他认为“世界在强劲的节奏中发展……世界的发展即文化,文化即音乐的节奏”[6],这表明在对音乐精神的理解方面,诗人与其他象征主义者有所区别,也是其思想逐渐贴近社会和生活的表现。同时他也认为音乐是世界的本质,世界的一切现象都蕴含着音乐。
由此我们把目光转向勃洛克著名的长篇叙事诗《十二个》,当我们认真阅读体会这首长诗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该诗本身从整体上便可以看作一部含有三个乐章的协奏交响曲,第一个乐章描绘一片混乱的场景,表达一种混沌的情绪(诗中第1节);第二乐章则表达一个悲壮的爱情故事,比德鲁哈内心狂乱的斗争(诗中第2-10节);第三乐章则是由混乱到澄明,基督的出现,由混乱到和谐(第11-12节)。我们知道,诗歌和音乐的相通之处就在于它们都传达一种或多种情绪,通过情绪我们可以由诗体会到音乐,也可以由音乐体会到诗。我们先看该诗的第1节,也就是所谓的第一乐章,这一节诗像陈列室一样,把各种人物对革命的反应陈列出来,每类人物(老太婆、资本家、作家、雄辩士、神父、贵太太、妓女等)都站在自己的角度看待革命,多声部交叉,像各种乐器声音齐鸣,诗人明显地在传达一种革命中混乱嘈杂的情绪或状态。这便是背景式的第一乐章;诗歌的第2节到第10节大部分在叙述一个发生在革命背景下的爱情故事,它所着重传达的是主角“十二个”之一的彼得鲁哈个人在爱与恨的情绪交织中狂乱的内心斗争,2、3、4、5节写彼得鲁哈发现自己的旧情人卡奇卡躺在了大兵敌人凡尼卡的怀中,4、5重在写彼得鲁哈的心理活动,特别是第5节以第二人称的角度传神地展现了他的心理:“唉,唉,来跳舞吧! 你那双小脚多漂亮啊!”“唉,唉,玩吧!心在胸口狂跳着!”“唉,唉,犯罪吧!从此我才能安心!”于是,第6节误杀了卡奇卡,面对自己亲手杀死的自己的爱人的尸体,他痛苦,他悔恨!“我这个愚笨的人就杀死了她,我一时心急就杀死了她!”(7节)后在同志的劝说下“又快活起来了……”但他并没有摆脱悔恨的心情,一直处在苦闷中:“哦,你苦中苦!/郁闷的郁闷/死的郁闷!”但很快他找到了把这一切的恨转移的对象,就是资本家:“资本家,你们像雀儿一样飞!/我要喝你们的血/为了我那情人/那黑眉毛的姑娘……”从而也在个人爱情命运与革命之间找到了协调。(8、9、10节)这种爱与恨交织的情绪汇成了第二乐章。在第11,12节,彼得鲁哈也从爱情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十二个不信仰圣明的人”“……踏着威武的步伐走向远方……”而在他们前面则出现了戴着白色玫瑰花环的耶稣基督!耶稣的出现使得一切变得澄明和谐,也使得全诗达到了高潮,使人感体验到一种崇高。这便是第三乐章了。通过这种阅读,我们从该诗交响曲式的结构中获得一种音乐体验,相信这也是诗人创作过程中所体验到的。另外,对于诗歌细部的节奏与旋律,我们来引入一个音乐概念:音乐形象。无论是传统的交响乐还是近代的交响乐中,一般都有一个或多个主要音乐形象,它们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多次地出现在乐曲中,主要的音乐形象一般都带有特征,有的是在旋律上,有的是在节奏上,有的是和声的序列或和弦的展开,有的还会通过某种特性的乐器表现出来。我们可以在《十二个》找到多个起类似功能的这样的形象,如“暴风雪”,“唉,唉,没有十字架啦!”,“前进,前进,劳动的人民!”,“嗒拉—嗒—嗒!”的枪声等这些有着丰富意味的句子和形象,在整个诗中反复出现,在形成强烈节奏感的同时,用来强调某种强烈的情绪或营造一个特殊的氛围。我们重点来看“暴风雪”这个形象,在诗中它在不同的章节以不断改头换面的形式出现了不下十次,贯穿全诗的每一个章节!它给这首诗定了基调和主旋律,在交响乐中完全可以扮演第一小提琴的角色。此外,对于诗歌末节意外的基督形象的出现,我们也可以用一个交响乐术语来解释:华彩乐段(Cadenza),它原指意大利正歌剧中咏叹调末尾处由独唱者即兴发挥的段落。后来在协奏曲的乐章末尾处也常插用此种段落,通常乐队暂停演奏,由独奏者充分发挥表演技巧。这部分演奏较自由,难度也较高,因而也较引人注目。《十二个》末尾基督形象的出现可以说正是这种即兴发挥的结果,诗人本人在谈到为什么基督形象会在结尾出现时说“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在长诗中出现了基督形象”[8]。
《十二个》这种交响乐式的内在结构与特征显然继承了俄国象征主义推崇音乐的传统,但我前面也说过,勃洛克的审美体系与这种传统有所区别,他强调“世界在强劲的节奏中发展……世界的发展即文化,文化即音乐的节奏。”[3]他的音乐精神是与世界的发展,抑或说俄罗斯的发展相联系的,即所谓的“世界乐章”、“世界音乐”。这一点他在与《十二个》同年稍前发表的《知识分子与革命》一文中有众多的论述,如“这就是革命潮流发出的声音,这正是所有有耳朵的人都应该听的音乐。”[2]并且还在文章的结尾发出“……用整个身躯、全部心灵、完整的意识去倾听革命吧”[2]这样的呼吁。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堪称诗人顶峰之作的《十二个》的诞生是来自于这革命的“宏达乐章”的回响,正是十月革命伟大乐章的奏响,才激起了诗人强烈的创作欲望。
因此,长诗《十二个》本身不仅继承了俄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内在的“音乐精神”,而且在形式上试图反映出一种交响乐式的结构,可以说是二者紧密结合的结果。这种结合用以反映俄国十月革命前的社会状态和情绪十分贴切。
【参考文献】
[1]袁可嘉.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选(第一册上)[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133.
[2]勃洛克.知识分子与革命[M].林精华、黄忠廉译.上海:东方出版社,2000.162,170,171.
[3]王彦秋.尼采的酒神艺术与俄国的象征主义[J].俄罗斯文艺,2000.S1.
[4]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北京:北京商务社,1982.177.
[5]尼采.悲剧的诞生[M].周国平译.北京:三联书店,1986.24.
[6]王彦秋.俄国象征主义“音乐精神”的历史传承[J].俄罗斯文化评论,2006.
[7]图尔科夫.勃洛克传[M].郑体武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6.241.
[8]康澄.对二十世纪前叶俄国文学中基督形象的解析[J].外国文学研究,2000,(4).
(作者简介:郭明军,西安石油大学人文学院助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