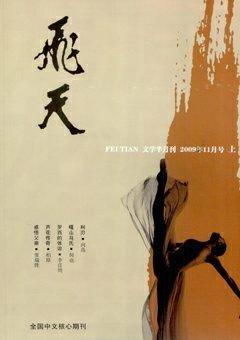土地的坚守者
当今社会的发展事实已经证明历史的发展与进步必然以牺牲某些道德为代价,而且经济的绝对发展与道德文明的相对发展是失衡的。于是,在这历史进步与道德文明发展的失衡中,有人倾向了经济发展的立场,有人走向了对道德文明的坚守。有论者认为:艺术家或具有艺术气质的思想家确信是历史的前进导致道德的退化,美德的丧失。[1]因而于这一类的艺术家或思想家来说,对于文明的坚守比角逐于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的享乐更有实际意义和终极价值。张炜便是走在这一队伍当中的作家。他在《周末对话》中说:“假使真有不少作家在一直向前看,在不断地为新生事物叫好,那么就留下我来寻找我们前进道路上疏漏和遗落的东西吧,这同样重要。”[2]
建构于农耕文明基础之上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难以割断的历史承续性和强烈的感召力,“土地”成为这种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播者。《吕氏春秋》中的《上农》篇[3]是对这种文明最为经典性的概括。生活在科技和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的张炜却仍然对土地充满着浓浓的眷恋之情,始终不能把自己与土地剥离开,不能忘记和放弃对土地的关注和思考。其小说构造的背景大多都来自于他的本土故乡:胶东半岛的西北部平原、芦青河畔的土地。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二十年的张炜,把所有对生命的体验和对土地的感悟都融进了小说。从早期的《芦青河告诉我》《浪漫的秋夜》到《童眸》《美妙雨夜》,再到《秋天的思索》《秋天的愤怒》《古船》以及《家族》《柏慧》无不是对土地的念叨和咀嚼,而备受瞩目的《九月寓言》则直接喷发出土地的芬芳气息和盎然生机,也更昭示出张炜对于土地的坚守。
《九月寓言》是一个人类与土地的故事。正如海德格尔把地球还原成大地母亲一样,小村与土地也正是一种充满着温情的母子关系。这种关系首先体现在“地瓜”上。地瓜给小村提供了根本的食物。在九月,地瓜是野地上普遍的能量之源。它养活的不只是小村里的人,还有成群的流浪人,它像乳汁一样将土地母亲与人联系在一起。费尔巴哈说过,人就是他所吃的东西。这位彻底的智者,正说中了张炜在内心不断鼓动的声音。于是他用村里老婆婆的话告诉人们:“人哪,还不就是瓜干化成的力气,化成的血肉心汁,化成的烦人毛病,不吃瓜干庄稼人就绝了根了!”没有土地,没有了地瓜,就没有了这个生气勃勃、多姿多彩的小村。所以对于小村,土地就是小村所有生命的母亲。这位伟大的母亲,不但给予了小村人得以维持生命的食物,还产出“白毛毛花”,可以直接采做棉衣棉被,让小村人不仅有了遮羞之布,还免去寒冻之苦。上帝造人的时候,既造了亚当和夏娃,也创造了其他有灵性的生命,他们既是人类的兄弟又是人类的朋友。所以在张炜的《九月寓言》里展现出一幅美好和谐的生态图画,土地里的野物与人类灵性相通,他们相互安慰,相互鼓励,俨然就是亲密的一家人。这就是生命的常态,这就是生命的和谐,然而这一切均来自于大地母亲。
土地是小村承载的基础,是小村人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他们不但认为自己靠土地而生,而且认为自己就是土,就应当做土人。这是小村人精神和信念的支柱。在任何情况下,背叛土地意味着背叛人类,最终不会有好下场的。当小村的女人们禁不住矿区洗澡池的诱惑,结队去那里洗澡,将身上的陈年污垢洗下来,变得又白又嫩时,却遭到了村里舆论的嘲讽与蔑视,以致“所有过去洗过澡的女人都无脸见人,一连数月像老鼠一样只在夜间活动”。因为被小村人视为生命的土被剥落,也就意味着她们的堕落,意味着背叛。文明的车轮是难以阻挡的,女人们不能放弃洗澡,也就意味着不能放弃背叛。但是背叛的人最终她们接受了应有的惩罚。惩罚不仅来自于小村人本身,还来自于文明的本身。小豆被看澡堂的小驴强奸事件,就是最好的例证。这一切都在昭示着:土地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旦侵犯或背叛便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张炜对于土地的反复咀嚼与赞叹,使他的生存经验与更广阔的文化基础(土地)相融合,并由此获得了一个艺术与存在同构的内在形式:万物由土地而孕育,最终又回归于土地。土地既是万物生存的根基,为万物提供保障,同时又是万物的终结地,因而“走出与回归”成为张炜小说的母题。《九月寓言》始终在这个母题中徘徊与循环。在《九月寓言》中那被称为“蜓鲅”的小村人,因为逃荒而走出土地,却又被小村接纳,表明返回土地成为事实,于是完成了出与回的第一次循环;小村被矿区所毁,进行了第二次迁徙,肥与挺芳的返回,是对土地的潜在的返回,由此完成了第二次循环。这两次循环不是毫无意义的循环,也不是普通意义的循环,而是一次次失去家园、寻找家园、返回家园的循环。肥与挺芳的最终返回,在表面上是一种单独行为,但却暗示了张炜的一个观念:人类难以超越割舍土地家园的宿命。这样的宿命感在张炜的小说中不断地重复再现,如《柏慧》。《柏慧》共分为三章,在三章连续的情节中,张炜依然依照了循环的逻辑:从最初童年在土地上的生长,到青年时因外地求学而告别土地,成年后再从繁华、喧闹的城市里返回到登州海角的葡萄园中,这同样是一个以土地为根基的循环运动。如果说《九月寓言》还是一次次割裂、表层的循环运动,《柏慧》便是整个生命的潜在运动,它的目标只有一个——返回土地。主人公无论走出多远,都是为返回打根基,为返回做铺垫。因为在张炜看来,无论是奔跑还是停留,无论是逃离还是返回,都是发生在土地上,并且最终都是为了土地。“因为土地是具体的,它就在每个人的脚下。”[4]没有了土地,一切的存在便是虚无的,不踏实的,所以人类只有回归土地,生命才是真实的。
土地就是这样的纯洁与朴素,不但使生人恋土,死人也不愿遽然离去。像老转儿这样一些先人的灵魂就始终在这片土地上游荡,共享着土地的欢乐与苦难。人事再反复,也掩盖不住土地的眼睛,再喧闹也掩不住土地的声音。尽管贫与罪依然在九月的土地上漂泊,人类只要有土地,终究有安慰和欢欣。在张炜看来,只有返回土地才是真实的。文明的修饰使一切都变得虚假和残酷,在虚假的背后,隐藏着膨胀的罪恶和欲望。诗人海子在他的长诗《土地》中,表达了类似的土地精神:由于丧失了土地,我们这些飘荡无依的灵魂必须寻找一种代替品,那就是欲望,肤浅的欲望。当大地恢宏的生命力只能用欲望来代替和指称时,可见我们丧失了多少东西。
张炜不但在小说中把对土地的感情倾吐得淋漓尽致,在现实生活中也始终把自己与土地的距离拉近。在《关于<九月寓言>答记者问》中,他强调:“我想把我所处的那个小房子的地气找准,这样就会做得很完整。”[5]一般来说这只是一个写作环境的意指,其实质却是对人生根基的一种朴素的表达。因为“人本身是不自足的、不完整的,是土地的生物,也只有挨近热土、融入野地才能直接与根源联系,才能生存得完整”。[5]所以张炜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本性是一棵树,“在泥土上萌生,他的一切都来自这里,这里是他一生探究不尽的一个源路。人实际上不过是一棵会移动的树。他的激动、欲望都是这片泥土给予的……”(《柏慧》)
张炜对土地的感情显然表明,他对传统的农业文明有着脉脉的温情,有着难以割舍的依恋。他不断地阐述着土地的根性、母性,这给暴掠大地、自私自利、欲望成性的社会一种警示,一种善意的补正。然而,“土地本身净化自己,保卫自己,平衡自己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今像一个年迈的母亲,不但不能放心去依靠,而且要悉心照料了”[6],我们还有理由和颜面再去依靠大地母亲吗?
我们究竟该怎么诗意地对待我们的母亲,这不是张炜的问题,这是我们全人类所共同面对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陶东风.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12.
[2]张炜.周末对话[M].问答录精选[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96.43.
[3]王范之.吕氏春秋选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4]张炜.关于《九月寓言》答记者问[M].问答录精选[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96.209.
[5]张新颖.栖居与游牧之地[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98-99.
[6]邓晓芒.灵魂之旅——九十年代文学的生存界限[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131.
(作者简介:王艳玲,山东外贸职业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