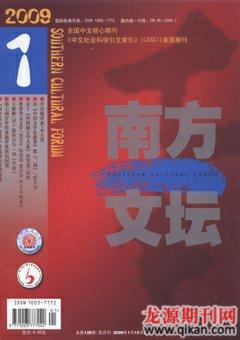为台湾当代新诗发展提供“证词”
笔者披阅过众多的台湾诗刊诗集,并数次前往宝岛考察,和各个派别的诗人座谈,让我感受到台湾诗坛的变幻多姿和波谲云诡。流派纷呈的亮点和各大诗社明争暗斗,促使我琢磨应如何描绘这座岛屿的新诗地图。然而当充满求新求变的地图描绘完毕,有三几位台北诗人大声向我说“不”。吊诡的是这样一来,倒是去古未远。君不见,自从大陆学者首次为台湾新诗写史以来,隆隆炮声一直响彻不停。“客”见我势单力薄,便在一片挞伐声中给我鼓气;“主”乘他采访之机,对批评者的意见择要作答。
谁最有资格写台湾新诗史
客:台湾新诗史的撰写,不仅是如何为作家定位和如何诠释诗歌现象,还涉及谁来定位谁来诠释,甚至谁最有资格定位、谁最有权力来诠释的问题。
主:最有资格者不一定是台湾学者或圈内诗人,最有权力者也不一定是掌握学术权力与资源的人。
客:你的话尽管有一点狂,但我还是认为你是有资格和权力书写台湾新诗史的。你2008年由台北文津出版社出版的新著能引发不少人的钦羡、不安、不满或焦虑,说明你的书有一定的讨论价值。对《台湾当代新诗史》不论是赞扬还是贬低,是爱不释手还是骂不绝口,均无法否定你在两岸诗学交流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主:你不要忙着定调子,以免帮倒忙。
客:我说的是事实。你以别人难以企及的对台湾新诗关注的热情,与台湾诗坛保持着既紧密又疏离的关系,以及站在局外人的鸟瞰观点来评说台湾诗坛,一直评到“中国坐标”与“台湾坐标”的对峙。这样的诗史可以一直写下去,只要你耐心跟踪,文章总做不完,这比起北京古继堂的《台湾新诗发展史》、台北张双英的《二十世纪台湾新诗史》内容自然更为丰富,信息量更大,由此更具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
主:《台湾当代新诗史》仍属“初写”、“试写”而非“重写”,它不具经典形态,也谈不上什么“纯粹性”。你这三个“更”,系溢美之词。
客:不要追求什么“纯粹性”和“纯诗”。你诱人的地方,是诗史中系着台湾政治风云与文化动态。事实上,你引起人们评说与关注的并不仅仅是对诗人的定位和文本的评价。如第二章《戒严寒流,诗花颤抖》,在新诗史书写中加入文化政治,做到“诗”与“史”互证,有助于唤起历史的遗忘。其中写林海音卷入“匪谍案”那一节,可视为“有文学故事的诗歌史”。至于《余光中向历史自首?》、《两岸新诗关系解读》所体现的文学史的政治性与政治性的文学史关系,是一个差不多被人遗忘但肯定是有价值的话题。你选择了相当前卫的诗坛“蓝”“绿”问题作终结,终结你描画的台湾新诗近六十年的历史图像。这个终结意味着新一轮论战的开始,很有看点。
主:关于文学史中“系着台湾政治风云与文化动态”,更适用于我刚杀青的《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这是一部富有挑战精神的文学史。
客:作为奉行“私家治史”准则的当代文学史家,能否回顾你单枪匹马写作这“六史”——《中国大陆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香港当代文学批评史》、《台湾当代新诗史》、《香港当代新诗史》、《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的某些遭遇,其中包括和自己的研究对象余秋雨在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簿公堂,和这次对你新著的“炮轰”。
主:还是长话短说吧。这回写台湾新诗史挨“骂”,是意料中的事。古继堂的书出版二十年,差不多被人骂了二十年。正如一位台湾作家所说:“古继堂的《台湾新诗发展史》早已引发审美疲劳,怎么又来了一个姓古的,你烦不烦呀,你这两股(古)暗流!”故我有自知之明,在书末写道:这是一部不能带来财富,却能带来骂名的文学史。这是一部充满争议的新诗史,同时又是一部富有挑战精神的文学史——挑战主义频繁的文坛,挑战结党营私的诗坛,挑战总是把文学史诠释权拱手让给大陆的学界。
客:写文学史必须有智者的慧眼、仁者的胸怀和勇者的胆魄。在胆魄方面,你将新诗史的下限定为著作出版前的2007年,这确是你的过人之处。
主:拙著与同类书不同之处,正在于突出当代性尤其是当下性,为台湾新诗发展作证,或曰提供“证词”,证明某些诗人试图让文学独立于政治之外,是一种迷思或迷失;尤其是新世纪的诗坛,一些台湾民族主义者扬弃20世纪80年代早期或以前的中华民族情感,不再承认自己是中国诗人,并在诗作和诗论中重写自己的国族认同、文学认同,这种现象就很值得记载和评价。当然,50年代以来台湾诗坛到底出现过什么著名诗人、诗评家和有影响的作品,诗坛发生过什么重大事件和论争,而著者又是如何“隔岸观火”评价他们的,更是我的“证词”主要内容。
客:与其用法律名词解释你的诗史,不如说你在“结语”中使用了政治学和社会学叙事理论诠释台湾诗坛的统独问题,这使人佩服你“抽刀断水”的勇敢精神,但你又必须面对“水更流”的尴尬局面。这就是为什么你的著作一再引发争论,以至有人认为你是靠别人的批判或批判余秋雨成名的学者……
主:请注意,是余秋雨告我这个“文革文学”研究者上法庭,而不是我告他。余说我靠批判他成名,这是他拒绝批评的一种借口。余秋雨不敢跟我正面交锋,总是质疑批评者的动机或为了出名或为了赚钱,这就像泰森不用拳头而用牙齿出击,无论是胜还是败都不光彩。对此,我已在《庭外“审判”余秋雨》一书中作了说明。至于我和台湾诗坛的几次论争,也是别人先挑起的。我从来都是靠自己的研究成果说话而不是靠论战乃至混战成名。
客:写小说史、散文史不会碰到许多麻烦,唯独写新诗史引来的议论最多,这与诗坛圈子太多摆不平有关,这就难怪覃子豪研究专家刘正伟在2008年7月《乾坤》上发表《评古远清〈台湾当代新诗史〉》时称,目前台北有三篇批评《台湾当代新诗史》的文章,均“贬多于褒”。
主:这有点意思,也有点值得本人喝一壶了。但请不要一锅煮,像杨宗翰与我的对话发表在2008年5月出版的《创世纪》,他比较客观冷静,认为“殊途不必同归”,并未采取一棍子打死的粗暴做法,与同刊在2008年5月号《葡萄园》上的谢辉煌《诗人·诗事·诗史——古远清〈台湾当代新诗史〉读后》、落蒂《介入与抽离——评古远清著〈台湾当代新诗史〉》两文不同。
新诗史书写中的吊诡现象
客:刘还说你发在2008年5月《葡萄园》的两篇回应《落蒂对台湾诗坛熟悉的程度不如大陆学者》、《小评谢辉煌对拙著的“反攻”》有“避重就轻”之嫌。
主:这个批评有一定道理。有些重大问题我回避了,结果受到台湾一位老诗人的批评,他在给我的信中说:“我觉得像谢辉煌引用游唤的说法,反对大陆学者将台湾文学视为当代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这倒是应该提出反驳的。不应该‘不展开讨论。海峡两岸当然都是中国的一部分,文学都属当代中国,为什么在大事大非面前不表明立场,做老好人不讨论、不辩驳?”不过,游唤不主张“台独”,而主张“独台”。如果对此问题真要展开辩论,那就要开辟另一战场。如要逐条作答,那就太浪费篇幅了。像落蒂批评我评价“关(杰明)唐(文标)事件”时加入了自己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天哪!我刹那间噎住了,半天也打不出一个嗝儿来。只要细心读拙文,就不难发现这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系我对关、唐两人“左”倾观点的概括,他怎么可以唐冠古戴?又如我把纪弦《你的名字》当成优秀诗作分析,落蒂说“令人读后颇怀疑古氏对诗的评鉴、欣赏能力”,这也不用作答,因为各人评价标准不同嘛。这里不妨再补充一例:我把余光中的《乡愁》全文引录并详析,有一位台湾诗人却认为《乡愁》“只是儿歌一类”,比他写的同类诗的艺术成就“相差何止百倍!”
客:你的《台湾当代新诗史》写得率直而刚健,具有“血性批评”的风格,可落蒂不这样看,他认为你鉴赏水平低,这到底应如何看?
主:那就听听一位资深台湾诗人在2008年5月28日给我信中说的一段话吧:“落蒂那文我也看了,水准不高。他还认为纪弦《你的名字》是普通中更普通之作。其实,纪弦这首诗是相当不错的,是爱情诗中的佳构,落蒂的欣赏力甚低矣。”再说落蒂批评我把杨渡的《一九八三年暮歌》放在解严时期论述不妥,可他自己也认为这首诗写于1983年当时未解严。他如此前言不对后语,还用得着我接招吗?再如谢辉煌对我引用陈千武所说日据时代“无诗”有不同看法,便罗列出一系列的诗人和诗事,以证明陈千武说法的荒谬。如此坐实理解“无诗”,未免过于皮相。
客:你是不是说在文学史如何书写的讨论中,出现吊诡情况:参与者在纠别人错的同时,又成为被批评者纠错的对象?
主:是的。先说谢辉煌给我纠错时,说高准在1989年北京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中,“亲往现场声援侯德健”,其实,高准当时在台湾,并未“亲往现场”。他是在“天安门事件”后约两个月才到大陆去为侯德健说项的。这在《高准诗全编》第155页说得很清楚。再说落蒂,他给我纠错时说“《乾坤》创办于1987年,却误为1957年”,可他自己在《青溪论坛》2008年第3期发表的《如何写一本较完整的台湾新诗史》,承认自己也搞错了,应为“1997年1月才对”。可见,谁都不能保证自己不出错,我回应时也受了他的误导。
客:落蒂讽刺你没有雅量接受批评,认为自己的《台湾当代新诗史》是“最完美的著作”。可见,你不能过于自信,总认为自己的书已到了无懈可击的地步了吧?
主:我从未认为自己的著作是“最完美的”。以诗人归属而论,确有改进之处,有些重要的诗人的确遗漏了。再以编校而论,除刘正伟帮我纠正了一些诸如“林美山”误为“美林山”、“新诗周刊社”误为“新闻周刊社”、《一九四九以后》误为《一九四九之后》的地名、单位名、书名一类错误外,高准也帮我发现了一些,如48页把彭歌与彭品光误为同一人了。相信这类错误还会有。校对就像扫地,扫得再干净也会残留尘灰。
所谓“杂乱‘芜章”、“‘编排失当”
客:一位喜欢读台湾新诗史著作的友人遗憾于大陆只出一个古继堂,他瞪大眼睛希望大陆再出一个为台湾新诗写史的人。“古”家果然后继有人,你不负众望来了,可你来得太匆忙,难怪刘正伟说你的诗史“杂乱‘芜章”啊。
主:我为了不重复古继堂,想把创作史、论争史、诗论史、诗刊出版史等均写进去,的确不好安排,难怪给人杂乱之感。至于刘正伟说我把《笠》等诗刊诗人“济济之士”挤在一节,而创世纪等诗社人皆一节,其取舍标准何在?答曰:笠以“集团”彰显,而不以个人成就著称使然。这种话圈内人似乎不便说,我这个被笠视为“外国人”的旁观者说说也就无所谓了。龙族等诗社也是诗社意义大于个人成就。不过,即使这样,我还是尽可能给每位诗人充足的篇幅。当然,确有比例失调之处,值得检讨。
客:一些文学史家,常常用强势文学团体的文学史观来否定弱势诗人的存在。你没有这样做,而是写出了外省与本省诗人之间的恩怨与纠缠、强势与弱势诗人之间的压迫与共谋,这是可贵的,但你的书毕竟如刘正伟说的“‘编排失当”啊。
主:他说我“‘下编几乎不见‘上编出现的诗人与诗社安排,是否创世纪、蓝星、笠、葡萄园等诗社与其诗人只出现在上世纪的‘上编,在‘下编的1980—2006年间,从此消声匿迹,不再活动?”这是刘兄看走了眼。在第118、119、147、180、202页均论述到《蓝星》、《创世纪》、《笠》、《葡萄园》的后期以至当下的活动。如果把这80年代以后的活动再放到“下编”,岂不犯了他自己说的把诗人或诗社割裂过多的毛病?刘兄偏爱《蓝星》诗,肯定拙著有“洞见”的同时有“不见”,即嫌我写了六节蓝星诗人不过瘾,还要我把夏菁、邓禹平、吴望尧、黄用统统写进去,无一例外用专节处理他也许才能满意。如此一来,《蓝星》诗人浩浩荡荡进军“诗史”,岂不成了他说的“百货公司”了?他又要我把中国新诗、海鸥、南北笛等诗社一一写上,其实拙著第16、261、107页等处已有提及,只不过写得过于简略。如要巨细无遗写出,那又成了刘兄自己说的“老杂货店”啦。
客:你说自己是站在局外人的立场书写台湾诗史,书写时是客观的,态度也是超然的。其实,正如单德兴所说“任何文学史都注定是选择性的、不完整的、有偏见的”。比如刘正伟和文晓村等人认为你没把向明放在蓝星诗社论述,便体现了你的“偏见”。
主:在开始时我也是把向明放在蓝星论述的。2007年我在珠海当面征求向明的意见,他坚持要将自己放在《台湾诗学季刊》。我后来一想也有道理。“向晚愈明”的他,对台湾诗坛真正形成影响是在不再主编《蓝星》诗刊以后。为此,445页我专门作了说明。
台湾诗坛与香港诗坛的“亲戚关系”
客:你这个“‘刽(快)子手”,听说又将在香港出版《香港当代新诗史》了。
主:笔者告别杏坛后,在赋闲中居然让《台湾当代新诗史》“下蛋”,生“第二胎”《香港当代新诗史》,我为自己没有辜负二十多次访港取得的资料感到庆幸。
客:这么说来,你的《香港当代新诗史》是“拣”来的?
主:不是我故作谦虚,《香港当代新诗史》对我来说确是“拣”的,“拣”了个金元宝。毕竟写完了《台湾当代新诗史》,写《香港当代新诗史》就顺理成章,下笔也顺畅多了。说“拣”或说下笔“顺畅”,决不是说香港新诗史容易写或暗含藐视香港诗人的意思在内。相反,香港新诗界有不少璀璨的名字,他们的光环逼使我总是睁大眼睛去审视他们。我既庆幸自己和这些相识或不相识的诗人心灵是如此贴近,但我又担心自己的拙笔不能将他们的文学成就一一道出。应说明的是,《香港当代新诗史》并不是《台湾当代新诗史》的附庸或骥尾,两者有各自的独立性,但台港新诗确有“亲戚”关系。
客:能否进一步说明台湾诗坛与香港诗坛的“亲戚关系”?
主:这是个复杂问题,我只能笼统回答:台湾、香港本来就有被“割让”的相似历史遭遇。在地理位置上,两地均属大陆的离岛。在意识形态方面,两地均不存在什么“社会主义主旋律”。他们的新诗比起内地新诗来,有太多的同质性。何况作为跨文化城市的香港,那里有不同背景的文化经验共存和交汇,比如在台湾诗坛颇为活跃的叶维廉、余光中等人,便是香港诗坛的要角。台湾诗人也参加香港诗坛的论争,如落蒂对香港大学黎活仁形式主义点评台湾诗刊的精彩批评,我已写到书里去了。关于这一些,均见《香港当代新诗史》第二章第六节。
客:你先后写作了六种当代文学分类史,这在两岸均是鲜见的,因而有人称之为“古远清现象”。不过,你不能萝卜求快不洗泥,应多花时间去修改、润色、打磨,否则就会像谢诗人说你的《台湾当代新诗史》送到废品收购站还不到一公斤哩。
主:谢诗人之所以有这种与“恶评”相差不远的“酷评”,并不像有人说的拙著没有写他而引起其不满,而是他以国民党老兵身份说我站在中共立场上否定“反共文学”。这“反共文学”尽是“乒乓劈啪哒哒轰隆隆地打回来”以及“像毛匪江妖那一小撮的逆竖,真是何其不自量力啊”(纪弦)一类的标语口号加诅咒,与左派写的“打倒蒋匪帮,解放全中国”的呼喊具有同质性,难道有什么艺术价值可言?
还未能找到让我折服的“论敌”
客:台湾对大陆学者写的台湾文学史,一直认为是统战的产物,多采取拒排的态度。谢辉煌的“酷评”是否体现了这一点?
主:大陆学者写的台湾文学史及分类史,不能说完全没有政治因素,但并非每本书的作者均肩负着“统战”的重任。像拙著《台湾当代新诗史》,完全是从个人兴趣出发编撰的,并无接受官方的任何资助。至于否定反共文学,不仅有大陆学者,也有本土评论家叶石涛,你总不能说叶石涛也在搞统战吧?
客:台湾学界在台湾文学史编写问题上,几乎交了白卷,而大陆学者却出版了众多的台湾文学史及其文体史。面对这种情况,具有小岛心态的学者发出了“抗拒中国霸权论述”的怒吼。
主:你要小心使用“小岛心态”这个词。像批评我的几位台北诗人,并没有这种心态,而是想帮我把诗史修改得更完美。但谢辉煌扬言要“反攻”,却蕴涵有两岸争夺台湾文学诠释权的意味,可惜他未展开论述。
客:在两岸三地,你早已不止一次成为某些人的火药目标。
主:不论在台港文坛还是上海法庭,我均领教过某些人对我的攻讦。所谓“卖废品”云云,自然不会泯灭我研究台港新诗的兴趣。不过,陈克华一类的台湾诗人不喜欢论争,他用不加置评的方式表示对拙著不屑一顾。更多的是餐桌上的耳语,这些我不一定都能听到,但只要有价值的我就会反思和检讨自己。
客:除落蒂你未谋面外,谢辉煌、刘正伟都是你访台时拜见过的诗友,你能否和他们作进一步比如私下的沟通,以避免不必要的误会?
主:没有这个必要,因我跟他们均没有恩怨和过节。像谢辉煌,我赏析过他的诗。刘正伟则是“不打不成交”的挚友。他们的文章均就事论事,没有人身攻击的地方。只要不像余秋雨那样因学术论争将我告上法庭,随他们说什么都行。对落蒂、谢辉煌、刘正伟三位先生一再为文指教,我心存感激。有不同意见,如刘兄说“引火烧身”系“引火自焚”之意,这是他的发挥,并不符合我的原意,属他的“再创造”。像这类情况,还是为文切磋、讨论吧。
客:有无使你佩服的对《台湾当代新诗史》的批评?
主:坦率地说,我目前还未找到一位能和我一边争论,一边让我欣赏“论敌”智慧的对手哩。■
(古远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