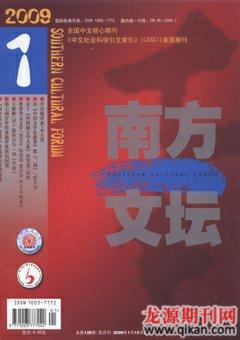写作十年
肉体使我们寡廉鲜耻。
——卢梭《爱弥儿》
尽管“80后”的写作偶像在出版领域的光芒已经让人炫目却仍以“孩子”自居,尽管文学史上有许多作家像曹禺一样在20岁出头已经发表了自己的代表作品,尽管对于文学变革和文学规律而言,年龄不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但是,作为一个出生于70年代的职业读者,我仍然觉得十年的经验对于常规写作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当喷发式的初恋般的写作热情消逝,当完全感性的个人性的写作资源业已殆尽,瞬息多变的日常生活如何转换为叙事想象,如何让写作激情汩汩流淌就变成了一个艰难而重大的课题。
生活是一切文艺之根。然而生活并不是端坐殿堂的神圣让大家朝贡的,也不是凝固的晶体供大家“体验”的,比如余华曾说:“我觉得生活实际上是不真实的,生活是一种真假参半、鱼目混珠的事物。”生活无法按比例切割,生活本身既是过程也是目的。生活就像车站,沉默地敞开它宽厚的怀抱迎来送往,每位写作者可从中获得不同的滋养。
2007:写作十年与精神成长
2007年在文学史上并不特别,即使有全国鲁迅文学奖第四届评奖也不过激起些许涟漪,作家富豪排行榜、各种年会、例会、研讨会的召开虽然能够赢得媒体的秋波,并不能打乱文学的流淌。文学的亮点始终闪烁于新文本的诞生。然而对于“70后”而言,2007年可能具有某种标志意味。路内的长篇《少年巴比伦》可以看成这种标志性的文本,整个文本是“70后”的路小路对着“80后”的女诗人张小尹的讲述。对整个文本而言,张小尹是个缺席的在场,“香甜而腐烂”的青春是路小路的,路小路的90年代和戴城都与她无关,即便她日后成了路小路的老婆也不能改变这个事实,她只可倾听却不能活在路小路的记忆和叙述中,她无法取代知识分子白蓝(厂医)在路小路灵魂和身体中的位置,路小路依恋白蓝甚至愿意为她去拍砖尽管他无法把握她的情感困惑,尽管他们那段恋爱没有希望没有结局却仍让他无比怀念。如果我们将这个文本看成一种象征,那么路小路和白蓝及张小尹的关系就可以看成“70后”与前一代和下一代的精神写照。
叛逆与性爱启蒙从来是成长小说的基本要素,白蓝不仅给了性压抑的青年路小路以身体的出路,也给了他“姐姐”般的人生引导并率先以考研的方式离开戴城离开那种沉闷枯燥和暴力的生活,她给了路小路走出毫无希望的工厂生活的勇气。时光随着记忆自由地在今昔之间穿梭,1993到1994年的戴城那灰蒙蒙的凝滞的空气因为路小路的讲述而独具光彩。自《麦田里的守望者》发表以后,成长小说就有了难以驱除的阴影,而成长小说又几乎是每代小说家粉墨登场的必修课。当路内的《少年巴比伦》面世,虽然我们迅速地从中感受到王小波的余味,感觉到文学的遗传之不可思议,然而,我们仍然同时感到喜悦,感到文学的希望——“每一条道路仿佛都很熟悉,地上的落叶也很熟悉,我想起她说过的,每一片枯叶都只能踩出一声咔嚓,这是夏天的风声所留下的遗响。”这是路小路在寻白蓝而不遇之后的一段感想,这不正如文学的处境吗?《少年巴比伦》就是与刚刚转身的90年代留在70年代人心灵的遗响。
从《穷亲戚、乡村与爱情》到《家道》,魏微展示了一种对世界广阔性、丰富性的理解与把握。前者有一种典型的经验性,这种瞬间而至的爱照亮了文本,也照亮了朴素的乡村伦理。而《家道》虽然采用的还是第一人称,然而我们明显地感受到虚构的长驱直入,绵长的回忆,阔大的时间跨度和空间跨度很好地融化了叙述者对叙述时代的理解和感觉。新作《李生记》算不上魏微最好的作品,作为一个过度期的作品它有效地展示了魏微对虚构的努力,从狭窄的情欲世界向广袤的生活世界进发。李生是个泛指,“自李唐来”,李就是中国的大姓,而生跟在姓后仅指性别,具体姓啥名谁已不再重要。像李生这种外来工充溢在城市的每个角落,他们不仅帮城市人搬运生活用品也帮他们运送生活垃圾,他们的工作弥合着生产和消费的各个环节,维护着都市表层的光鲜清洁,使城市人生活便捷,而他具体的姓名、他的个人处境、他的精神状态以及生活方式却是真正的城市人所不屑关注的。“李生”每天在别人的屈辱或淡漠中接过一沓小币值的钞票,用这沓钞票换取低微而辛酸的生活,却仍然在钞票慢慢变厚时自发地积攒起生活的希望,然而希望是那样微薄那样易碎,以至于经不起任何一点风霜。小小的变故都有可能摧毁外来工家庭生活的平静和全部的希望,甚至摧毁肉身。偶然悄悄地遮盖着必然,个体生命的消失与否都不再是悲剧,叹息也轻微地消散在空中不留痕迹,一切都轻飘飘的,只有文学叙事在无声且节制地为之挽歌。城市是现代性叙事的必然选择,魏微将视点集中在李生这样一个奔走在城市的小人物的命运上,这样不仅使叙事获得了现代感,也与中国转型期的现实互相呼应。《穷亲戚、乡村与爱情》等文本所流露的女性性别意识在《李生记》中也巧妙地隐藏了,如果前者是魏微对乡村的诗意审视,那么后者则是作家对乡下人的现实关注。
李师江的长篇小说《福寿春》显示了作家在写作十年之际如何从都市重返家园。在文学中,家园始终是一个难解的魅惑,故乡总是在游子的心间盘桓并在文学史上代代相传。李师江所叙述的故乡是急剧变化时代的故乡,是遭到现代性压抑的故乡。田园牧歌式的故乡已经退隐。现实的故乡只能以其缓慢的脚步应对着时代匆忙的步履。一边是晃动的目不暇接的社会世相,一边是亘古未变的乡村旧俗,父辈和子辈之间的隔膜犹如万丈沟壑,他们再也无法泅渡到对岸去探测对方的欲望。人心不古的安春、游手好闲的浪子三春、爱土如命的父亲、溺爱孩子完全没有原则的母亲交织成当下乡土生活的变奏曲。欲望在膨胀,生活方式在剧变,时代的风雨正在无情地侵袭着延续千年的亲情和古朴的伦理。
鲁敏的《颠倒的时光》通过大棚西瓜对时节的改变叙述出现代社会农民的情感不适。传统的乡村生活本来是没有历史感的,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的生活循环往复,时间观念也是模糊的而不是精确的。自工业革命以来,这种通过高科技来强行改变自然秩序改变事物本来模样的做法已经越来越深地介入现代生活,从都市到乡村,田园情调不复悠扬。这种改变既是我们求快的结果,同时又变成对快的追求的目的。时代的车轮就在这种循环中加速度旋转,这种加速度的现代生活导致了我们从身体到心灵的疲惫,导致了真正意义的审美疲劳。大棚西瓜可以改变时节,可是并不能改变我们对自然对事物本来面目的神往和虔敬。鲁敏的叙事哀悼了一种诗意生活的彻底丧失,这种丧失不仅是对乡村的剥夺,也是对都市的剥夺,是现代人必须面对的基本困境。
当许多女性作家仍将视点停留在带刺的玫瑰上时,部分70年代出生的男作家已开始勇敢地关注那些无名的野花,并给予它们在春天应有的位置。田耳的《一个人张灯结彩》和徐则臣的《跑步穿过中关村》不约而同地将笔触伸向社会底层,在体面的、道德的阴影下面蛰伏着的灰色群体,他们的生活中到处布满红灯,他们试图抢在黄灯区间快速冲过警线,但是,在关键时刻,爱却比红灯更快地照亮他们粗粝的心。就已发表的并不太多的作品显示出田耳对刑事案件的外壳很痴迷,他对侦破技术所需运用的高科技很关注,他的叙事能有效地深入到技术深处的蛛丝马迹中。电脑不只是他的写作工具,也是他的叙事道具,同时他能很好地把人脑中的情感和电脑的功能缝合起来,比如小说中分明是为了让一个哑巴帮助拼图专家回忆出嫌疑人的长相,却能够很好地发掘相片对于思念者所具有的安抚功能。田耳在还年轻的时候就愿意将小说的女主角设置为哑巴,这是让人吃惊并钦佩的,同时这也反映出作者对于言辞的高度警惕,比起言语,行动更接近心灵的真实图景。直面残缺的生活及其内心的深渊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更敏锐的感受。聋哑人于心慧善良、心灵手巧甚至逆来顺受,然而,她的男人仍然抛弃了她。可是,她连祥林嫂那样抱怨的武器也没有,她丧失了语言这种最基本的权力,手语也不曾真正掌握,就是尖叫也是沉闷的、混沌的,无法生效的。残疾使小于不可能拥有正常人的日常生活。无声的静寂、可怕的孤单压迫着年轻的小于,催逼着她去依靠男人。爱着她的钢渣为了给她弄点钱去敲诈,杀死的的士司机却是她的哥哥于心亮。眼泪成了小于唯一的武器,等待成了小于唯一的命运。她一个人张灯结彩等着钢渣来践约,而钢渣却已因命案被抓进去了,他交代落魄的警察老黄替自己去赴约。背负着死者于心亮和即将伏法的钢渣的双重托付,沧桑的老黄艰难地走在赴约途中,远远看到小于精心挂起的满屋灯笼,内心充满了犹豫,脚步也变得迟疑。自古以来,杀人偿命,然而,由于钢渣单纯的作案动机,我们内心的天平也从法理向情理倾斜,我们理解并同情钢渣这样的卑贱者。小说并没有停留在这起刑事案件上,而是通过警察的角色掀开生活的黑色帷幕,魑魅魍魉粉墨登场。比起钢渣、皮绊这些赤裸裸的犯罪分子来说,更可怕的是像刘副局长这样道貌岸然的掌权者,依仗特权腐败,内心糜烂成一摊欲望的烂泥,除了欲望就再也找不到人伦人性。
田耳的《环线车》的叙事链是圈套式的,像洋葱一样一层又一层,大的跟踪案下面是小的敲诈案,然而,当这些故事像外衣一样层层褪去,最终敞亮的却是富人苍白的身体和贫乏的精神,肉欲的泛滥与之构成凄厉的对比。数码相机、银行卡、网络视频等诸多新生事物拥入文本,时代气息拂面而来。
徐则臣的《跑步穿过中关村》这个题目颇有意味,我们知道中关村就是北京的“硅谷”,是现代文明最新成果的集散地,那里充斥着高科技,当然也必然地包含着其私生子——盗版;而跑步却完全是个前现代的行为方式,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象征。在两次进监狱的空隙时间里,卖盗版碟的敦煌始终在跑,为生存而奔跑,为不被警察抓获而逃跑。口袋里的那点薄薄的钞票让他几乎无暇喘息,他只能像《罗拉快跑》一样一直在跑着。因为同是天涯沦落人,他和夏小容轻易地发生了肉体关系并同居,后来又和进去了的同伙的女朋友七宝发生肉体关系。社会地位的卑微加上囊中羞涩,使这个正当年的小伙子不能有正常的爱情生活,更不能做成家立业的打算。漂泊动荡使得他们在一起几乎不抒情,他们苦涩的爱被表达在行动中,比如敦煌对夏小容男友矿山不问由来的一阵揪打和灌酒,比如最后为了挽救矿山却勇敢地承认那箱色情盗版碟是自己的。小说在悲伤中结尾,当敦煌的双手被拷住的时候,他亲眼目睹了夏小容的流产,同时亲耳所闻的是七宝怀孕的消息。生活在手铐的“喀嚓”声中中断,奔跑和希望随之结束。小说形象地展现出“京漂族”要在首都北京立足何其艰难,夏小容成个家当个妈妈的“小农意识”何其难以实现。当前现代碰上了后现代,大城市那片尴尬的丛林中哪里还留有跑步穿越的小径?《跑步穿过中关村》展现了光滑的都市生活底色的残忍,而新作《伞兵与卖油郎》和《人间烟火》中弥漫着一种乌托邦气质,叙述致力于内心与现实的鸿沟,理想总在生活上空盘旋。
有如田耳喜爱科技细节,王棵则迷恋无实质性伤害的谎言的功用,比如《海面平静》最后一刻,女孩灵机一动为自己的身体编织了一个血癌的谎言,这个谎言或许可以像海水冲击沙滩一样平息要终身困在海岛的少年突如其来的初恋。另一个作品《次要战争》中受伤的女主角只想用艾滋病的谎言来惩罚那对怀疑她纯洁的母子。谎言为前者提供了抚慰,为后者提供的是心理惩罚。对谎言功用的辨析也可以视为作者写作的潜在动机,即写作所探询的真相何在?是梦的真实还是此在的真实,这种疑惑使得王棵的叙事特别细腻柔软,这种阴柔也有别于其他男性作家的写作气质。
“70后”的敞亮与遮蔽
“70后”在推出之时就呈现阴盛阳衰的局面,这也应当看成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较量的结果。伊恩·P.瓦特在《小说的兴起》一书中谈到:“闲暇证实和强化了我们已经看到的读者大众构成的图画,它也为说明其中女读者扮演的角色日益增多提供了最充分的适用的证明。因为,在许多贵族和绅士的文化水准不断地由伊丽莎白时代的廷臣退回到阿诺德所谓的‘野蛮人的同时,与之并行的另一种趋势是文学正变成一种主要的女性消遣物。”?譹?訛 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发展,女性的身份也随之分化,不仅作为文学的主要消遣者存在,也在文学创作领域与男性平分秋色。
1996年第3期《小说界》开设了“七十年代以后”的栏目,其他刊物也做了一些响应,但真正使这个概念在文坛深入人心的则推《作家》杂志的“七十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小说专号”。1998年7月,在宗仁发、施战军、李敬泽一次“密谋气氛”的谈话② 之后,《作家》杂志隆重推出“七十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小说专号”,集中推出卫慧、周洁茹、棉棉、朱文颖、金仁顺、戴来、魏微七位女作家的作品,并配发了各自的照片和著名批评家的点评以及女作家自己的创作谈。这期专号的封底特意转载了《文汇报》上的报道《一批年轻女作家崭露头角》③,这篇报道指出这些年轻女作家外貌“或清秀或亮丽”,打扮“流露出都市中现代派女性的前卫和时髦”,文风“热烈而无所顾忌”。而被置于头条地位的卫慧在自己的照片下方写道:“穿上蓝印花布旗袍,我以为就能从另类作家摇身一变为主流美女。”事实上,此后的卫慧与东方女性身体象征的旗袍发生了较深的纠缠,也因此被媒体关注有加,在《上海宝贝》的勒口采用的也是穿着旗袍的照片,旗袍这个典型的东方意象成了卫慧的符号资本。
“美女作家”的称谓也因此在文坛不胫而走,策划者李敬泽等也被媒体冠之以“美女作家”的制造者。此后,出版界趁此风气出版了一些女作家的作品,如“文学新人类丛书”和“突围丛书”;卫慧和棉棉两位“美女作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出版时机④,此后爆发了“卫慧棉棉之争”。不久,“七十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小说专号”的策划者宗仁发、施战军、李敬泽又一次发表三人谈《被遮蔽的“70年代人”》⑤,这次,他们以编辑家和评论家的专业身份对“美女作家”这个哗众取宠的称谓进行批评,他们认为这个提法是“媒体阴谋”,并强调“本来一些期刊接纳和扶持新作者并无强烈的商业考虑,但图书出版一介入进来就不一样了”。媒体对此关注有加,最终,这些专业批评和媒体炒作一并转化成了符号价值,其中,受益最大的是卫慧,她成了典型的消费符号——“70后”和“美女作家”的代表形象,当然这也是她毫无顾忌的以“美女”自诩的结果。就像作家东西感谢批评家提出“晚生代”来安顿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一样⑥,卫慧也得益于“美女作家”和自己的双向选择。
卫慧的大胆不仅表现在现实的言谈中,也表现在叙事中。《上海宝贝》的封面上印着三句广告,“一部半自传体小说、一部发生在上海秘密花园里的另类情爱小说、一部女性写给女性的身心体验小说”。这三句广告从不同的角度诱惑读者:“自传体”强调叙事的真实性,同时暗示读者可以用索引法加以解读,并暗示叙述满足隐含读者的窥私欲;“另类”则在兜售一种新奇的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女性的”强调女性的主体性,即叙述所包含的女权主义态度,我们知道,90年代中期,在林白、陈染等女性作家的叙述下,女权主义在文学场域中漫漫洇开,被越来越多的读者所认可。女性的“被看”的地位注定“一部女性写给女性的身心体验小说”依然能提供诱惑,邀请我们依照提示语按图索骥。消费者是我们共同的社会角色,我们很难拒绝消费发出的信息,我们不自觉地打开书页,接受关于“上海”这种国际化大都市想象与“宝贝”这一私密想象的亲昵接轨。
我叫倪可,朋友们都叫我CoCo(恰好活到90岁的法国名女人可可·夏奈尔CoCo·Chanel正是我心目中排名第二的偶像,第一当然是亨利·米勒喽)。每天早晨睁开眼睛,我就想能做点什么惹人注目的了不起的事,想象自己有朝一日如绚烂的烟花噼里啪啦升起在城市上空,几乎成了我的一种生活理想,一种值得活下去的理由。
这就是《上海宝贝》在引用了乔尼·米切尔的《献给莎伦的歌》作为题记之后的开篇。这是一段坦率的自我介绍,制造出“半自传”的真实性,第一人称迅速地将我们带进叙述现场。
在这短短的出场白中,叙述者引用了两个名字,这是两个不同领域的代表符号。他们均来自西方,CoCo·Chanel本身是名牌的符号,是昂贵的顶级的消费品的符号,跟发酵的物欲密切相连;而亨利·米勒是著名的性叙事大师,他的代表作标题就是《性》,这本书是20世纪40年代在巴黎出版的,而在我们一直以为非常开放的美国它一直是被禁止的。CoCo·Chanel和亨利·米勒这两个符号就像河流的两岸,规定了《上海宝贝》的叙述流向:在汹涌的物欲和性欲的挟持中滚滚向前。
“我”想“做点什么惹人注目的了不起的事,想象自己有朝一日如绚烂的烟花噼里啪啦升起在城市上空”。这种想法不仅是主人公的欲望,也是叙述的内驱力,而亨利·米勒正是叙述者在写作路途上的导师。“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书的时候我就立下志向,做一名激动人心的小说家,凶兆、阴谋、溃疡、匕首、情欲、毒药、疯狂、月光都是我精心准备的字眼儿。”⑦ 对亨利·米勒的崇拜和这些“精心准备的字眼儿”一道出示了卫慧的叙事趣味。在《性的政治》中,凯特·米利特对亨利·米勒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发现“米勒小说一个重大的虚构是,小说的主人公(他总是或多或少是作者米勒的化身)具有不可抗拒的性魅力,且性功能无比强大,令人叹为观止”⑧。在卫慧的叙述中,这种强大的不可抗拒的性魅力和无比强大的性功能被移植到女主角身上。并且,经常性地,女主角为自身这种性魅力和欲望骄傲。
性欲叙述的意义是敞亮文明的压抑。《废都》揭开了性的面影,但仍是男权的视角,女性不过是男性取得快乐的工具,“因为有史以来,绝大多数女性被局限在向男性提供性的发泄渠道和繁衍后代这一动物生活的水准上。这样,在女性的生活方式中,性只不过是不时降临到她头上的一种惩罚”⑨。卫慧则试图还原自然状态的性,将男性也作为女性获得性快乐的工具来叙述,女性不再是被动的他者,女性和男性在满足性欲的过程中互为他者,他们同时兼具主体和客体的双重身份。脱掉披在性欲之上的文化面纱之后,男性和女性在性行为上是一种契约关系⑩。男权文化的结果之一是塑造女性的从属地位,并进一步将性别差异讲述为政治差异以强化男权文化的存在事实。
《上海宝贝》一度畅销,其后被禁售,《上海宝贝》的强光遮蔽了其他“70后”文本的光华。在评奖、发表与评论共同将60年代出生的作家群推向实力派的同时,出版商对速度追求的日益加剧使“80后”迅速浮出并成为新一代的偶像。“70后”陷入发表和出版的夹缝中,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尴尬境遇使得关于“70后”的叙事趣味和美学理想也被简化对待。“70后”这个命名昙花一现,仿佛只是为了使“80后”“弑父”而存在;然而“70后”死而不僵,就像幽灵一样飘荡,遮蔽了70年代出生的写作群体叙事面貌的复杂性和精神内蕴的丰富性。
超越感性经验,超越“70后”
我国三十多年经济的持续发展使社会的各个方面发生了变化,消费主义迅速蔓延使人心欲望的变化尤其惊人。黑格尔说:“一个人走不出自己的时代,犹如走不出自己的皮肤。”波德里亚将我们所处的时代总结为“消费社会”并判断:“性欲是消费社会的‘头等大事,它从多个方面不可思议地决定着大众传播的整个意义领域。”?(11)消费社会这种特质也构成了作家们基本的叙事想象,“性欲亦偏离了其膨胀的合目的性”成为叙事的支点。
同样,一个人也走不出自己的历史,犹如走不出自己的血源。叙事很好地呈现出作家与时代和历史的深层纠葛。在我国的文学史中,张爱玲成了女作家们巨大的阴影,就是王安忆也要撇清与她的关系。张爱玲所开创的两性之间情感战争一直在叙事中被继续、发扬和拓展,她创造的经典话语总是在后继的叙事河流中复活。张爱玲告诉我们:“现代婚姻是一种保险,由女人发明的。”而法国的杜拉斯则告诉我们:“夫妻之间最真实的东西是背叛;任何一对夫妻,哪怕是最美满的夫妻,都不可能在爱情中相互激励;在通奸中,女人因害怕和偷偷摸摸而兴奋,男人则从中看到一个更能激起情欲的目标。”婚姻及其背叛,混沌的诱惑,算计的戒备等汇成女性的情欲叙事图景。
女作家大抵情感细腻,善于把握微妙暧昧的心理感受,这是女性的叙事优势。在女作家的写作之初,这种优势尤为明晰。王安忆提醒我们:“处女作是心灵世界的初创阶段,它显示出创造力的自由状态。……但我们必须正视处女作的局限,它毕竟是没有经过理性成长过程的感性果实。”(12)
从《水乳》到《道德颂》,盛可以依旧在勤恳地开掘两性情爱题材。在盛可以笔下,爱是肉感的,是欲望的最深处。但随着作者对爱的理解的深入,叙述面貌也在不断改变。《道德颂》中巧妙地利用了语言能指的歧义和谐音,使文本更加丰富更加有趣。叙述的狠劲慢慢缓和,怨恨中渗融了温和的理解。嫉妒的旨邑和三个男人的故事仍旧是一个俗套的故事,不外乎爱与欲的搏斗,感情与责任的战争,可是,盛可以在老旧的故事中注入了自己新鲜的理解,在尊重身体欲望的同时歌颂了道德和责任。故事的底牌竟是有妇之夫水荆秋有一个患尿毒症躺在床上的妻子,精神世界的理解和俗世生活的责任参与到身体的情欲中,爱便变成了沉甸甸的具象事物,爱的丰厚得到了延展。对于爱,现实是比性欲更强大的支撑。
金仁顺的短篇《桔梗谣》中两性情爱关系退为叙事的底色,视点不断聚焦于众多人物的内心,叙述者的仁慈温暖地弥散着。在对待私生儿子婚事的态度上,我们重新看到了时间掩护的真爱,也看到与时间同行的亲情。爱情如何在更广阔的叙述世界像白云一样自由地飘荡成了这批女作家的共同思考。她的《云雀》和《彼此》则着重叙述爱与欲的冲突,并关注金钱对情感的介入作用。在纯粹的爱的天平上,金钱依然成了一个不可漠视的砝码。《云雀》中春风朗诵名牌香水说明书的细节则反应出叙述者对消费社会的敏感,品牌在无形中渗入我们的生活。“彼此”这个标题很好地揭示了金仁顺的世界观,她没有部分女权主义者那么极端,在她看来,男女不仅在身体方面都彼此需要,也在心理上彼此需要,道德上并没有高下之分。事实上,作为欲望主体的人,并没有能力细分内心那些微小卑琐而隐蔽的想望。这种中和包容的态度决定了她叙事的气象和格局。
乔叶一直致力于叙述人心最深处的纯真善良,将笔触伸向温暖而美好的事物。她的《指甲花开》以指甲花的美辉映人情之美。柴禾守寡后回娘家居住,与妹妹柴枝跟同一个男人生活并老死娘家葬在柴家的祖坟。这个在文明社会看来荒唐的故事却在文学叙述中演绎得合情合理,叙述者给了所有当事人以同情、理解和爱。人物身上也携带着生活本来的两难,无言、将一切留在心底就成了他们的命运。乔叶的《像天堂在放小小的焰火》叙述一对男女同事之间超越两性情欲的友谊。在作者的内心深处,一直为这些世俗所不容的纯洁情感留着一方幽谧的净土。在这个欲望发酵的时代,在混乱的现实面前,作者依然对美丽洁净的事物保持信心,并通过饱满的叙述热情将这种文学世界的真实传递给我们。
戴来的《向黄昏》则叙述出夫妇之间的隔膜,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了一辈子,大家仍然陌生,互不理解。老童和陈菊花就像那两只“拖鞋”一样“一东一西互不买帐地在房间里”。遭到身体拒绝的老童试图到外边的街心花园同比自己年轻的女人在一起宣泄内心的郁积,而陈菊花则在午后回顾自己起伏的一生,“都是因为工作”这句反复涌上陈菊花心头的托词也给他们的不幸找到了部分的时代根据,工作不是使生活变得更好更有意义而是对生活侵占对人性的剥夺。走到人生的黄昏,陈菊花重新找回了年轻时的勇气,与生活一辈子然而完全形同陌路的丈夫分道扬镳。
黄咏梅的《开发区》一反过去女性叙事中女主角“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自恋之态,将视角投向在生活中卸装之后的都市大龄女青年“开发区”的尴尬境遇。此时,疲惫遮盖了青春的流光溢彩,皱纹爬上眉梢,郁闷却上心头,在生活中习得的智慧只能用于对异性的不屈不挠的“开发”中,频频的相亲过程中,她们不仅遭到俗世目光的挑剔,而且也遭遇来自母亲和女性同伴的压力,还有自身的关于身份和年纪的焦虑。白流苏到底在步步为营中得到了,而“开发区”却仍停留在不断的开发中。“开发区”的这种开发和白流苏的算计正是典型的世俗的市民行为,正是哈贝马斯所谓的“与公众相关的私人性的经验……它一开始就具有私人特征,同时又有挑衅色彩”(13)。它挑衅的就是所谓的宏大叙事的启蒙功能。
女性在70年代写作群体中依然占据数量优势,除了1998年被隆重推出的外,乔叶、鲁敏、盛可以、黄咏梅、映川、姚鄂梅、柳营、王芸等都在写作中渐趋成熟。虽然两性情感题材仍是女性创作的重点所在,但是都市的欲望书写获得了更广阔的视野参照更丰富的话语方式,心灵之维再度拓展,时代的困惑、身份的焦虑、爱与欲的冲突等得到了新的演绎。
消费主义的法宝是使一切奴役无形而有序地在场,使被奴役者愤懑压抑却无法摆脱,生活本身已经演化成了世界上最沉重的事业。社会现实变成了一个磁场,消费主义,金钱和性欲汇聚成一只“看不见的手”拉扯着我们的衣襟。一方面现实生活的这种强大的向心力使很多男性作家在作品初露头角之际就转身逃跑了,另一方面对现实的反作用力又转化为部分男性作家的叙事动力和写作资源,使他们能够窥探到经验之外生活长长的阴影。
十年在写作中弹指一挥间,70年代出生的作家群队伍慢慢扩大,他们的作品越来越频繁地扎根于文学期刊、各种选刊选本,并开始得到一些除新人新作奖等安慰青年性质以外的奖项,他们也不断得到批评界的深入关注。总之,“写作十年”可以看成这批作家共同的成年礼,是他们得以摆脱“70后”这顶帽子的光环及其阴影的时候了。
从而立奔向不惑,每个出生于70年代的作家正在面临考验,我们生活在一个今非昔比而喜新厌旧的时代。如何把握这个捉摸不定的时代的表象的精神内核,如何以个人独到的方式叙述出这个消费社会五光十色的迷离与困惑,我们如何在身体已经成熟时在精神上摆脱“未成年状态”,如何承担起作家这个身份的使命已经无法回避地摆在了70年代出生的作家群体面前。■
2008年于穗
【注释】
① [美]伊恩·P.瓦特:《小说的兴起》,41—42页,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版。
② 参见宗仁发、施战军、李敬泽:《关于“七十年代人”的对话》,载《长城》1999年第1期。
③ 邢晓芳:《一批年轻女作家崭露头角》,载《文汇报》1998年5月21日。
④ 卫慧于1999、2000年出版了《蝴蝶的尖叫》,湖南文艺出版社;《像卫慧一样疯狂》,珠海出版社;《上海宝贝》,春风文艺出版社;《水中的处女》,花山文艺出版社;《欲望手枪》,上海三联书店;《来不及拥抱》,百花文艺出版社。棉棉出版了《每个好孩子都有糖吃》,花山文艺出版社;《糖》,中国戏剧出版社;《盐酸情人》,上海三联书店。
⑤ 宗仁发、施战军、李敬泽:《被遮蔽的“70年代人”》,载《南方文坛》2000年第4期。
⑥ 东西等:《认识晚生代》,载《南方文坛》1997年第5期。
⑦ 卫慧:《上海宝贝》,3页,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⑧⑨ [美]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钟良明译,5、18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⑩ 参见[美]卡罗尔·帕特曼:《性契约》,李朝晖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11)[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159页,全志钢、列成富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2)王安忆:《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2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3)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55页,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本文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创新团队(GW2006-
TB-008)成果。申霞艳,文学博士,副编审,现供职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