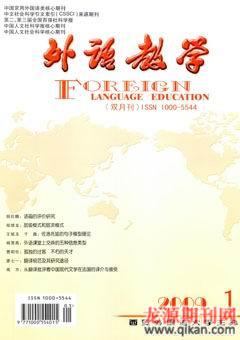语言学派翻译研究的意义观
卢玉卿 温秀颖
摘 要:本文从历时的角度对语言学派翻译研究的意义观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指出语言学派翻译研究的发展轨迹是一个由言内到言外,由静态到动态的过程;在此基础上提出:当代语言学派翻译研究已开始走向整合结构主义语言学静态意义观与语用学动态意义观的新阶段,意义是翻译的本体,而动、静态意义综合研究才是翻译研究的本体研究。
关键词:语言学派;意义观;静态意义;动态意义;翻译研究本体
中图分类号: 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544(2009)01-0104-05
Abstract: Through a diachronic exploration into the theories of meaning put forward by several representative linguistic scholars, the present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studies conducted by linguistic schools has undergone a process from explicit perspective to implicit perspective and from static perspective to dynamic perspective, on the basis of which it advances that the contemporary linguistic translation studies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of integrating the static meaning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lism and the dynamic meaning perspective of pragmatics. Meaning is the key object of translation, and the study of meaning is a return to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per se.
Key words: linguistic school; perspective of meaning; static meaning; dynamic meaning;noumenon of translation study
1.引言
20世纪中叶,索绪尔语言学理论在为语言学研究带来范式转换以后,也对翻译研究产生了革命性效应。翻译研究由“经验陈述”模式转入科学的语言学范式发展时期。人们常说的翻译的语言学派,特指这一时期的翻译研究(张柏然 2008)。
到了20世纪末和本世纪初,语言学理论,特别是语用学理论获得了长足发展,而随着语用学学科理论的逐渐成熟,语言学派的翻译研究也逐步得到了完善,而这种完善主要表现在意义观的完善。2008年第5期《中国翻译》刊登了谢天振教授的“翻译本体研究与翻译研究本体”一文,指出“不要用翻译本体取代翻译研究的本体”。本文将从历时的角度深入探讨语言学派翻译研究对意义的探索历程,分析这一历程的演进规律,并提出“当代语言学派翻译研究已开始走向整合结构主义语言学静态意义观与语用学动态意义观的新阶段,意义是翻译的本体,而动、静态意义综合研究才是翻译的本体研究”,以回应谢文的观点。
2.意义与语言学派翻译观
意义是哲学、逻辑学、语言学及翻译学等学科的核心问题。关于意义的实质历来学派林立,观点纷杂。但就语言学的方法论而言,大体上可分为两类:静态的意义观和动态的意义观。传统上划归“语义学”的部分,如词汇意义、语法意义及逻辑真值等属于静态意义,而划归“语用学”的部分,如含意、用意等所谓使用中的意义(meaning in use)(Katz 1987)属于动态意义。两类意义同时属于意义整体的两个方面,而这个整体意义构成了翻译所传递的对象——翻译的本体。正如许钧所言:“翻译就其具体形式而言,是语言或符号的转换,而语言或符号转换的根本目的,便是‘意义的再生成。……‘意义是翻译的根本”(2003:132)。“当代翻译理论之父”(叶子南 2001:161)、语言学派翻译研究的创始人之一奈达则更直观地指出“翻译即翻译意义”(Translating means translating meaning)。我国学者刘宓庆(2001)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分析意义,指出翻译的实质是“语际的‘意义对应转换(equivalent transferring of meaning)。意义在翻译运作全程中起轴心作用”(2001: 278)。 纵观语言学派翻译研究的发展历程,从雅克布逊、卡特福德、奈达、纽马克到哈蒂姆、格特等,我们不难发现,语言学派翻译研究是对翻译的根本——意义的翻译——的一个逐步深入研究和不断修正完善的过程,是意义观逐步走向全面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分为前后两个阶段:静态意义观阶段和动态意义观阶段。前一阶段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主的现代语言学为基础,后一阶段立足于语言学的新发展——语用学。二者互补而形成完整的意义翻译理论。
2.1 静态意义的翻译研究阶段
张柏然认为语言学派的翻译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关于翻译的论述;另一类是以现代语言学理论为基础的专门从事翻译问题研究的学者的论述。“前者……仅将翻译问题作为语言结构分析的个例或个别途径,其有关翻译的论述与其说是翻译研究,不如说是借助翻译来探索语言研究的方法论;而后者在前者范式的指导下,对翻译过程、翻译方法等范畴进行描述,预期得出具有普适性的翻译模式——语言学模式”(2008:58)。其实,这两类的翻译研究都是针对词汇意义、语法意义及逻辑真值等静态意义的翻译进行的探讨,属于静态意义的翻译研究阶段。
2.1.1 语言学家的翻译研究
索绪尔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创始人,其语言学理论标志着现代语言学的开端。他认为,语言学研究的是语言的共时性,研究的是语言而非言语。语言是一个关系系统,即一种结构。语言的特点并非由语音和意义所构成(而语音和意义是言语的特点,只是语言的物质体现和功能性特点),而是语音和意义之间的关系构成的一个网络,即成为一个体系,也就是语言的结构。这种语言体系被视为一个符号体系。一切符号都可以分为能指和所指。索绪尔之后出现了三派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和美国的结构主义学派。其中,布拉格学派十分重视对语义的研究(这构成了与美国结构主义学派的根本区别),其观点是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的结合,可称作结构—功能语言观(刘润清 1995:87-114)。此外,同属现代语言学派的伦敦学派更多地注意到语言的功能和符号性,而且关注语言出现的情景,从社会学角度研究语言。
作为布拉格学派的创始人之一,雅克布逊注意到翻译问题与普通语言学的关系,认为翻译是语言学方法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语言符号的意义在于用另一种符号对它的诠释,翻译实际上就是对语符信息的诠释。在《翻译的语言观》中,雅克布逊列举了诠释语符的三种方式: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其中语际翻译涉及到一般意义上的翻译概念)。虽然这一切旨在强调在诠释语言现象时语言学对翻译行为的依赖性,但是,认为“对词义的理解,进而也就是对整个语言含义的理解……取决于对语言的翻译”,“准确的翻译取决于信息对等”(谭载喜 2000:243)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雅克布逊认可语言的意义是词汇意义——语言静态意义的总和,翻译是用一种语符替代另一语符所表达的静态的意义。
伦敦学派的奠基人弗斯继承了索绪尔的“结构”和“系统”的概念,并接受了波兰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情境意义”的概念,创造了新的语义理论。他用翻译来阐明语义,认为意义体现在语音、词汇、语法和语境四个层次上,对语言材料在这些层次上进行全面分析,建立在这些层次上的意义对等,才能实现“完全翻译”(totaltranslation)的概念。虽然弗斯提出了明确、系统的理论,并“为传统的翻译课题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开辟了新的途径”(谭载喜 2000:248-249),但仍只不过是静态意义对等的详细描写。
弗斯的学生、伦敦学派的代表人物、系统功能语法的创始人韩礼德认为,语言是一个有规则的系统结构,语言系统是一个丰富的意义源泉或意义潜势(meaning potential),语言系统和意义之间的关系是体现的关系,语言意义可分为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语篇意义三个层次;通过对语言系统的研究,才能理解语篇及其语义(Halliday 2000)。由此看来,韩礼德的意义观体现在封闭的语言系统结构中,虽然他也研究语境,但是,正如朱永生所说:“Firth 和Halliday等人的(语境)类型研究最多只能预测语言使用者对语言形式的选择,预测语言的字面意义,而不能预测语言的隐含意义”(2005:28)。另外,韩礼德的翻译研究的出发点是外语教学。他把翻译当作一种特殊的语言对比形式,包括语际间从语素、词、词组等,到句子、段落、语篇以及语法结构等各项的全面对比,以此使学生了解母语和所学外语两种语言的异同。虽然卡特福德在《翻译的语言学理论》中表达对韩礼德和弗斯的感谢时指出:“韩礼德对语言现象的形式和功能的研究对翻译分析所起的作用比乔姆斯基的转换语法和布隆菲尔德的直接成分分析还要重大”,但是韩礼德本人却认为,翻译理论只是普通语言学的一个重要方面(Newmark 2006:65-70)。
通过上述研究我们发现,语言学家对翻译的研究,其根本目的在于探讨语言学理论,翻译研究发挥的只是工具性功能,因而其结论就难免偏颇和局限。该类翻译研究突出的是对封闭的语言结构和系统及其对应各项静态意义的对等,这一特征在张柏然划分的将翻译研究作为学科的第二类文献中依然保留。只是这第二类的语言学翻译理论,其理论基础是语言学——即语言学反过来成为翻译研究的工具,因为“翻译是特定形式的言语行为,而语言学则是研究语言的科学,它能够提供关于语言研究的基本概念、理论模式和方法,因此……对翻译性质、过程和方法的分析和描述必然要用语言学的基本概念、范畴和方法”(张柏然 2008:59)。
2.1.2 翻译学家的翻译研究
随着现代语言学理论由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到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韩礼德的功能语法的深入发展,翻译研究也由语言研究的工具逐步具有了独立学科的性质。这期间奈达、卡特福德和纽马克三位理论家的贡献最为值得关注。
奈达的翻译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描写语言学阶段、交际理论阶段和社会符号学阶段。第一阶段奈达以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为理论基础,对词法、句法和翻译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第二阶段他将现代交际理论和信息论的研究成果应用于翻译,并提出翻译的交际学理论和翻译科学的概念。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从译文读者角度出发,着眼于原文的意义和精神,而不拘泥于形式对应的“动态对等”思想,并且指出翻译过程包括分析、转换、重组与检验,其中分析过程主要分析语法意义、所指意义和内涵意义。在第三个阶段,奈达修正和发展了他的翻译理论,创建了新的理论模式——社会符号学模式,将语言看作一种符号现象,结合所在社会环境进行解释;强调形式也具有意义,并用“功能对等”取代了“动态对等”,提出“翻译即译意”的思想,同时又将意义重新分为修辞意义、语法意义和词汇意义——即指称意义和联想意义两类(廖七一 2002:85-98)。由此可见,不论研究范式如何变化,意义始终是奈达译论关注的焦点。
伦敦学派的语言学家和翻译理论家卡特福德的研究也不例外。卡特福德认为,任何翻译理论都必然利用语言理论——普通语言学理论。他的翻译理论就是以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早期的级阶论和范畴语法为理论基础的。首先,他定义翻译是“用一种语言(译语)的文本材料替换另一种语言(原语)的对等的文本材料”,其中的“对等”是“替换”的基础,提出“翻译理论的中心任务就是确定对等的性质和条件。”他将翻译看成是“一种用语言进行的操作过程:是一种语言文本替换另一种语言文本的过程。”这种“替换”不是“形式意义”在两种语言之间的传输,而是“形式意义”在语境中的功能的传输;这种替换是通过“形式对应”和“语篇对等”来实现的。另外,卡特福德提出“形式对应”和“语篇对等”是通过“翻译转换”完成的。“翻译转换”是指把原文变成译文时偏离形式对应。卡特福德的这种偏离形式对应的“转换”目的是“使译文具有原文所包含的‘值”,也就是使原文语境中形式意义的功能与译文的形式意义在译语语境中的功能对等(Catford 1991)。
纽马克的翻译理论在语言学翻译研究中可以说具有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纽马克分析和总结了各家各派的翻译思想,将文体学、话语分析、符号学、格语法理论、功能语法和跨文化交际理论应用于翻译理论和研究。他对语义结构以及影响语义的诸多因素进行了详尽的分析,针对不同的文本类型提出了其著名的“语义翻译”、“交际翻译”两种方法,并在后来不断地完善形成“翻译关联法”。纽马克翻译理论的核心问题是语义,他把语义分为认知意义、交际意义和联想意义。其中的交际意义,认知意义中的隐含意义,以及联想意义属于动态意义的范畴。纽马克虽然没有对这些意义进一步研究,但在翻译实践中如何采取措施以避免意义走失还是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探讨。另外,纽马克在讨论翻译原则时用“贴近”(close)代替了其他语言学翻译研究学家所惯用的“对等”,但他在根据贴近的程度排列各种翻译方法时,仍然避免不了用“描述对等”、“功能对等”、“文化对等”等“对等”术语来表达。因此,纽马克的翻译理论属于研究静态语义的“对等”翻译研究范畴,但是他在语言学翻译研究中所起的继往开来作用备受学者们的关注。
语言学派翻译研究的两类文献表明,无论出发点是语言学还是翻译学本身,其理论基础——布拉格学派、伦敦学派、转换生成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等——都属于结构主义的语言学;结构主义的一个前提是把语言作为一个自足的系统,其中的所有成分在功能上都是相互关联的,所有成分的意义完全来自于和其他成分之间的功能性关系。因此,其研究都始于语言分析,探讨的都是语言从词汇到句子、语法结构等各个层次上意义的对等。这些意义是语言文字本身固有的属性,这种属性是内在的、固定的、不受任何客观因素的影响,属于抽象的,游离于语境之外的静态意义范畴,即传统的语义范畴。然而,语义只有与语境结合才会构成真正意义上的意义,它随语境的变化而变化,这便是语用学的意义观——动态意义观。
2.2 动态意义的翻译研究阶段
语用学(Pragmatics)属于语言学的范畴,最早见于美国哲学家莫里斯的《符号理论基础》(1938),它研究的对象是符号与其使用者之间的关系。1977年《语用学杂志》的开始发行,给这个领域以正式的命名。语用学逐步与其他学科如翻译学、应用语言学、文学等相互渗透。语用学因其关注言语意义与(言语使用的)语境之间的关系而为翻译研究学者所青睐。将语用学引入翻译研究领域,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理论模式。随着语用学的发展(由传统语用学、关联理论到维索尔伦的语用学新解等)和其对翻译领域的层层渗透,语用学翻译研究日益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形成了自己的发展轨迹,正为翻译学的建构提供有力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
2.2.1 传统语用学为基础的翻译研究理论
传统的语用学是语言符号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的语言学,其研究对象是说话人的意图。传统语用学翻译观认为,翻译是信息交流活动,它重视语言交流中的语用意义,强调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同等的语用效果。
最早运用语用学研究翻译的是哈蒂姆与梅森(Hatim & Mason)。在他们合著的《话语与译者》(1990)一书中,哈蒂姆与梅森从语境的语用学翻译角度讨论了言语行为与翻译、合作原则与翻译。他们认为,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要根据语境对原语的语义进行推理,综合考虑译者和读者的不同文化语境、原语与译语的关联、译文与读者的关联程度,充分挖掘原文的意图,最后把原文的意图在译语中传达出来。虽然该理论较笼统,但它对意义与语境的关系以及作者意图的关注,在语言学派翻译研究的历史演进中,却具有里程碑般的意义。
另一位运用语用学研究翻译问题的是英国语言学家贝尔。他认同Debois对翻译的定义:“翻译是把第一种语言(源语)所表达的东西用第二种语言(目的语)重新表达出来,尽量保持语义与文体方面的等值”(Bell 1991:5)。贝尔重视翻译过程的探讨并且使之模式化。他把翻译过程分为分析和综合两个阶段,每个阶段包含意义的句法、语义和语用三个层面。贝尔还用传统语言学理论、语篇语言学和语用学理论着重分析了意义问题。贝尔认为意义是翻译之首要,他对意义进行了从认知意义、交际意义到语篇意义等范畴的探讨。贝尔指出意义的语用层面包括原文的意图、主位结构和风格以及它们对语境的依赖性。但需要指出的是,贝尔的意义观以系统功能语法为理论基础,他对语用意义的界定模糊,用统而概之的方法认知和表达意义,没能指出理解意义的各个层面的具体方法。
利奥•希金(Leo Hickey)汇编的《语用学与翻译》从多方面探讨了语用学对翻译实践的制约与影响,如合作原则与文学翻译、言语行为的各种语境和方式、语义前提和语用前提、礼貌原则、关联原则、新信息与旧信息、前提与指示、时间指示与空间提示、模糊限制语、话语连接词等制约翻译的因素。利奥指出,在翻译过程中,不论语法、词汇等语言特征怎样变化,总有东西是不变的,那就是意义。语用学旨在阐释译者对原文作者的意图如何反应、如何翻译以及为什么这样翻译,从而做到意义在语用层面上的对等。语用学有助于“获得译文同原文之间的语用等值,从而最大限度地使译文的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等同的理解和感受”(Leo Hickey 2001:8)。
从以上描述中可以看出,以传统语用学为基础的翻译研究基本没有形成翻译的语用学研究所需要的基本概念和可操作性翻译理论,也没有探讨该领域内这些概念的合理性和局限性,这是语用学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的初级阶段。
2.2.2 以关联理论为基础的翻译研究理论
斯珀伯和威尔森(Sperber and Wilson 2001)的关联理论是有关交际的理论,根据该理论,语言交际是一个明示—推理的过程(ostensive-inferential process),它从认知语言学角度提出语言交际是按某种思维规律进行推理的认知活动。关联理论的提出使得语用学对翻译理论的解释力得以更加充分地展示。威尔森的学生格特(Gutt)提出了关联翻译理论。借助于关联理论的语用认知视角,关联翻译理论开展了对翻译过程的认知解释性研究。根据关联理论的说话人进行明示—听话人进行推理的交际观,格特提出“刺激取向翻译模式”和“理解取向翻译模式”,从而达到译文与原文的最大和最佳关联。在格特看来,推理关系是意义协商过程的关键,原文的语义固然重要,但阐释原文作者的意图意义是译者的中心任务。然而这一观点“没有足够重视‘规约性对话语理解的作用,它似乎过分强调交际主体的创造性与主观能动性”。此外,关联理论“将话语的关联性看作是一种必然,认为话语了解的结果是由认知主体在具体交际过程中根据语境变项作出选择、确定。然而,关联理论并没有对这一结果的必然性与或然性问题作出清楚的解释”(何自然等 2001:35)。虽然格特的关联翻译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独特视角,但是正像威尔森(2003)所说“不可把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分别当作字面意义和非字面意义”(引自王建国 2005:24)。
2.2.3 以维索尔伦的综观论语用学为基础的翻译研究理论
1999年,维索尔伦(J. Vershueren)在他的《语用学新解》(2000)一书中以综观的全新视角和适应论的观点理解和诠释语用学,指出语用学是关于语言使用的语言学,其研究的中心问题是意义,这种意义不同于语义学所研究的语义,它是语言使用过程中动态生成的,是“语言的表意功能的发挥”(meaningful functioning of language),即语言对其意义所发挥的意义性的作用——超语符意义或言外之意。在他看来,意图不是决定话语意义的唯一因素,认知、社会和文化因素也会对意义的生成和理解有重要的影响。另外,维索尔伦还指出,因为语言具有变异性,所以语言的使用过程就是做出选择的过程,选择的方式是协商,选择的目的是适应;语言的选择过程是动态的适应过程。
中国学者在维索尔伦的语言适应论基础上创造性地建立了自己的顺应理论翻译模式。戈玲玲(2001)讨论了语境顺应决定了翻译中的语言选择与词语的意义,动态顺应的译文语言选择不仅要顺应时间、原语语境、语言结构,而且要反映交际者的意识程度和作者的真实意图。宋志平建构了新型的顺应论翻译观。他认为,翻译过程的“选择”除了涉及文本、文化立场外,文本意义和信息等是选择的主要对象;这种选择具有跨语言、跨文化特征, 受到文本内外诸多因素的影响,如译文读者的时间环境、审美心理等。顺应性翻译活动的过程和模式可描述为:解读原语文本,选择意义——选择合适的表达策略和技巧,用目的语表述所选择意义——明确翻译目的,选择顺应的语言对象或层面——选择相应的策略技巧,实现相应的顺应。这种语言使用的模式用于探讨翻译过程的探讨,虽可以当作是对原文整体意义的传达方法的探索,而对于原文意义的获得却无济于事(2004:19-23)。
上述语用学翻译研究表明:一方面,语言学范式的翻译对等不仅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翻译的一大特点,也是近一时期以来以语用学为基础的翻译研究的特点之一。语用学翻译理论追求的是语用对等,即语用意义的对等。另一方面,语用学翻译理论,不论是传统的语用学翻译研究还是关联理论的语用翻译研究都以探讨作者意图为中心,寻求语用意义的翻译对等。另外,虽然,语用学所探讨的语言使用中的语境问题能够对翻译主体和受体所处各种环境,影响和制约翻译的诸多文本外因素进行阐释;但是,根据维索尔伦的理论,语用学探讨的是由特定的语境所决定的、在特定的文化氛围中的超语言意义,即言外意义;这种超语言意义不仅仅是意图意义,对这些意图意义之外的超语言意义的翻译研究还少有探讨;它们应该是语用翻译学继续研究的范畴。正如林克难1996年就提出翻译理论的下一个研究重点是语用,而今,虽已取得很大进展,但仍需努力。
3.结语
通过对语言学派翻译研究的历时性描述和分析,我们发现,1)语言学派的翻译研究始终是以追问和探讨语言(言语)的意义的翻译为核心的;2)在语言学派翻译研究的历史演进中经历了两个重大的转变:一是研究主体由语言学家向翻译学家的转变,即语言学作为目的向语言学作为工具的转变,一是研究范式由结构主义语言学向普遍语用学的转变,即语言静态意义研究向语言动态意义研究的转变;3)这一个核心,两个转变不仅反映了语言学派翻译研究本身的历史性、继承性和发展性,而且昭示了翻译研究喧嚣之后回归本体的必然诉求。然而,如何回归,则是我们不能不思考的问题。正如谢天振所说的那样,我们必须区分翻译本体和翻译研究的本体。如果说翻译的本体是指翻译过程中两种语言文字的转换过程本身,那么翻译研究的本体则不仅涉及语言文字的转换过程本身,而且还包括翻译主体和翻译受体所处的历史、社会和文化环境,以及对转换产生影响和制约作用的各种文本以外的诸多因素(2008:9)。而这语言文字转换本身之外的诸多因素,则正是当代语言学派翻译研究动态意义观的核心。由此,我们认为,当代翻译研究只有走动、静态意义综合研究的道路,才能真正回归翻译研究的本体,这一回归是螺旋式的上升,而不是返回起点。中国译界必须警惕重走“非此即彼”、“非墨即杨”的老路,惟其如此,“我们的翻译研究才不会在学科交叉、学科借鉴日益成为当代科学研究突出特征的情况下,迷失自己,不成为某一‘宗主大国的殖民地或保护国”(温秀颖 2007:61)。
参考文献
[1] Bell, Roger T.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ng: Theory and Practice[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1991/2001.
[2] Catford, J.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M].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穆雷,译. 翻译的语言学理论[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91.
[3] Ernst August Gutt. 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xt[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4] Halliday, M. A. K.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0.
[5] Hatim & Mason. 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6] Katz, Jerrold J. Common sense in semantics[A]. In Lepore Ernest(ed.). New Directions in Semantics[C]. Academic Press Inc. 1987.
[7] Leo Hichey. The Pragmatics of Transla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nge Education Press, 2001.
[8] Newmark, Peter. About Translation[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6.
[9] Nida, E. A. Translation Meaning[M].California: English Language Institute, 1982.
[10] Rodger Bell.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ng[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11] Sperber, D. & Wilson, D.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12] Verschueren J.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M].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0.
[13] 何自然,冉永平.《关联性:交际与认知》导读[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
[14] 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15] 林克难.语用——翻译理论下一个研究重点[J].福建外语,1996(4).
[16] 刘宓庆.翻译与语言哲学[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17] 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
[18] 钱冠连. 汉语文化语用学[M].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7.
[19] 宋志平.选择与顺应:语用顺应视角下的翻译研究[J].中国翻译,2004(2).
[20] 戈玲玲.语境关系顺应论对词义选择的制约[J].中国科技翻译,2001(4).
[21] 谭载喜.新编奈达论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22] 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3] 王建国. 关联翻译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中国翻译,2005(7).
[24] 温秀颖. 翻译批评——从理论到实践[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
[25] 谢天振.翻译本体研究与翻译研究本体[J].中国翻译,2008(5).
[26] 许 钧.翻译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27] 叶子南.高级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28] 张柏然.试析翻译的语言学研究[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8(6).
[29] 朱永生.语境动态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卢玉卿,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翻译学博士生,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语言学。
温秀颖,天津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外语系教授,研究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翻译批评、典籍翻译。
收稿日期2008-01-14
责任编校石春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