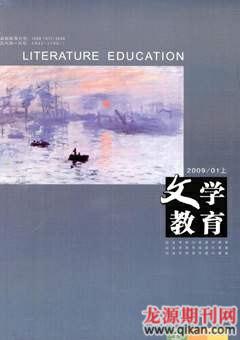“体用”思想的嬗变
“体用”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本源,是中国的元哲学。在倡导思想大解放、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今天,我们应该认真地学习、品味这一元哲学理论,准确把握其思想内涵以及其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实践运用和嬗变,并且结合自身的工作实践不断地加以运用、发展、创新。
“体用”见于体用思想最早可追溯到《易经·系辞》“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易经》中主要用来指占卜中的动卦和静卦。其分别的准则是静卦为体,动卦为用。因此,“体用”之说,其实质可以说是主次、本末之分的问题,也就是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问题,或者说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问题。《墨子·非命上》指出:“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于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这里的“本”、“原”就是指古代圣王和老百姓的经验,也就是“体”;“用”就是在具体实践中去行动、去验证。可以说,墨子的“三表”说就是对“体用”哲学的具体发微。
宋代新儒学由于受佛教思维的影响,名实之辨不断地向深层次推进和发展,“体”和“用”的区别也更受重视了。特别是儒学大师朱熹,更是严格区别“体用”。例如,周敦颐《太极图说》中第一句话是“无极而太极”,就被朱熹理解为:“无极”是就“理”上说;而“太极”是就“气”上言。一谈到“太极”,就意味着“生阴阳”二仪的趋势。“无极”与“太极”所指虽是一样,但其能指却各有差别。这当中其实就已包含着“体”、“用”之内涵意味了。胡五峰《知言》则明确指出:“道者,体用之总名。仁其体,义其用。合体与用斯为道。”并且以体用来解释儒家的中庸思想:“中者,道之体也;和者,道之用也。”北宋张载《正蒙·神化》提出:“德,其体;道,其用,一于气而已。”认为“德”是气之体,“道”是气之用,更加明确地发展了体用的思想元素。
明代哲学家王阳明反复强调“本体”即是“一”,“本体”是抽象性最高、概括性最强的范畴。在谈到“良心”的问题时,他认为,本体良心的具体的发用、流行、展开,就是良能。作为“体”的是良知,作为“用”的是良能。“良知者,心之本体。”并认为作为心之本体的“良知”是无所不包的,是无一物所能超然于其外的,“心之本体,无所不该”(《传习录中》)。从哲学思想角度看,“良知”是理解问题,属于认识世界的范畴;而“良能”则是运用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与实践,属于改造世界的范畴。它强调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精神,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格物致知”的思想精神。例如“为老人折枝”而不为是属于“知”的问题,“挟泰山以超北海”而不为就属于“能”的问题了。再比如初到城里的乡下人并不知道随地吐痰是不道德的而随地吐痰,这是“知”的问题,“不知者不怪”;有些官员明知以权谋私是不对的,但是禁不住金钱、美色的诱惑而丧失了行政道德人格,这就不是“知”而是“能”的问题了,必须严惩不贷!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的渗透,中西文化的大碰撞不断朝着深层进发,“体用”的问题再次被提了出来。洋务派郑观应(中山人)等人就从“体用”的深度对中西文化进行了比较阐发,中西文化的交融可以说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和广度。洋务大员张之洞更是明确地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著名观点,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始终作为“本体”、“本源”的东西;而将西学定位在“用”的层面上,这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和精神是一致的,与鲁迅先生所倡导的“拿来主义”思想以及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精神也是一致的。
可以说,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体用”思想的发轫与滥觞,凝聚了我国历代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桌思想的盛宴。
古林松,广东省中山市教师进修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