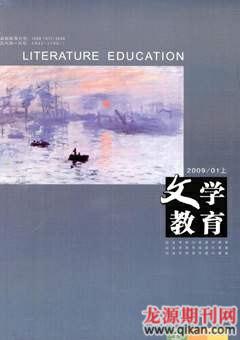一个罪犯的心理自白
张惠雯的这篇小说并不像它的题目那样浪漫,《月圆之夜》实际上是讲述的一个犯罪故事,主人公两次行凶碰巧都是在“月圆之夜”,而在那种浪漫幽深的意境中却透露出死亡的气息。一切看似“都是月亮惹的祸”,其实还有着比“月亮”更复杂难言的非理性因素。不仅主人公的犯罪动机是一个谜,甚至他的整个人生都充满了不可破译的宿命。不仅主人公“当局者迷”,而且作者和读者也无法做到“旁观者清”。
其实每个时代、每个国家都会有罪犯。罪犯是人类社会演化过程中一种必然会出现的边缘群体。在政治家和法学家的眼中,罪犯是对正常社会规范的越规犯禁者,需要加以监禁和惩罚,而在文学家和哲学家的心中,“罪犯”的存在正暗示了我们正常社会秩序里人类精神心理中潜伏的另一种冲动和可能,“罪犯”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非人”,他们是“常人”的另一个隐形自我的外在确证。也许正因如此,自古以来文学家对罪犯的命运非常关注,仅就西方文学传统而言,古希腊三大悲剧全都是关于“罪犯”的故事。《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讲述了一个“政治犯”的故事,《俄狄浦斯王》讲述了一个“杀父娶母”而后自残的双重犯罪故事,而《美狄亚》则讲述了一个为了向夫复仇而杀子的女人的故事。虽然古今文学家对“罪犯”似乎情有独钟,但不能因此误解文学家无情,实际上,真正的文学家是这个世界上最温情的人,只有文学家(包括少数哲学家)才会去抚慰“罪犯”这种被主流社会抛弃的边缘人的心灵,文学家的无情正是他们有情的表现。一个作家写犯罪的故事,只要不是写那种渲染凶杀的通俗侦破探案小说,而是把笔触对准“罪犯”的精神世界和深层心理,那他(她)就坚守了一个文学家的良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惠雯的《月圆之夜》赢得了读者的尊重和理解。
小说以限制性的第一人称展开叙述,“我”是一个被监禁的罪犯,在狱中“我”回想自己的人生之旅和犯罪轨迹,觉得处处充满了玄机和迷惑。“我”的叙述是舒缓的,沉滞的,带有常人难以理解的冷静,有时候仿佛“我”叙述的不是一个关于自己的故事,而是讲述的一个陌生人的遭遇,这种冷静近乎冷漠,散发出绝望的气息。由于选择了第一人称的限制性叙述,所以“我”无法像先知先觉的非限制性叙述者那样掌握着故事的知情权和解释权,恰恰相反,“我”对自己的命运和犯罪动机充满了困惑,无语言表且无法理喻,这使得整个小说笼罩着一层神秘主义的面纱。实际上,这篇小说不仅通过选择主人公来做叙述者,使这篇小说成了一个罪犯的心理自白,而且藉此把作者降到了和读者同样的位置,他们同样对主人公的犯罪和命运之谜充满了疑惑,换句话说,作者和读者都是主人公或叙述者的倾听者,这似乎是对作者话语权力的一种剥夺或放弃,其实体现了作者的艺术选择和非理性主义的现代人生哲学理念。在这个世界上,人的命运和非理性冲动其实是无法用我们惯常所接受的理性主义思维来解释的。理性主义视阈中的因果定律在丰富复杂充满偶然性的人生命运中有时候并不具备必然的阐释能力。所以在这样一篇犯罪小说中,作者与其去充当那种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对主人公的犯罪动机和人生宿命做出貌似合理其实牵强的解释,不如选择目前这种第一人称的限制性叙述者,让人物和作者乃至读者一并陷入非理性的人生迷惘中。至于对犯罪心理和人生宿命的解释权,一切都交给了读者,这是对读者也是对人物的尊重。
小说中的“我”入狱前是一个假烟贩子,时刻都有人赃俱获的危险,长期过着“隐身人”的生活,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呆着旅馆房间里等人取货,灯光对于他来说比阳光更为熟悉。等待的日子总是无聊、空虚和孤独的,而他的等待还充满了恐惧。就在这种难熬的等待中,他不经意地卷入了一场杀人案,而且一不小心成了案件的主犯。回想起来,仿佛旅馆的老板娘从一开始就盯上了他,他一步步地沦为了她的猎物或棋子。他毫无觉察地充当了她的假情人,又在无意和恐惧中杀死了她的丈夫,事实上解救了她和她的真情人,而自己却成了杀人的逃犯。在长年累月的逃亡中,他完全生活在杀人的噩梦里不能自拔,他不知道究竟是不是自己杀死了那个陌生的男人,他陷入了一个永远无法确证的人生谜团。这种无法解脱的痛苦让他不堪重负,他在恶性循环中越陷越深,终于再度行凶,沦落法网。狱中的他从疯狂回归冷静,在无休止的思索中终于明白,原来自己陷入的是一个被神秘预设的命运圈套,他在劫难逃!
李遇春,评论家,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新文学学会理事。